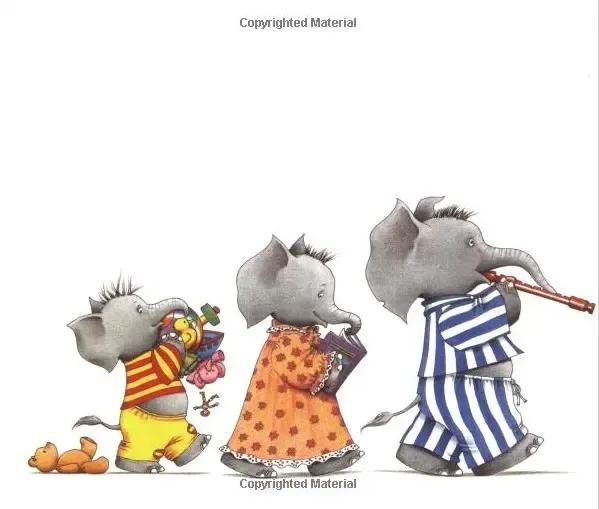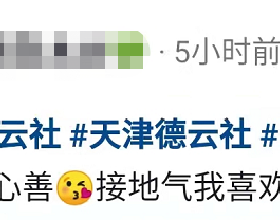村西頭有座橋,叫馬店橋,橋北頭有家飯館叫“好運來”。老闆是趙莊人,叫趙磕巴。他帶著大兒子和老婆開飯店,掙了不少錢。
這一天,飯館來了兩女一男,看相貌打扮就知道是外地人。 三個人要了大魚大肉吃飽喝足,算賬的時候,卻說沒有錢。趙磕巴可不是吃虧的人,想從他這裡佔便宜,吃白食,猶如從螞蟻身上放血割肉。
那個男人說:“我們來投親訪友,現在找不到人,錢也花完了。這樣吧,我帶著閨女來相親結婚的,找不到親戚,你們給操個心,在附近村裡找個好人家嫁了,讓我女婿付飯錢,算是兩全其美的好事兒吧。”
趙磕巴沒辦法,讓人把劉五叫了過來。 劉五在村裡愛操閒心,問閒事兒,感到這是大年三十夜肥豬拱門,自己找上門的好事兒。說媒拉縴這事兒在鄉村最有人緣,有吃有喝有紅包,專業媒人一年也弄不成三兩對,如今有姑娘登門相親,村裡大齡光棍好幾個,豈不是正瞌睡給個枕頭,天下難找這麼好的事兒。
劉五來到飯館,看三個男女個頭不高,臉蛋坨圓,一看就是雲貴川一帶的人。衣服是新的,可是穿在三個人身上很彆扭,不如穿件舊衣服順眼。中年夫妻五十多歲的年紀,一口南方口音,聽不懂幾個字。那個年輕的姑娘能說幾個聽得懂的話,劉五從她惜字如金的嘴裡瞭解了大概情況。
知道姑娘要找婆家,劉五心裡犯嘀咕。他聽說過有一種騙婚的行當,叫放鷹的,專門騙老光棍。有些男人想掙錢,不會做生意,邊在老婆女兒身上打主意。不顧羞恥,帶著老婆女兒或者兒媳婦,跑到外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經人介紹給村裡一些大齡青年,收取一筆彩禮後結婚,女方過幾天找機會逃掉。如此反覆,能掙不少錢。
劉五害怕上當受騙,決心先搞清楚三個人的身份。他對身邊聚攏過來的鄰居說:“看衣著打扮,他們都像是莊戶人,正經人,可是光看相貌不行,得想法瞭解他們的真實底細。”
聽說有姑娘來相親,村裡幾個老光棍急匆匆跑了過來,想沾點光,湊個熱鬧。萬一來了桃花運,遇到姑娘把繡球砸在自己頭上,死活要嫁給,這種沒事兒不是沒有,戲臺上經常演這種戲。
劉紅河家裡是地主成分,三十多歲了還是光棍一條。他在一邊提醒說:“你個笨茄子孫,問他要串的親戚是那個村的,姓啥叫啥,去個人問一問,看有我沒有這個人。有這個人啥情況都弄清楚了,沒這個人就是騙子,讓他們走人。”
劉五拍手叫好。問那個中年男人:“你家親戚是哪個村的?”
中年男人從帆布包裡掏出一封鄒巴巴的信封,劉五接過來一看,寄信人地址是北柳園村。劉五心說,怪不得找不到,是難為他們三個人。
北柳園距離我們村不到六公里,路程不遠,道路很難走。從我們村到北柳園沒有一條正兒八經的路,全都是走村串寨,更讓膽小的人不敢走的是過一截黃河故道,草深林密,都是鄉間小路。不要說外地人,就是我們本地人不常去的,走一趟也迷路,甚至轉悠一天又回到家。
紅河是村裡年齡最大的老光棍,他經常去黃河灘火槍打大雁,迷魂陣套兔子,這點路難不住他。他騎上腳踏車,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在村裡找到那個叫韓四海的人。他老婆也是個南方女人,一說情況,都對上茬口,正是南方人要找的親戚。
韓四海兩口子跟著紅河來到村裡,幾個人一見面,抱著哭的稀里嘩啦,好像三八線隔開的南北雙方失散的親人終於相聚一樣激動。
韓四海付了飯錢,要領著岳父母和小姨子回家,劉五不幹了:“你們走可以,姑娘得留下。說好的在我們村找婆家,吐了不能咽回去,說了話就要算一句話。”
韓四海個頭不高,確是精明人。馬上給劉五敬菸說好話:“劉叔,我妹妹找婆家這事兒,是我老岳父走投無路說的。現在找到我了,就不要較真了。實話和你們說,我這小姨子已經有人家了,我的親姨兄弟,他上個月下了兩千塊錢的聘禮,現在已經著手籌錢蓋房娶親了。”
劉五說:“你姨兄弟下兩千塊錢的聘禮,我們下三千,這個姑娘非留在我們村裡當媳婦不可。”
姑娘叫燕紅,身材不高,模樣不醜,也在一邊猶豫。她嘀咕說:“姐夫的姨哥是個傻子,我不嫁。”
韓四海這會兒沒話說了,呆在一邊抽菸。
劉五心裡有自己的打算,他有兩個兒子,五個閨女。大兒子傻兵,三十多歲至今未娶上媳婦,劉五想把這個閨女留下,給傻兵娶回家,是再好不過的沒事兒。至於錢,他讓結了婚的三個閨女,一人拿一千贊助,給傻哥哥娶媳婦,她們肯定樂意。
劉五看看周圍幾個男人,又怕別人說他損公肥私,中飽私囊,很費心思的對紅河說:“你掏三千塊,讓這個姑娘嫁給你。”
紅河趕緊往後撤身子,連忙搖手:“沒有,沒有,我沒有這麼多錢,我也不做這個美夢了。”劉五又看別人,別人也往後咧身子。
村裡有錢人家的孩子,不需要掏這麼多錢娶親,尤其是不想娶外地媳婦。他們講究門當戶對,雙方互相借勢,互相幫襯。那些娶不上媳婦的老光棍,不管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都是一色的窮光蛋,家裡東西都賣了也不值三千塊錢。
沒人競爭,劉五滿心歡喜把幾個人帶回家,準備掏錢娶親。燕紅姑娘看到傻兵,卻哭鬧起來,說啥也不願意,給多少聘禮也不幹,劉五弄個臉紅脖子粗,只好死了娶兒媳婦的心。
劉五帶著眾人去了馬家。馬家大兒子犯罪剛從號子回到家,想娶媳婦,卻拿不出錢來。
幾個人走出劉五家,碰到蠻子金格急火火的來了。她對劉五說,她願意掏錢把這個姑娘留下來,給他兒子三鬥做媳婦。
三鬥在家排行老三。老大叫勝利,二十八歲了還是光棍一條,前年盲流到新疆了。老二叫二歪,二十五六歲了,去年去北京要飯,至今沒有音信。秦家一家五口住著三間矮草房,年年吃隊裡返銷糧。家裡唯一的家用電器,是勝利看莊稼用的手電筒。這些兒不算事兒,有一個誰也不願說出口的原因,三斗的媽金格名聲不好,是附近十里八村有名的破鞋,當地叫這些女人為“半掩門”。
早年花園口決堤,三鬥爹秦老三的父母、哥哥和全部家當被黃河水捲走,好好的一個家眨眼間沒了。不等水耗幹,他隻身一人外出逃荒謀生。從河南到山東最後到安微,一路上啥苦都吃過,啥罪都受過,秦老三從一個半大小子長成一個棒小夥子,又學會了拉二胡。尤其是豫劇《秦雪梅弔孝》之類的曲目,拉的最好。憑著這個手藝,跟著戲班子到處流唱,最後在三鬥媽的村裡定住了下來。
此時三鬥媽二十七八歲,已經有了二兒一女,肚子裡還懷著勝利。老公吃喝嫖賭,骨瘦如柴,對家裡不管不問,還經常帶一些戲子到家裡胡搞。一個蠻大的家業不到兩年就給敗光了。秦老三年齡二十出頭,因為生理的需要,很注重打扮,拉得一手好二胡,又會對三鬥媽獻殷勤。沒事兒的時候還經常坐下來聽三鬥媽訴苦聊天,再為她拉一段梁山伯與祝英臺之類的小調。三鬥媽內心空虛,一個青春,一個年少,三鬥爹的美言是她最大精神寄託,兩人成了苦命的鴛鴦。
在勝利兩歲的時候,三鬥媽和秦老三私奔外逃。兩人東躲西藏,走了兩年多才回到村裡。本來,兩個年輕人帶個孩子,只要不是太懶,就能過上殷實的小日子。屋漏偏逢連陰雨,勝利六歲那年,三鬥爸患了尿毒症,看病吃藥找醫生,折騰幾年,已經沒有了人樣,瘦的除了皮就是筋,走路不穩。秦老三和當年那個抽大煙的丈夫形同一人。
這些事兒都是聽村裡人講的。梁紅衛還沒有出生,當然也沒有三鬥。打記事起他知道三鬥不是他爹的兒子。其實不問也能看出,三鬥人黑個低,長像不賴。他和尖嘴猴腮的秦老三,他哥勝利矮胖頭扁、二歪的人高馬大沒有一點相像的地方。儘管雞鴨牛羊同一個圈,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出不是一個品種。
有人傳三鬥是鄰村一個在縣裡工作的一個叫大志的人兒子,因為前幾年三斗的媽和大志常來常往,大志的媳婦經常到村裡來鬧。也有的說是何支書的種,三斗的媽和何支書有一腿,是全大隊社員公開秘密。但不管是誰的種,有秦老三在,誰也不敢過來認兒子。
此時的三鬥跟著他的死黨梁紅衛,正在公社大院裡參加徵兵目測。
兩個人從小一起玩尿泥長大,關係很鐵。是那種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的關係。兩人關係好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兩個人都是村裡的小光棍。
在豫東鄉村,男孩子一般十四五歲就定婚,到了十七八歲,父母該操持結婚成家了。
梁紅衛已經18歲,至今還沒有訂婚,在村裡算是大齡未婚青年了。
梁紅衛沒有定婚是因為一直上學。農村上高中的學生不多,被稱作大學坯子,前途未定,家裡不敢訂婚。前幾年,附近一些村有在上學期間定婚的,後來男的或女的考上大學進了城,吃上了商品糧,為退婚打得雞犬不寧。訂婚男女雙方和從中介紹牽線的媒人,本來都是關係不錯的親戚鄰居,因為退婚翻臉成仇。
高中畢業回到村裡,梁紅衛已經進入大齡青年的行列。村裡和他同齡的小夥伴,小學初中輟學回家,早早訂婚找好物件,現在開始籌錢蓋房娶媳婦。村裡和他一樣沒物件的夥伴只剩下三鬥。
昨天,兩個人偷瓜的時候,差點被支書何存財逮住。回來的路上,遇到來公社接兵的部隊幹部,其中,還有一個漂亮的女軍官。那模樣長得,梁紅衛和三鬥都看呆了,直到人家吉普車屁屁後面冒出一串黑煙跑開,他們才醒悟過來。
“三鬥,剛才那個女兵排場不?”
“比戲臺上的貴妃娘娘還洋氣。”三鬥流出哈喇子,他嘴裡咬著巴掌大一條鯽魚。
“我不當新農民了,老子要當兵。走,找趙柱子報名去。”
提著一串魚,剛走到村口,正碰上民兵連長趙柱子。趙柱子40多歲,矮胖敦實,嘴唇肉多皮厚,一件舊的良軍裝穿在身上,滾瓜溜圓的肚子從下面擠出來。軍裝只有三個發灰的銅釦,兩個黑色塑膠扣。
趙柱子手裡提著半桶漿糊,手裡拿著一沓紅的黃的標語。徵兵工作開始了,他的任務就是把“一人當兵、全家光榮”、“保家衛國,人人有責”之類的標語貼在路口顯要處。
“柱子哥,剛摸的魚,回去給嫂子燉魚湯。”梁紅衛將魚遞給趙柱子,一邊接過漿糊和標語。
趙柱子看看那些還在張嘴喘氣的魚,露出一嘴四環素牙。
“你倆又幹操蛋事兒了吧?”
“柱子哥,我想當兵,找你報名。這不是給你帶點見面禮,要不嫂子見了我,又跟扒她褲子一樣,生氣罵我。”
“我和你說,咱們一個鄉九個大隊,給了八個名額。我們大隊這個指標,王莊、趙莊、何莊、馬店四個自然村上百號人爭。何支書侄子外甥五六個,那還能輪到你們去?”
梁紅衛道:“柱子哥,我要當了兵,給你弄一套新的卡軍裝。看你身上這件破的確良,烤糊的紅薯一樣,至少有十年,聞著有股牛糞味兒了?”
趙柱子將菸屁股吐在地上,雙眼迷成一條縫:“我大舅哥給我的二手貨。新的給了他大舅哥。紅衛,你說話算數,可不能騙我。”
“騙你是小狗,一輩子蹲著撒尿。我到了部隊,馬上弄一套寄回來。”
趙柱子提留著魚走了,撩下一句:“幫我把標語貼好,我給你填表去。”
沒想到,兩個人目測一個也沒有過,公社武裝部大胖子李部長在他手裡的花名冊上仔細查了一遍,在梁紅衛和三斗的名字後面打了個很大的叉號,好像要槍斃的犯人佈告。梁紅衛心裡頓時涼透:“目測都沒過,還當個毬的兵。走,回家去。
兩個人想當兵,大隊和公社卡著名額,你沒辦法。三鬥回到家和金格說,金格當天晚上去找何支書。金格和支書關係好,全大隊的社員都知道。三鬥輕而易舉弄到一個名額,這事兒算是沒跑了。尤其讓三鬥高興的是,金格東拼西湊拿三千塊錢給他娶個媳婦,當兵前結婚娶回家。
梁紅衛想當兵,沒有關係。趙柱子為了那套的確良軍裝,給他出個餿主意,要他託媒人去何支書家提親。何支書的四女兒梅香長的一等一的人,和梁紅衛比較般配。
梁紅衛託的媒人叫張永聚,是親舅張永簡未出五服的堂兄弟,梁紅衛也叫舅。張永聚是專業媒人,從不幹農活,肩膀上挎個糞籮頭,走東家,串西家,專門給人介紹物件。三里五村,誰家的姑娘長成了人,誰家的小夥串成了個,門兒清。別看老頭一天到晚有點瘋瘋癲癲,到那個村都格外受人歡迎。青年男女喜歡,當父母的同樣要求他幫忙。據說,經他的手介紹成家的男女有幾百對。具體多少沒有統計,反正,至少每個月都有人設宴招待,更有意思的是,好多人父母是經他介紹結的婚,下輩的兒女還是經他的手說媒牽線,結婚成家。
張永聚剛進何莊村,梅香騎著腳踏車,帶著兩籃子青草過來了。梅香中等個頭,穿一件粉紅色的確良襯衣,嗶嘰尼褲子,高挽褲腿,一身泥水汗水。張永聚聽到腳踏車響,回過頭來一看,像是絆倒撿個元寶一樣興奮:“四妮兒,你別走,叔給你說句話。”
梅香下了腳踏車:“永聚叔,你有啥話,不是給我說媒吧。”
“咦,你這個妮子,你是孫悟空變的吧。我還沒有張嘴,你就知道我要說啥。你這麼排場的一個妮兒,該找婆家了,這不是啥丟人事兒。”
“說媒的事兒,你得跟俺大爺說,這事兒他當家。”梅香一臉累的臉上汗水亂流,有點手腳發慌。
“您叔我說了一輩子媒,最會掂量那頭輕那頭重。你是個仙女下凡間,得給你找個有才有貌的薛丁山。我給你說的這個人,你絕對願意。”永聚一見年輕人,嘴頭子格外利落,說的話對方最愛聽。
“誰,不是神仙下凡吧,俺家可養不起這種人。”梅香一笑,露出一個酒窩,怪好看。
“前劉莊的梁紅衛,認識吧。那孩子長的排場,頭是頭,臉是臉,屁股是屁股。還是高中生,一肚子學問。我給他介紹了好幾個女孩子,他都沒有樣中,眼光高著哪。我看你合適,你們倆般配。要是你同意,我給你們牽個線,中不中?”
何梅香一聽是梁紅衛,“撲哧”一下笑了。他們倆是初中同學,互有好感,便說:“中,你跟俺大爺說吧。”
進了何支書家的院落,梅香故意把大門弄的叮噹響,對後面喊了一句:“永聚叔,你這是要去哪兒,到家歇一會,喝口水吧。”
永聚高聲大嗓的應答:“中,妮兒。你爸在家沒有?”
“在。來吧。”
何支書頭上那頂綠軍帽沒戴,露出光禿禿的白禿頂。四周幾縷又長又細的頭髮圍著禿頭,像沙堆上面幾根茅草一樣。他穿了一件白背心,戴一副花鏡正在屋裡讀新來的報紙在《人民日報》的社論上勾勾畫畫。今天晚上,全大隊幹部和黨員會議上,他要讀這些重要的文章。看到永聚過來,只是透過花鏡上邊的邊框,快速的掃了一眼,算是打了招呼。
“張永聚,你是聞香到。我看那個村請客吃飯都少不了你,比我這個支書臉面還大。”何支書一邊看報紙,一邊漫不經心的說。
支書這話很耐人琢磨。你可以當批評的話,也可以當作表揚的話。如果你對支書沒意見,絕對是當鼓勵表揚的話來聽。
張永聚一聽,連著嘿嘿幾聲:“支書,我的臉哪有你的臉大。你沒邊,我有。人家請我就是陪客,照應著把事兒辦好。你去是領導,得多大的面子才敢請你啊。”
何支書咳嗽一下,把痰嚥到肚裡。張永聚立馬不說話了。不住的拿眼觀察支書的面相,然後低頭抽菸。人家畢竟是支書,張永聚四處說媒,往好了說是積德行善做好事,上綱上線就是遊手好閒,不務正業,這個小辮子在人家手裡攥著,稀里馬虎可不行。
梅香換了一身衣服,白的良襯衣,牛仔褲,頭髮也收拾潤貼。端了一碗紅糖水過來:“永聚叔,你喝口糖水,天熱的不行。”
張永聚算是找到了話匣子:“還是俺四妮兒好。人長的排場,還機靈懂事兒。對了,看到四妮我想到個事兒,閨女定了沒有?”
梅香站在一邊,看著大爺和永聚。何支書依舊看報紙,沒有看其他人。他當支書二十多年了,從來就是這樣。半天,嘴裡扔出一句話:“沒哪。”好像閨女不是親的與他無關。
“我這裡有個媒茬,我給你說說,你看中不中?”永聚仰著臉,討好的看著支書和他閨女。
“誰家的孩子,說說。”
“前劉莊村的梁麥囤家的三兒子,高中畢業生,和四妮兒是同學。那小子頭是頭,臉是臉,屁股是屁股,跟戲臺上的文官武將一樣威武,是個好坯子,給你做女婿絕對配上咱閨女。”
何支書這次把報紙放下,眼鏡摘下,看了張永聚一眼:“那孩子我認識,一般。張永聚,你說話別摻那麼多水份。誰不是臉是臉,頭是頭,你家孩子頭和屁股長一起。”
“人家可是高中生,一表人才。”
“咱們大隊的高中生多的是,比他排場的男孩子也多的是。俺梅香要找個吃商品糧的人,才能配得上,那個孩子,不行。”何支書沒有說明為啥不行,張永聚也不敢多問。
何支書看了女兒一眼,對張永聚說:“昨天晚上我做個夢,俺梅香的女婿來了,騎著高頭大馬,跨著盒子炮,是個軍官,還是個團長哩。”
張永聚裝傻:“何支書,我咋聽著像是胡蘿頭,找他可不中,他比梅香年齡大的多。”
胡蘿頭是當地一個土匪頭,娶了七八個姨太太。每天騎著馬帶著老婆四處顯擺,是當地男人做人的標杆。四九年解放的時候,他帶著一家老小跑到緬甸去了,在哪裡種鴉片。
張永聚沒有說成媒,卻把梅香和梁紅衛的情絲牽出來嬲在一起。在梅香的勸說下,何支書放了梁紅衛一馬,讓他參加了徵兵體檢。梅香給他幫忙,找她表姐出面,梁紅衛體檢安全過關。有這幾次接觸,梁紅衛和梅香成了一對戀人,難分難捨來。
體檢回來,幾天漫長的等待。
晚上,門外一陣腳踏車鈴響,聽到大爺問:“妮兒,你喝湯沒有?”
梅香的聲音,很好聽:“喝過了,大爺。我來找紅衛,給他送本書。”
梁紅衛一骨碌從床上翻起,兩步走到門口,和梅香差點撞個滿懷。
“梅香,你來了。”梁紅衛有點羞怯。
“是啊,不歡迎?”梅香倒是落落大方。她這話,不是說給梁紅衛的,而是說給劉麥囤聽的。
屋裡登時清淨下來。梁紅衛感到沒有話說,何梅香有話不知道從哪裡說起。
梁紅衛看著梅香,燈光下,朦朧中,梅香更是楚楚動人。梁紅衛笑道:“我當兵走了,給你寫信,你要回。
梅香道:“我怕你不給我寫信。人一走,風箏脫線一樣。還有,你要訂婚了,我算啥人。”
“到部隊你好好複習功課,爭取考上軍校。”何梅香看了梁紅衛一眼,兩人相視一笑。
梅香要走,兩人推車出了院子,屋外月光把大地照成一片銀白。梁紅衛汽車帶著何梅香,咬著牙使勁兒,他想盡快走出村子,躲開那些熟悉的眼光。
前劉莊村到何莊村有三四里路,中間是一些莊稼地。儘管已是深秋,莊稼收回家,仍有一些乾枯的玉米在地裡長著。來到玉米地,梁紅衛捏了一下腳踏車閘,停在路邊。很有默契,何梅香跟著梁紅衛進了玉米地。
玉米葉子和棵杆都已經乾透,兩人有點慌不擇路,弄的呼啦啦作響。走進玉米地深處,在一個較為寬闊的地方,梁紅衛脫下外衣鋪在地上,一把抱過何梅香,放在地上。何梅香身體似出水的鯉魚一樣,不停的擰動打滾,不肯就範,把梁紅衛累的一身汗水。渾身沒有了力氣,看何梅香沒有配合的意思,只好作罷。
“你怎麼了?”梁紅衛一臉的憂傷,他擔心自己理解錯了女人的心思。
何梅香沒有言語,只是呆呆的望著梁紅衛。她心裡再翻騰,嘴裡卻說:“我怕懷孕。你走了,我挺個大肚子,去哪裡找你?到時候,你再不認賬。”
“你懷孕生子,我求之不得。我是買一頭母驢,肚裡帶個駒兒,雙喜臨門,我賺大發了。”梁紅衛戲謔道。
何梅香伸手打他,被梁紅衛抓住了胳膊,就勢推到在地,一陣手腳忙亂,梁紅衛沒有更多的想法,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辦了她。”幾下撤掉衣服,直挺挺的撲了上去。
“哎呀”一聲,梅香的疼一聲喊叫,讓梁紅衛腦袋一片空白。
兩人收拾妥當,悄悄走出玉米地,看到腳踏車旁站了一個人。
“我看到你們兩個了,你們沒辦啥好事兒。”原來是三鬥。
梁紅衛一股無名火竄上頭頂,還沒發作,何梅香如發怒的母獅一般,衝上去朝三鬥猛打。
三鬥不知是哭是笑,幹呵呵幾聲:“我本來找你借衣服,看你和梅香出來,沒敢打攪。我想跟你一起送梅香,又怕耽誤你們說悄悄話,只好在後面遠遠的跟著。你們兩個進玉米地裡解手,腳踏車扔在外面,我怕有人偷,站在這裡看車子,怎麼出來不分青紅皂白的打我。”
梁紅衛走過去,拍拍三斗的肩膀,算是安慰和道歉:“深更半夜,人嚇人,能把人嚇死。好了,別難過了,跟我一起作伴,把梅香送回家。”
第二天天上午,女方一家三口兒來了,後面跟著她姐和姐夫。有他姐夫韓四海當翻譯,溝通交流方便多了。幾個人看了看三斗的家,房子泥坯瓦房,不太好,可家裡東西比較多。糧食跺滿了一間屋子,足有四五千斤,門外扎著腳踏車,牲口棚裡有白馬,還有一大一小兩頭牛,一頭驢。豬圈裡有大大小小三頭豬,兩隻羊,儼然一個小康之家。
中年夫婦滿臉高興,一個勁兒的說:“好人家,過的比較殷實,女兒嫁過來不會受罪,這門親事算定下了。”
當天舉行婚禮,三鬥請了村裡大廚黏魚頭掌勺,做了個“回門席”。回門席是閨女結婚三天情新女婿吃的席面,新客登門吃第一頓飯,當然是最好的,也非常講究。
一般是先上道果子點心。點心都是姑娘家的近親前來賀喜時專門買來用的,第一道肯定是舅舅家,然後是姑姑家、姨家往下排。夠了八家其他就不上了。親戚不夠,就以鄰居家的名義往上頂,上誰家的點心誰敬酒。後面是八個盤子裝的冷盤。葷菜是白菜心拌豬肝、大蔥拌豬心或豬腸,也有豬耳朵和豬舌頭。
素菜是拌藕、拌粉絲、拌黃瓜、拌芹菜等一些菜。主菜是上八個扣碗。這些菜是先拌好面用油炸,再切好一些蔥花薑絲放到碗底,先用小碗上籠梯蒸,熟後扣在大碗裡。葷菜有炸雞、炸排骨、炸帶魚,素的就是冬瓜、茄子和豆角乾菜。撤走八大碗,就是八大件。八大件有甜有鹹,甜的有紅糖糯米,拔絲蘋果。鹹的就是雞、魚、四喜丸子和紅燒肉。
紅燒肉一定是四方塊的,一般用五花肉,不能用刀切斷,俗稱“碗麵”。這種席面老家裡的人叫“八八席”,男人一輩子也只能吃一次這樣的席面。
三鬥家的“八八”席,除了八道果子沒上,其它的都上了。
梁紅衛忙前忙後,比自己娶媳婦還忙活。
熱菜沒上完,那個中年男人喝的東倒西歪了。他和前來陪客的何支書說:“我有話在先,要給女兒找個好人家。去年韓四海的姨兄弟出的聘金,我給兒子娶親花完了。這筆錢要三鬥家還,要不然把女兒領走。”
何支書說:“你說說,得多少錢?”
姑娘的叔叔沒說話,她嬸子說:“拿三千就行了。”
三斗的父母一聽,一邊站著,一句話沒有說。何支書說:“三千就三千,這事就這麼定了。”
姑娘一聽也很高興,當天和三鬥圓房,算是結婚成家。他父母姐姐夫一干人,酒足飯飽之後帶著錢和禮品走了。
梁紅衛在廚房幫忙,始終沒有看到三斗的媳婦。等到客人都走了,才來到新房。
梁紅衛看了那女人一眼,這個女人有三十多歲,個頭不高,眼睛挺大,濃妝豔媚下,掩蓋不住絲絲魚尾紋。看人的眼神,有點對不正焦點的手電筒一樣,胡亂照射,不像正經人。
“三鬥,這個女人比你大很多吧?”梁紅衛把三鬥拉在一邊,悄聲問道。
“大四歲,她今年二十二歲了。”三鬥臉紅撲撲的,有點不好意思。
“這個女人至少有三十歲,你肯定看錯牙口,上當了。”梁紅衛堅定的說。
“這騾子馬我能看出牙口,人我看不出來。大幾歲就大幾歲吧,反正娶到家了,好壞就是她了,不能退不能換的。我老婆說她有個妹妹,讓我幫忙再找個沒有物件的人,挺漂亮的,給你介紹一下。”
梁紅衛往後咧了咧身子:“算了,我還是在本地找吧,外地的老婆我齁不住。”
三鬥挺遺憾:“你要同意多好,我們可以做伴兒瞧老丈人。”
兩天後,三鬥家裡沒有人,回來後發現那女人失蹤了。
梁紅衛聽說後去了三鬥家,三鬥從臉上擠出一絲苦笑。“真是放鷹的,跑了。”
梁紅衛過去,拍拍他的肩膀,算是安慰。
“我把她先辦了就好了。”三鬥說的話不著邊際,梁紅衛愣神半天,居然沒有明白啥意思。
“她睡覺,死也不脫衣服,不和我一個被窩睡。她說自己姨媽來了,我也信。我媽告訴,她身子是乾淨的,沒有大姨媽。真後悔,白花了幾千塊錢,欠了一屁股債,連根毛也沒有落下。
梁紅衛這才明白,笑道:“虧透了。你是貓咬水泡瞎喜歡一場。”
三鬥找了幾天,連個人影也沒有找到。她的姐姐姐夫幾次過來找三鬥要人,說是三鬥把他妹妹高價轉賣了,鬧的昏天黑地,直到何支書出面調解。
兩天時間,三鬥人瘦了一圈,大病一場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