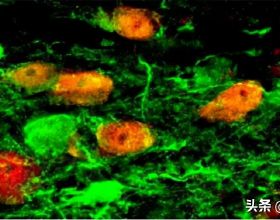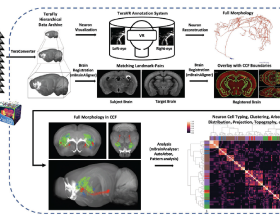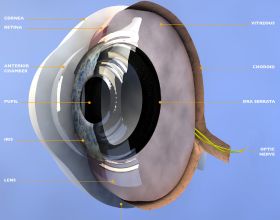二十三,糖瓜粘,灶王爺爺多美言。
今日是北方的小年,我早早地起床,做了早飯,然後直奔超市,採購包餃子用的肉、菜等一眾食材,並買了一瓶黃酒佐餐。回來後,妻子仍在熟睡。
驀然回首,不知不覺間已經過了四十個春秋。離家也已經十餘載,故鄉的習慣卻始終不曾改變,過年,不論小年還是大年,餃子是一定要吃的。小時候在大興安嶺,最盼著過年。那時候物質生活緊張,也只有過年的時候才能吃點好的,穿件新衣服,相信80後的人小時候都對春節有著這種病態的期待和懷念。
那時候,只有我們家春節的時候是三口人,其他的小朋友都去爺爺奶奶裡或者姥姥姥爺家。那時的我尚不明白,為什麼父母要選擇背井離鄉,離故鄉那麼遠,沒想到後來的我,走得比他們更遠。
但是在我心裡,只要父母在身邊,春節對於我來說,就是“年”,離家十幾年,和父母分開兩地,春節對於我來說,漸漸淪為一個普通的假期。父母在身邊,是過年,父母不在身邊,我們卻也要為別人營造出過年的氛圍與感覺。愛,不就是奉獻嗎。現代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凡事都只想索取,不想奉獻,導致橫生枝節。
一歲多一點,我就和母親從哈爾濱去了大興安嶺。所以,父母的故鄉對我來說,其實是異鄉,而我的故鄉,卻是父母的異鄉。在母親的記憶中,我們在大興安嶺的第一個春節,是借住在鄰居家的房子裡度過的。那時候的左鄰右舍比較樸實,不講求租金,看我們母子二人可憐,就把房子借給我們容身。父親彼時還遠在北大荒農場工作。
清貧的歲月,孤寂的日子,母親帶著我在不太溫暖的房子裡過了到達興安嶺後的第一個春節。據母親回憶,除夕那天她燉了一盤排骨,然後就放在了桌子上。那時候的我,十分頑皮,每天在屋子裡跑來跑去,在桌子腿旁邊竄來竄去。中秋前後我們母子二人到的大興安嶺,臨近春節,已經過去了半年的時間,我長高了。這一跑,撞倒了桌子,撞翻了排骨。母親聞聽,跑進屋裡,並沒有責怪我撞翻了飯菜,而是先看我受傷了沒有。見我沒事,然後默默地念叨,兒子長高了。
臘月的大興安嶺,天寒地凍,僅僅這一會,排骨就已經在牆角凍住了,母親無奈,也只能任由它去。直到春暖花開,排骨才解凍,從牆角撿走。後來,父親也來到了大興安嶺,我們一家三口在那裡度過了十九年平凡但是幸福的時光。
每逢春節前,都是父母忙碌的日子。那時候父親在森調隊工作,算是林業系統效益比較好的單位。每到冬季,尤其是進了臘月,單位就開始分發各種員工福利。小到襪子鞋墊,大到電飯鍋電炒鍋,一應俱全。尤其是那個時候緊缺的副食品,豬肉,淡水魚,帶魚之類的,都是幾十斤的分發給員工。
我的廚藝,源自母親的傳授,而母親的廚藝,正是在那個時候鍛煉出來的。老公和兒子要吃,家裡也有食材,她作為女主人,自然要大展拳腳。進了臘月,父親騎著腳踏車,馱著單位發下來的半扇豬肉、年貨,我和母親則另外還要去市場,額外再採購一些。八九十年代,山裡的物資相對匱乏,交通、資訊也閉塞,春節的這次採購,不僅僅要滿足過年期間全家人、來訪客人們的吃喝用度,更要為青黃不接的三四月份做準備。
過年過年,有了採買的氛圍,有了父母在身邊忙忙碌碌,才叫年。辦年貨、包餃子、打掃衛生,十幾年的時間,我圍在爸媽身邊跑前跑後,我們家雖然只有三口人,但很有過年的氣氛。到了正月十五,一向嚴厲的父親還會用柴油拌上鋸末,給我燃起元宵節的燈火。
小時候,我是一個有錢不過夜的主,好東西從來攢不下。過了小年後,我開始忍不住放鞭炮,每天都偷偷地扯下幾隻鞭炮拿出去點燃,到了除夕老爸發現鞭炮少了許多,哭笑不得。從那時候開始一直到高中畢業,放鞭炮一直是我的一大興趣,後來出門上了大學,再回家,那種童趣就漸漸不在了。
在當時的林業局,啤酒是比白酒還要緊俏的物資。我看著大人們喝啤酒,心裡就在想,這個東西黃黃的,冒著白色的泡沫,一定很好喝。於是有一次我嚷著要喝啤酒,結果被老爹揍了一頓,現在回憶起來,歷歷在目。直到上了初中以後,我也被允許逢年過節喝上一瓶,我這個啤酒酒癮,從那時候就逐漸養成了。後來去哈爾濱上學、來青島居住,兩大啤酒之城,成為了我人生當中最大的樂趣。
每隔幾年,父母都會帶著我,從興安嶺腹地坐上火車,一路前行,來到他們的故鄉,松嫩平原,哈爾濱下轄的一個小縣城,在哪裡過春節。每次回去,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們的樣子都會有很大變化,也會有新進門的姐夫、嫂子和我打招呼,後來,我的輩分漲了,新出生的孩子們開始叫我叔叔、舅舅。只有在這個時候,父母的臉上才露出了會心、輕鬆的笑容。那時的我很不理解,直到現在我才明白,那裡才是他們的家,而他們只是我的家。
後來,我離開了大興安嶺,去父母的故鄉——哈爾濱上了大學。大學的幾個春節,我都會帶著一箱子書回家,不像小時候那樣喜歡湊熱鬧了,而是選擇一個人躲在房間裡讀書。那時候的林業系統已經顯出疲態,天然林保護工程開始後,林業局各個單位的效益大不如從前。父親也離開了森調隊,去了另外的單位。但是我們一家三口還是十分珍視這難得的團聚之日。
2005年的春節,我們一家人去了湖南長沙,看望多年未見的大姨、大姨夫。姥姥一共兩個女兒,小女兒嫁到了最北邊大興安嶺,大女兒嫁到了位於南方的長沙。她的兩件小棉襖,一南一北,聚少離多。
長沙的這個春節,也是我們一家三口人在一起不間斷過春節的最後時光。從那以後,我和父母便不能每年都見面,我也很少再能回到黑龍江了。放寒假的時候,我用在冰雪節做志願者賺來的補貼,來了人生當中的第一次遠遊,從松嫩平原一路南下,來到了湖南長沙。母親比我和父親早到長沙接近半年的時間,早已熟悉那裡的環境。我一抵達,她就拉著我大街小巷的逛,帶著我買衣服,那時候我已經長大,自己也能賺點錢了,但是在她心裡,我始終是那個撞翻排骨、愛喝啤酒、愛放鞭炮的孩子。
大學畢業後,我從哈爾濱來到了青島,我們一家人從此聚少離多,春節對於我來說意義變了,變成了我和父母相聚的節日。那時候的我經常為了回家的火車票而費盡周折。每次回家,都會發現父母的頭髮又比從前白了很多。2006年的春節,我一個人身在青島,處於失業狀態,為了生活不得不去網咖打工。除夕之日,按黑龍江的習慣,下午兩點前後就要吃年夜飯,我自己煮了速凍餃子,做了紅燒雞翅。給父母打電話說:我很好,請放心。也給同樣身處異鄉,在廣州一個人過年的她發簡訊,互相鼓勵,互相溫暖。
除夕夜正值我的夜班,午夜十二點的鐘聲敲響,上網的客人稀少,我打掃好了大廳裡的衛生,老闆給我們煮了餃子。面對著延安路上的車水馬龍,我迎來了人生當中的第二個本命年。那時候的我,不會想到自己會在青島生根發芽、成家立業,不會想到她會從廣州遠赴青島,和我組建家庭。
四十年的歲月,從小學到中學,從到大學到畢業工作,我走出了興安嶺,走進了山海關,總盼著自己長大,現在,卻越來越怕長大,怕歲月流逝。我離父母卻越來越遠,父母也一天天的衰老,父親的酒量已經大不如我,母親的廚藝也日漸生疏,漸漸要和我學習了,而我的頭上也早生了華髮。
在大興安嶺的那些歲月,父母總盼著我快點長大,盼著我能幫他們乾點什麼,而當我上了高中,真正能幫他們做些什麼的時候,卻發現這時間是這麼短暫,轉眼就到了上大學離家的日子。子欲養而親不待,或許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最大的悲哀。
後來我在青島有了自己的家,父母便從黑龍江來青島過年,往返於東北、山東兩地。母親也會在餐桌上把我小時候的故事說給她的兒媳婦聽,兒媳婦也會把她的故事講述給婆婆。
但是現在的日子雖然富足了,卻少了從前的些許年味。一方面是經濟社會的發展,加速了人口的流動,人們不像從前那樣能夠時不時地膩在一起,親情淡漠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物質的極大豐富,讓人們對春節的這個儀式沒有了過多的期盼。以前為了這個儀式,全家人會節衣縮食、絞盡腦汁,讓除夕這一餐年夜飯儘量豐富、儘量富足,讓孩子們的身上穿戴整齊,迎接未來。它不僅是一頓飯,更是一個儀式、一種美好的寄託。
為什麼要叫“辦”年貨,而不是叫“買”年貨,因為在物質匱乏的歲月,年貨這種東西不僅僅要靠錢,更要靠思維、靠辦法,才能搞到。而這個過程,正是過年的樂趣所在。現在,辦年貨成了買年貨,只要有錢,啥都不缺,但是唯獨缺了那個“辦”的過程。而且由於人們工作普遍很忙,996的節奏過後,哪還有力氣去買年貨?除夕前一天放假,又有誰有精力大包小包的採購東西?更多的是選擇在家休息,躺平七天。
現在的生活不像以前那麼緊張,我們對年夜飯吃什麼已經不在意了,對於已經步入成年的80後90後來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在除夕夜陪在父母身邊,幫老媽做頓飯,陪老爸喝杯酒。然後再陪他們看看那對於我們來說已經早已沒有新鮮感的央視春晚。
爹媽在身邊,才是過年;爹媽不在身邊,春節只是七天假期。今年的春節對我來說,又是一個七天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