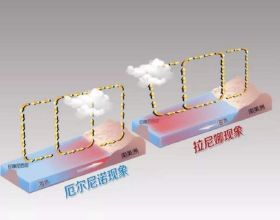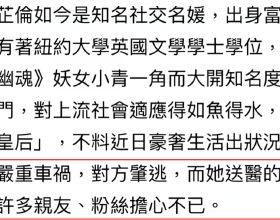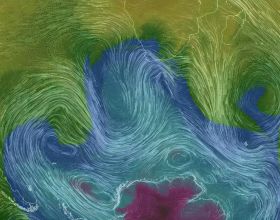一九三六年秋,北上抗日的紅二方面軍三十二軍,到達了甘肅南部的成縣。我們本想在這裡好好的休整幾天,然後繼續前進。
然而,這時候蔣介石的嫡系—王均率領三個多師從三面向我們圍攻了上來,妄圖消滅我們這支不到一千人的戰鬥部隊(三十二軍過草地時縮編為三個營)和軍的後方人員。擔任掩護任務的英雄們激戰了兩天一夜,將敵人殲滅了一部分,但我軍損失亦很大。
這時我們三營八連組成了三個班又投入了戰鬥,我帶著一個班去完成最後一次衝擊任務時,不幸負了重傷,營長對我說:“你的傷很重,不能繼續戰鬥了,自己向橫川方向找軍的醫務所去吧。”
天已黑了很久,我才在橫川找到醫務所,一個十多歲的小鬼揹著揹包抱著一支小馬槍見了我很親切地問:“你是前面下來的傷員嗎?”我們簡單地說了幾句,他便接過我的槍攙著我到房子裡。
屋裡有幾個人,有的揹著皮包,有的從穿著的衣服上看像是醫務所的負責人和醫生,看形勢他們就要出發了。背皮包的矮個子這時對穿白衣服的說:“藥箱沒有馱走吧!快給他上藥。”
穿白衣的沒說什麼順手拿來一個藥包,一開啟我的傷口,他愣了:“呀!傷很重呀!怎麼辦?”
我聽了大吃一驚,心想:周圍的敵人很多,醫務所走了,跟前又沒有老百姓抬擔架。就算能走幾步,可是傷在腿上,如果要過河浸了生水,不就一步也不能走了嗎?草地那樣艱苦都過來了,難道快要到勝利的時候,斷送了我的生命不成?
想到這裡我就大叫:“同志,你給我換藥吧,只要我還有一口氣,還能動一下,我就要跟著主力紅軍走到抗日前線去!”
穿白衣服的一邊給我換藥一邊嘆著長氣,那個背皮包的心事重重望著我的傷口,雖然他們沒說什麼,可我卻很明白他們的難處。這時有人在後面喊叫:“部長,走吧!後面的部隊都下來了。”
不久又進來一箇中年人低聲問道:“醫生,藥上好了嗎?部長叫快走!”
“這傷員呢?”穿白衣服的人問。
“咱們攙著他走吧!這一帶老百姓受了敵人的欺騙都跑光了!”
路上斷續地走著部隊,來路上還隱約地傳來槍聲,看來只有少數作掩護的人在後面了。他們兩個攙扶著我在這八月初的黑夜裡,急急忙忙地向徽縣前進。
走不多遠,那個背小馬槍的小鬼跑來叫道:“姜醫生,部長叫你快去,前面還有幾個傷員沒上藥哩!”
“這個傷員怎麼辦呢?”
“部長叫你就交給這個幹事。”
他們走後,我就靠著幹事艱難地前進。他已經背了不少東西了,但仍很耐心地攙著我走,一路上對我說了不少過草地幾天不吃飯還要行軍的故事,談到黨中央和毛主席發出的北上抗日宣言和紅軍官兵為這宣言奮鬥的情形,他這許多動人的話,鼓起了我的勇氣,我說:“你背那樣多的東西還攙著我走,給我一支槍,我自己走吧。”
他卻安慰和鼓勵我道:“慢慢走吧,只要你能走就行呀!明天我們到徽縣就好了,那裡有四方面軍的總醫院。”
其實我的傷口越來越痛,為了減輕幹事的負擔,我只能咬著牙撐持著前進。
天剛明的時候來到橫河邊上,這是條一里多寬的渾水河,必須涉過。這時幹事在後面整理東西還沒趕上來,我想,他已經為我勞累了一夜,難道遇著這點困難就不能克服,還要等他背過去嗎?
於是我就像初次掛花又沒有衛生常識的人一樣,連褲子都沒挽,就在水裡“撲通撲通”地走了起來,當我拄著棍子一步一步地走到河中間的時候,幹事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到了河邊,他驚歎地叫道:“哎呀!同志,你怎麼不等我來揹你過河呢?傷口灌進了生水,就是輕傷也會變成重傷的呀!何況你的傷還這樣重!”
我頭也不回拼命地向河岸走去。
哎呀!真是輕傷變了重傷,過河之後傷口痛得更加厲害,越來越受不了。我掙扎著前進,好容易才走到徽縣城內,趕上了總醫院。
傷員越來越多,有本軍的也有二軍團的。從他們口中我知道:天水、武都、成縣的敵人已從東、南、西三方面圍上來,幾乎四周都是槍炮聲,敵機輪番轟炸和掃射,簡直連給我們上藥的機會都沒有。
一個衛生員正在給我換藥,突然“轟”地一聲,附近的房屋炸塌了,我們身上都落滿了塵土,醫院的工作人員不顧自己的安危搶救著我們。
晚間,我們在槍炮轟鳴中向北突圍,黑夜裡我迷迷糊糊地不知是誰,反正是自己人把我背出了敵人的包圍。
這樣走了一天一夜,敵人還在跟蹤追擊,部隊只有加快速度才能甩開敵人,老百姓不是受了欺騙宣傳就是怕挨飛子,都躲藏在山野裡,找不著人。醫院的擔架又少,不用說一個醫院,就是再有幾個醫院的擔架也不夠用。
醫院的工作人員也不多,他們已經夠辛苦的了,還在忘我地救護傷員們,這時我的三個傷口早已感染腐爛成一片,整個大腿都在流膿,一過高橋鎮我就痛得人事不省。
中午我才忽忽悠悠地醒來,聽到有人在我的前面叫道:“院長,我來抬吧!你從昨晚抬到現在,快一天了!”
“沒有關係,只要能把傷員運走,不丟掉就行哪!”
我模糊地掀開頭上的被子,才知道抬我前面的就是總醫院的院長,一時感動得連話都說不出來,心想:就是親生父母也沒有這樣好!那個同志好容易把院長換了下來。我決定無論如何也要起來走幾步,好讓同志們休息一下。
可是傷口痛得使我無法爬起來,我正在掙扎的時候,院長同志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
他一邊用右手使勁地擦著臉上的汗珠,一邊用左手慈祥地按著我的胸口說:“同志,你好好地躺著吧!我們再累一點總算是好人,你的腿已經不能動了!”
我一聽更加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豆粒大的淚珠滾滾地往外流,一會兒就把胸前都溼透了。過去的生活又一幕一幕地出現在我的眼前,我感到再也沒有比黨更親切的了,就是死也要跟著親愛的黨!
這天下午,天下著濛濛小雨,黑雲瀰漫山谷和山腰,我們匆忙地轉移到馬踢灘宿營,這裡離高橋鎮最多不過一百里,我們醫院住在北山根一個不到二十戶的小村裡,離開大路足有兩裡多地。
我住的那個四合院,大概是個地主家,人都跑光了,什麼東西也沒剩。最初我們北房住著七個傷員,大概是為了便於照顧,後來護士同志把那四個輕傷員安置到別的地方去了,剩下三個重傷號留在那空蕩的屋子裡。他們兩人都比我矮也比我小,護士叫他們謝胖和小丁。
謝胖是一連的戰士,江西瑞金人,年紀不過十七歲,黑方臉矮矮胖胖的,性子比我還急,他的傷也是在腿上,不過是左腿;小丁是一營的通訊員最多不過十六歲,福建長汀人,白圓的臉,鼻子上有顆小痣,他傷在腰裡,嵌著兩個炮彈片。我們雖是初次見面,但很快就在患難中成為親如骨肉的朋友。
護士同志不知從哪裡弄來了一些柴火,幫助我們煮粥,吃飯,又用鹽水給我們洗了傷口,然後沿火堆鋪了些野草安置我們睡覺。
秋天的下半夜,寒氣逼人,我很快就被凍醒了,火早已熄滅又沒有燈,屋子裡黑得伸手不見掌。我慢慢地爬去摸他倆,不小心觸到了小丁的傷口,“誰呀!”小丁這一驚叫把謝胖也吵醒了,接著他又說,“你怎麼這樣不留神,我的傷就在腰裡!”
“瞧你說的,我的眼睛就是睜得雞蛋大,也還不是瞎子點燈—白費蠟!”這下逗得大家都笑起來,由於興奮過度又忽地引起了傷痛,三人的笑聲便馬上轉為呻吟。
接著我們便像三隻羊羔一樣,頭挨頭地依偎在一起,等護士來換藥、煮飯吃,天明好出發。冷呀,疼呀,等呀!時間似乎過得特別慢。
忽然聽見村裡有雞叫,小丁便很興奮地說道:“雞叫頭遍了,快天亮了。”實際上這已是第二遍雞叫了。這時突然聽到嚓嚓的腳步聲向我們走來,手電燈光也越來越近,不一會兒便聽得進來的兩人問道:“你們起來了?吃飯了嗎?”
這時我們才認出是院長和政委。他們問寒問暖,仔細地檢查著我們的傷口,他們用手電照了又照,看了又看,後來便一言不發默默地你望著我,我望著你,從那微弱的電光中我們看出他倆的眼角都掛著眼淚,最後他倆親切地摸摸我們的頭,含著眼淚慢慢地走了出去。
機警的小丁一見這情況便說:“完了,我們不能繼續跟部隊行動了。”
謝胖卻並不明白:“哼!草地那樣的苦我們都過了,今天還能丟了我們嗎?”
小丁馬上分辯道:“那時我們沒負傷,雖然沒糧吃,但究竟沒有這樣多的敵人追趕我們。再說,那時路上行動的部隊多,掉了隊也不要緊。今天只有我們這個部隊在最後,要是丟了下來,明天敵人不來殺你,地主回來了也會搞掉我們!”
我雖然比他們大,一時也不知說啥好,認為他們說得都有道理。要是真的把我們留下來可怎麼辦呢?可跟著醫院走吧,醫院也實在沒有辦法,如果說非要丟掉我們,院長抬了我一天又是為什麼呢?
這時許多念頭都湧上心頭,真是千頭萬緒亂糟糟的。這時門外又來了兩個人,問道:“小丁在這裡嗎?”
“在這裡。”我們三人異口同聲地回答。
他們進來擦了根火柴,點著了幾根鋪草,我們才認出是醫院的總支書來了。他倆看了看我們的傷,問了問晚間的情形,接著,總支書便把話提到了正文。
“同志們,目前的處境你們也知道:四面都是敵人,我們的傷員多,擔架少……組織上確定把你們留在這裡養傷,以後我們一定會來找你們的。”
他的話還沒說完,小丁便“哇”地哭了起來,我和謝胖也都說不出話來,說什麼呢?事實確是如此。
另一個同志在腰裡掏出一個小包交給總支書,總支書說:“這是上級給你們的養傷費。”他們兩人含著眼淚摸摸我們的頭又親切地一一握了握我們的手,低著頭再也沒說什麼,向外走的時候還不停地回頭來望我們。
事既如此,怎麼辦呢?相依為命的醫院和革命同志離開了我們,叫我們如何不傷心?大家都低著頭,流著淚,想著各自的心事。我們心裡都很明白,這不是組織上不要我們,而是那可恨的敵人把我們逼到這步田地。
為了讓醫院救出多數同志,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再妨礙他們。
“時不容緩,咱們快下決心想辦法吧!”謝胖堅強了起來,首先打破了沉寂。接著我們便緊張地討論了起來。
“呆在這裡是不行的,”我說,“因為我們都是槍傷,明天敵人上來或地主回來一見,非殺死我們不可,還是爬上山找適宜的人家去吧!”
“可是,人地生疏,又怎麼能找著適宜的人家呢?同時我們的口音不對,敵人是會知道的。”
“那麼,走吧,到大路上找部隊去,可能還沒有過完—”
我還沒說完小丁又說道:“如果在路上碰著的是敵人又怎辦?”
我焦急地向四周望,發現兩段燒剩的木柴和門檻下的石頭,又想起來時大路上有兩個破石磙子豎在那裡,突然一個念頭出現在我腦海裡,我一把抓起木柴叫道:“有了,有了……就拿這傢伙。”
我把我的想法告訴了他倆,他倆聽我一說也高興得叫了起來,“好!就這樣,咱們馬上就走吧!”說著,我們就一人拿了一段木柴往外爬。
臨走時,小丁想起了總支書留下的東西便說:“慢著,還有這個哩!”我們開啟一看,才知道是一塊大煙和十多塊光洋。
我們費了很大的勁,才爬到屋外,一聽來路上還有隱約的槍聲,知道後面還有我們的部隊,大家都非常高興,努力地向大路爬去。
可是天還下著雨,道路非常泥濘,加上我們每人還要帶個大木棒,這怎麼成呢?
最後還是小丁機靈,他說:“我們用鋪草搓根繩子,把棒子捆在身上拖。”
這個辦法真對勁,這樣我們爬一會兒,歇一會兒,爬一下,哼一聲,慢慢地向前蠕動。背上的衣服被雨溼透了,雨水和汗水混在一起順著肚皮直往下流,地上的稀泥又一股勁地往上沾,身上的衣服越穿越重,好像馱了幾百斤東西一樣。即使這樣困苦,我們的情緒仍然很高,內心裡充滿了希望。
最初是我爬在前面,可是後來,性急的謝胖一直領先,只有小丁傷在腰裡不好使勁,一直落在後面,可是我們都越爬越有勁。
“這一下倒好,今後回到連裡用不著練習匐匍前進的動作啦!”
謝胖這一說惹得我捂住傷口大笑起來,說: “對,要是我當連長的話,準叫別人出操讓你在家睡大覺。”
“我要不是為了革命,為了抗日,就是死也不幹這玩藝兒。”小丁補充了一句。
我們足足在地上滾爬了兩個多鐘頭才爬完這二里多地,終於來到大路上,看見石磙子一邊一個對立在大路兩邊,我們把帶來的木柴一試正好能搭上,便把三個人帶來的木棒都搭在兩個石磙子上,攔住了路。
只要過路的人碰到這個障礙說一句話,我們便可辨別出是自己人還是敵人。擺好以後,便爬到大路右側十多公尺遠的一個大石頭後面隱蔽起來。
一切都按計劃弄好了,可是靈不靈呢?這幾根柴火棍變成了我們的生命線,我們把希望都寄託在它身上—靠它指示我們救命恩人的到來。這時已近五更,是黑夜最後的一個時辰,也是我們三人最後後決定命運的時辰。
我們三人在大石頭後面又顧慮起來,要是來的不是自己的部隊怎麼辦?要是天亮後還不見部隊來又怎麼辦?許多問題又兜上心頭。
謝胖很樂觀地說道:“剛才還聽來路上有槍聲,一定有我們的部隊在後面掩護,我們就要跟部隊一起走了,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這麼久沒見人來,部隊可能早撤走了,要是敵人故意打槍壯膽的呢?怎麼辦?天都快亮了。”小丁說。
“要是天亮了還不見人來,”我說,“我們就去找最窮的人家,他們是會幫助我們的,只要傷口好了就有辦法。”
我正在勸說和安慰他倆的時候,突然小丁止住了我說道:“聽,前面有腳步聲!”
我們的全部精力便都馬上集中在昨天走過的那條大路上,三人都不顧傷口的疼痛用四肢撲地,靜靜聽著由遠而近的腳步聲,好像不止一個人。
聲音越來越大,我們的精力也越來越集中,可恨的黑天呀,我們睜著六隻大眼也看不出是什麼人。“你們聽,還有馬蹄聲哩!”我輕輕地說。
“前面有幾個尖兵,後面騎牲口的是軍長吧!”小丁不知為什麼突然這樣興奮地說。
“我們喊吧,好叫軍長知道這裡有他的戰士。”謝胖更有些沉不住氣,聽他這麼一說我急忙阻止道:“不要亂動,弄清楚了再說,那幾根木柴擋住了路,他們一定會說話的。”
我們屏住呼吸聽見大路上“踢踢踏踏”地來了一大路人。不一會兒,便從石磙子邊傳來了罵聲:
“他媽的,是誰把木頭攔在這裡。怎麼?就這還能擋住咱們前進!”
“你怎麼不走呢?”另一人在後面催。
小丁一聽是自己人就想大叫,可是他感情太沖動了,反而不知說什麼好。
我和謝胖剛叫出“你們是三十二——”,就聽得有牲口掙扎不前在地上打圈子亂踢,同時有人罵到:“鬼東西!為什麼不過呢?前面有鬼呀?”接著就是一聲鞭子響。
我們一聽這真是軍長羅炳輝的聲音,更加激動起來,小丁仍然叫不出聲來,他猛地一下站起來想向軍長衝去,但又被傷口那可恨的疼痛將他摔倒。
我和謝胖大聲叫道:“軍長!我們是傷號!”
這時突然寂靜了一剎那,聽得軍長翻身下馬喊道:“警衛員,快去看看是誰?”
死裡求生的我們不顧一切地拼命向前爬去,不停地喊著:
“是我!軍長!”
“在這裡!”
兩個身強力壯的警衛員攙扶著我們三人一到羅軍長跟前,我們就像久別的孤兒又見了親生母親一樣驚喜交集,我們的感情都衝動到了極點,再也說不出什麼,只知道用雙手緊緊抱住軍長的腿痛哭,眼淚一會兒就溼透了衣襟。
身材魁梧的羅軍長,彎下他那粗壯的腰,用手撫摸著我們的頭問道:“你們是哪個部隊的?在哪裡負的傷?傷在哪裡?”
我仰起淚臉抽搭著說:“我是八連的。在成縣負的傷。”
“噢,你是趙德文啊!”軍長彷彿一切都明白了,接著便聽得他叫道,“警衛員,把我的牲口拉來給他騎上,我就是走路也不能丟掉他們!”又說,“後面誰把牲口讓出來,叫這兩個傷號騎!”
軍部的科長首先從馬上跳下來喊道:“把我的牲口拿去。”
接著又有好幾個人叫道:“拉我的騾子吧!”
“軍長,用我這匹馬吧!”
“我們怎樣累也不能丟掉傷號啊!”
羅軍長挑了兩匹馬,親自把我們挨個扶到牲口上,又囑咐拉馬的人好好地拉住牲口,別把傷員摔壞了。
遠處又響起了槍聲,總之,我們是匆匆地又踏上了征途。
不久,東方便放出了燦爛的光輝,羅軍長在晨曦中親切地伴隨我們前進。他一方面仔細地瞭解我們的情況,一方面告訴我們:敵人把老百姓都騙走了,出草地後給我們造成了新的困難,但現在我們已經殺出了敵人的重重包圍,敵人用絕對優勢的兵力、飛機和大炮都擋不住我們英勇紅軍前進的步伐!
說著他又問我們吃了飯沒有,叫警衛員把為自己準備的軟麵餅分給我們。他告訴我們說:
“同志們,敵人千方百計地想消滅我們是消滅不了的,可只要我們還有一個人,我們就會戰鬥到底!我們怎麼也不能丟掉你們,我們一定要共同前進!”
趙德文同志簡介:一九三六年紅二方面軍三十二軍北上抗日,指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