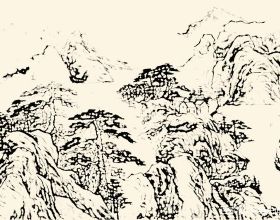葉良駿
從小在老家鄉下的我一直是“野蠻生長”。那天阿孃把我送進初蒙學堂。4歲的我,以為又是一個好玩的地方,一把推開教室的門,衝了進去。
“出去!”穿長衫的老師走過來,兇巴巴地說:“你遲到了!”“遲到,是什麼?”心裡想著,但不敢問。我坐下,先生舉起手裡東西問:“這是什麼?”“戒尺!”“告訴這個新同學,戒尺有什麼用?”“做規矩!”先生搖頭晃腦地吟:“無規矩不成方圓。戒尺不打教不成,戒尺底下有功名!”他說:“上學不能遲到,第一天就沒守規矩,要打手心!”他高高舉起戒尺,輕輕落下,沒有我害怕的痛,但這第一堂課印象深刻,很久以後我明白了,如做人不守規矩,路會走歪,那時,“戒尺”打的就不是手心了。
到上海正式上學,是離家50米的“民治小學”。第一天進校門,見兩位先生站著,對每個學生微微彎腰說:“早!”我學著做,大聲答:“先生早!”我們在空地上坐好,一位先生在臺上鞠躬說:“同學們好!今天我請大家看幾張圖片。”原來是湖南發生大災後的圖。校長說:“讓我們幫幫這些可憐人,請每位同學明天每人帶一把米來,我謝謝你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雖不懂,也明白沒飯吃是一件很嚴重的事。第二天我在米缸裡抓了一把米,媽說:“一把米能幹什麼,給你袋子,多裝點。”我揹著沉甸甸的半袋米去學校。校門口人很多,手裡都拿著東西,人人都提著米。我把米倒進門口的大缸,不小心撒了些在地上,班主任老師走過來和我一起撿,誇我:“謝謝你,這些米能救活好幾個小朋友。”我見不少同學還帶了衣服、鞋子,大筐裡已堆得很滿。我趕緊奔回去翻箱倒櫃,媽媽拿了雙新皮鞋和剛織好的毛衣說:“把這些捐掉吧!”我拿了就走。
校長見我氣喘吁吁地把衣、鞋放進筐裡,過來對我鞠躬,他摸摸我頭說:“謝謝,你真是個好孩子!”他不斷對送衣服的大人作揖拱手,對每個學生點頭致謝。操場上搭了臺,上面站著一排人,有個穿旗袍的女人一直微笑著,在陽光下,她的臉顯得特別柔和,我呆呆地盯著她看,心裡好喜歡。她,把一張紙送給了校長,校長舉起來說:“這位太太捐了三千元!”女人鞠躬,那笑容燦爛極了。短短的晨會結束,臺上的人走了,我不捨得那麼漂亮的太太,跟在她身後送。在校門口,她停下,忽然,摘下手上的戒指、手鐲,取下一串項鍊,還有耳環,全放進了大筐。她看見我,彎下腰說:“你也捐了米?你是個好孩子,好心會有好報。”她輕輕親吻我的額頭。我呆住了,這麼好看的太太親了我。她好香啊!
當時的我,不明白湖南在哪裡,大人的焦慮、同情,我都不明白,但我知道這是行善。小時候,一直跟著阿孃送東西給窮鄉親,這回是我自己把東西捐了,心裡滿是快樂。
兩所學校都很小,沒有操場,更沒有標準跑道。但都是名校長,一位校長是上海第一條公交線路的建設者、慈善家董杏生。一位是新聞教育家顧執中,那天我見到的是名記者陸詒副校長。他們把學校辦得很“大”很“大”。
這兩節開學第一課都很短,卻因戒尺、一把米,還有老師的鞠躬,變得很長很長。它們把身外環繞的形形色色從心上隔除,使我的人生因此渾圓無際,安穩自如。
來源: 新民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