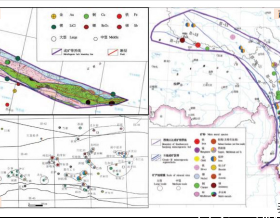三星堆近百年的學術史留下很多富有傳奇色彩的學術故事,其間有三次關鍵性歷史時刻。回顧這些關鍵節點,令人驚喜的是,每個時段的三星堆學人,都為三星堆留下了珍貴的一手記錄,拍攝了關鍵時刻的珍貴影像,已成為中國現代考古學百年學術史的重要瞬間和珍貴史料。
■三星堆遺址出土金杖
縱觀考古百年百大發現,其中發現發掘早、長時段持續發掘且在每個階段都有重大發現的,只有三星堆等屈指可數的幾個遺址。三星堆近百年學術史是一部厚書。我們從三部“日記”重溫“堆史”,揭開時間的鉛幕,重返學術史的若干特殊時刻。
■2021年考古發掘現場
“三星堆的故事,從春天這一頁說起”
——三星堆第一次閃耀
時間:1934年3月16日
地點:廣漢月亮灣燕家院子
三星堆故事的開端,與三個春天有關。
三星堆浮出水面,事起春耕。1929年春天,燕道誠父子在燕家院子整治水車,在倒流堰發現玉石器。很可能此前三星堆文物已經出現,然而這次在燕家院子“浮出水面”,是第一次被記錄在案,從而進入學術史的記憶。
被稱為“三星堆發掘第一人”的葛維漢(David Crockett Graham,1884—1961),1932年擔任華西協合大學教授、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館長。他注意到此前華西邊疆研究學會同仁提供的廣漢資訊,1934年帶領助手林名均到廣漢燕家院子進行發掘。
葛維漢為第一次發掘留下了珍貴的記錄。他在巴蜀進行多次考察活動,大都寫有日記,而今《葛維漢日記》等珍貴資料在美國史密森學會檔案館儲存。《葛維漢日記》中提到,當時的廣漢縣長羅雨蒼以縣政府名義邀請葛維漢和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1934年3月1日,他們來到廣漢,與當地官員一起對此次發掘作最後安排。由羅雨蒼出面主持全部事項,發掘方法則完全由葛維漢負責指導。3月16日開始發掘,10天后,由於當時土匪猖獗而被迫停止,不過這一次發掘仍取得重要成果,出土了系列玉石器等文物。
1935年,葛維漢在《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誌》第6捲上發表《漢州發掘簡報》,這是學術史上第一份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報告。在報告中,葛維漢對三星堆的第一次發掘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記錄,當時使用了許多工具,“旨在更清楚地瞭解地層關係,準確記載每件珍貴器物的方位和深度。儲存這次發掘充實而詳細的記錄,以便能更多地揭示出當地的歷史和重視那些埋藏的文化”。
葛維漢用學到的“風水”術語來描述自己的地勢觀察:“三星堆、孤樹、月亮灣以及附近的這塊土地是顯著而強烈的風水之地,並且是廣漢的風水中心。”“風水”是秦漢以來才形成的理論體系,葛維漢用這個詞體現了他在工作中的自覺嘗試和運用,也反映出三星堆先民對環境的選擇。
對於此次發掘獲得的玉石器,羅雨蒼認為“很有科學價值”,把它們贈送給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至今仍在四川大學博物館收藏並展出。“我對他同時也對廣漢人民表示謝意,感謝他們送給博物館的這些禮物。”葛維漢寫道。
從1921年安特生和袁復禮等一起對澠池縣仰韶遺址進行科學發掘開始,中國現代考古學走過百年曆程。回望過去,可以看到這些早期考古發掘工作以及學人之間的一些資訊交流。葛維漢在廣漢十分關注仰韶、殷墟的狀況,與安特生有學術交流,也注意到同時期李濟主持的殷墟發掘,在撰寫《漢州發掘簡報》時引用了仰韶、殷墟等材料與廣漢材料進行比較。葛維漢的觀察代表了他當時的認識:李濟《安陽發掘簡報》中的三組陶器與三星堆有同樣的紋飾,在殷墟和廣漢文化中發現同樣的紋飾,令人驚異;安特生認為,廣漢與仰韶的出土物極相似。葛維漢當時在簡報裡寫道,殷墟出土文物與廣漢文物有明顯區別,自然也有大致相同之處,如石斧、石刀和石鑿以及陶器的刻紋和印紋等。不同之處就頗引人注目了,即“殷墟出土文物有大量的青銅器、甲骨文、骨器、彩陶等,但廣漢附近遺址就絲毫未發現這類遺存”。
由於當時三星堆考古工作剛邁出第一步,葛維漢自然想不到,數十年後他腳下這片廣漢大地將出土大量青銅器等文物,震驚海內外。
第一次的發掘工作在當時引起了學界關注。葛維漢和他的助手林名均把發掘報告等資料寄給當時在日本的郭沫若。身為蜀人,郭沫若為故鄉的新發現大為驚喜,他回信大意這樣說道:你們真是華西科學考古的開拓者。你們在廣漢發現的器物,均與華北、中原地區的出土器物極相似,這就證明西蜀文化很早就與華北、中原有文化接觸。也希望你們繼續進行更多考古發掘以探索四川史前文化,包括民族、風俗以及它們與中國其他地區的文化接觸。這些都是極為重要的問題。
抗戰時期,學人紛紛入蜀。結合考察結果,衛聚賢於1941年撰文明確提出“巴蜀文化”學術概念,並在其主編的《說文月刊》上先後策劃兩期“巴蜀文化專號”。衛聚賢還呼籲蜀中文化機構繼續“在廣漢太平場(即今三星堆遺址)等廣事發掘,以便出《巴蜀文化論》,在古史上添一筆材料”。
由於時局原因,葛維漢沒能繼續在廣漢主持發掘工作,而轉向了民族學人類學領域,並於1948年離開了中國。20世紀50年代隨著院系調整,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資料撥歸四川大學,更名四川大學博物館。記者此前到該館參觀,館內展出有葛維漢夫婦辭行的名片資料,留下一份珍貴的告別記錄。
2019年,“葛維漢”再度踏上巴蜀大地——這次是他的外孫克里斯多夫·胡根戴克(Christopher Hoogendyk)和曾外孫女應邀回川,沿著葛維漢的學術足印重訪。胡根戴克將外祖父的日記和照片刻錄到光盤裡,贈送給了四川大學博物館,在四川大學博物館舉行了“葛維漢在華西”學術研討會。
2019年3月22日,廣漢的又一個春天。在距離葛維漢1934年發掘整整85年後的這一天,葛維漢的後人在四川學人陪同下重訪三星堆。在三星堆博物館展廳,胡根戴克帶著女兒在葛維漢1934年發掘三星堆的歷史照片前合影。
就在葛維漢後人重訪三星堆的8個多月後,2019年12月,三星堆祭祀區發現三號坑,其後陸續發現四號到八號坑。2021年3月20日,廣漢的又一個春天,春風染綠了鴨子河南岸,國家文物局在廣漢和成都發布三星堆階段性成果。三星堆再次閃耀,驚豔世界。
“火熱的三星堆祭祀坑,發現於那個炎熱的夏天”
——三星堆第二次閃耀
時間:1986年7月18日
地點:廣漢三星堆一號坑
“這些只能有待未來的考古學家們去清理發掘。”葛維漢停下漢州發掘工作時寫道。
三星堆確實開始了漫長的等待。其後巴蜀考古學界雖有所調查和發掘,但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深入展開,直到52年後,才隨著兩個祭祀坑的發現發掘大放光彩。198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現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陳德安和陳顯丹一起主持了一、二號祭祀坑的發掘工作。這一次,考古學人從“月亮”轉戰“三星”。
記者從月亮灣一路步行,跨過馬牧河,走到三星堆,路途中見到鄉親們在田野耕耘,竹林掩映,溪流潺潺,巴蜀田園風光令人沉醉。千百年來,繁華散盡,悠悠蜀墟,生生不息。
“在我未來成都之前,我不知道什麼叫巴蜀文化。四川出土的東西有些什麼,這我有印象。巴蜀文化是什麼?說不清楚。但是,當我看過四川博物館、文管會的工作成果之後,啊!我看到巴蜀文化了。這就是廣漢月亮灣、三星堆……”1984年,第一次“全國考古發掘工作彙報會”在成都召開,蘇秉琦先生在會上這樣說道。蘇秉琦於1981年正式提出“區系型別”模式,影響深遠。他此次入川,觀摩了月亮灣的材料,對於三星堆和巴蜀文化研究工作給出非常重要的指導。
1986年的夏天,尤其是7月18日這一天,值得銘記。這一天,陳德安、陳顯丹等在三星堆遺址磚廠宿舍(現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所在地)整理上半年的發掘資料;磚廠職工在遺址取土,並發現玉石器。考古隊員聞訊後,立刻跑到遺址現場,著手開展工作;陳顯丹也就此寫下日記,留下了珍貴的記錄——《三星堆遺址一、二號祭祀坑發掘日記》(收入《四川文物》2006年第3期“紀念三星堆遺址祭祀坑發現二十週年專欄”)。
那是一個“難忘的三星堆之夏”。炎炎夏日,考古隊連夜發掘,雖揮汗如雨,但心潮澎湃。據考古隊員回憶,他們嘗試了夜間考古發掘,由於是首次開展夜間考古發掘工作,大家沒有任何經驗,全憑著熱情,在夏夜熱火朝天地開展工作。特別是到了後半夜,四處一片寧靜,除了蟋蟀啾啾和一片蛙鳴之外,只有坑中考古隊員偶爾的說話聲和手鏟插土、刮泥的聲響。臨到天亮時,倦意上升,但是大家依然堅持工作。
■三星堆遺址工作站,1986年為磚廠宿舍。
陳顯丹的日記生動細緻記載了象牙、青銅大立人像、青銅縱目大面具、金杖等重要文物的出土。金杖前所未見,一出土立刻震驚四方:
7月30日凌晨2點30分,當我在坑的西北壁的中部用竹籤和毛刷清理時,突然一點黃色的物體從黑色灰渣中露了出來,我繼續清理,發現它是黃金製品,再繼續清理下去,發現上面刻有魚紋,再繼續,發現上面還有其它的紋飾,而且彎彎曲曲越來越長。此時我開始緊張起來,心想這可能是古蜀王的一條“金腰帶”……清理工作在繼續,發現的文物也越來越多,“金腰帶”的清理也在繼續,不久,這條“金腰帶”的全貌也現了出來,原來這是一枚象徵古代蜀王王權的“金杖”。上面除刻有魚紋外,還有鳥紋和頭帶(戴)王冠的人頭像,總長為1.42米。早晨5點過一點,縣委縣政府在接到這一重要報告後,立即派出了36名武警戰士到現場維持秩序。此時我才放下心來,並當眾向大家宣佈:“我們發現了古蜀王的金杖。”這訊息一經傳出,立即引起了轟動,當天來看的人絡繹不絕。
對於三星堆,奇蹟總是“一而再,再而三”。不可思議的事情又發生了,就在一號坑基本清理完畢還在整理發掘資料時,現場不遠又發現了二號坑。陳顯丹當天日記裡記錄道:
8月14日星期五,晴。我們正在磚廠整理祭祀坑發掘資料,至下午18點,磚廠挖土民工楊永成來報,在距一號祭祀坑不遠的地方又發現了文物,我即刻趕到現場,發現又是一個祭祀坑,發現的情況與一號祭祀坑一樣,也是在挖“神仙土”時挖出來的(所謂神仙土,即是人們從陡坎的最底處向裡挖空,然後再從最高處用鋼鍁倒土,這樣一來可以省力,又可以一次倒下兩、三方土),現已暴露出一個銅面具,並能看到其它的灰燼。
時間在三星堆似乎是在盤旋往復中前進的。30年後,也是在這一天,2016年7月18日,“三星堆與世界上古文明暨紀念三星堆祭祀坑發現三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廣漢舉行。作為學術紀念,這一天釋出了陳顯丹編著的《三星堆祭祀坑發掘記》,發掘日記也收入書中。
“考古人只相信天道酬勤,只相信地道酬勤”
——三星堆第三次閃耀
時間:2019年12月2日
地點:廣漢三星堆三號坑
2021年3月20日,三星堆第一次集中釋出階段性成果,立刻火遍全國,然而時鐘要由此往回撥轉大概16個月,回到2019年12月2日那一天。
這是一個令人激動的“三星堆之冬”,也是本輪三星堆熱潮的起點。
為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四川省委宣傳部組織實施“古蜀文明保護傳承工程”。考古工作者制定新的三星堆考古發掘研究計劃,重啟對三星堆遺址的深入調查、勘探與發掘。專家們認為,三星堆應該還有大發現。隨著工作進展到這一天,發現了“坑”的蹤跡——在挖探溝時,發現三號坑的一角,並露出一件青銅器物的邊緣。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雷雨和副站長冉宏林迅速趕到現場,對於露出的銅器口沿兒,大家還不太敢確定是什麼,又請來開會的老隊長陳德安。
■燕家院子出土寫有“燕三泰”的大石璧,現藏於四川大學博物館。
“大口尊,沒問題。”陳德安下坑一摸,吐出“六字妙音”。冉宏林當天這樣提醒隊員們,要多記日記,事無鉅細,全部記錄。此後順藤摸瓜,一路驚喜不斷,四號到八號坑陸續被發現。隨著準備工作完成,從2020年10月9日開始,對新發現的6個坑啟動考古發掘。
百年來對於考古重大發現的記錄和分享,已天翻地覆。微博微信微影片等易於隨手記錄分享,各種新媒體成為實時記錄交流的新平臺。雷雨是一位攝影達人,微友們隨著考古人的鏡頭,目擊考古發掘的點點滴滴:從考古調查開始,到搭建考古大棚,建立考古發掘方艙,建立考古工作室,裝置測試,專家諮詢,文物出土,再到成果釋出會,其中也有工地邊的巴蜀田野,伸頭來考古大棚窺探的青青翠竹。在他的鏡頭下,有文物,而更多的是來往三星堆的人——學人、學生、技工、安保人員、主持人、記者等,有汗水,有笑臉,有眼睛與鏡頭的對視。一位讀者說,“感覺考古記錄可以出一本書了”。
1984年,雷雨走出燕園,來到四川,就此走進三星堆。2021年,雷雨回到燕園,回到北大。對著師長和學弟學妹,他說道,在不少人看來,三星堆很神秘,其發現過程又頗具故事性,“三星堆的很多發現固然是偶然的,但偶然中實則有必然。我們考古人從來不相信運氣,考古人只相信天道酬勤,只相信地道酬勤”。
近百年來,三星堆三次脈衝,書寫了奇妙的三星堆三部曲。當收穫豐碩果實的時候,讓人想起三星堆的三次閃耀——1934年的春天、1986年的夏天、2019年的冬天。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曾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