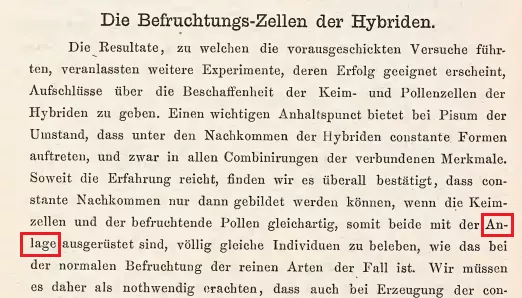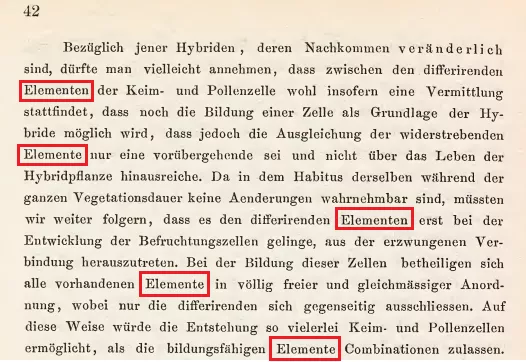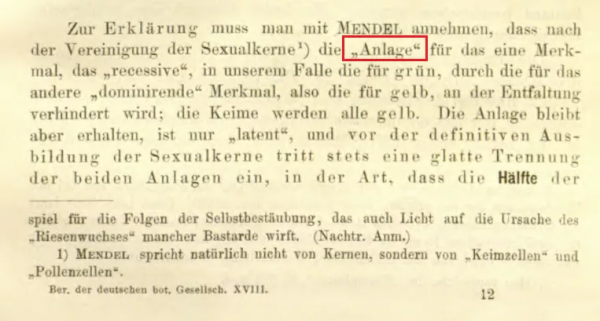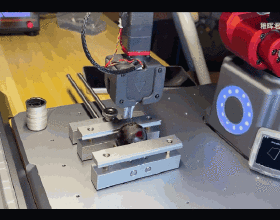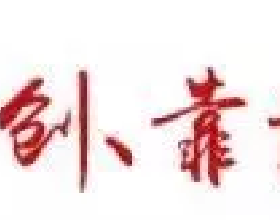1.24
知識分子
The Intellectual
“基因”(Gene)一詞的發明和翻譯堪稱完美 | 圖源:pixabay.com
導 讀
基因所代表的物質在生命中至關重要,它的發現是科學史一個偉大的里程碑。“基因” 這個詞的發明和翻譯也堪稱完美。
旅德免疫學學者、《知識分子》專欄作者商周,在本文介紹了基因(Gene)一詞的由來。
撰文 | 商周
責編 | 陳曉雪
● ● ●
對科學名詞的翻譯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意譯(根據含義來翻譯),另一種是音譯(根據讀音來翻譯)。能在意譯和音譯上都達標則效果更佳,但這樣的名詞極少,一個難得的例子是 “基因”(Gene)。
把 “Gene” 翻譯成基因,在含義和讀音方面都達到了要求,相比其它廣為人知的生物學名詞(比如細胞(Cell)、器官(Organ)、組織(Tissue))的翻譯,明顯要更勝一籌。
那麼,“基因”(Gene)這個詞是如何來的呢?
孟德爾的 “天性”(Anlage)和 “因子”(Elemente)
詞彙不是憑空出現的,只有當人們需要描述一個新鮮事物的時候,創造一個新的名詞才成為必要。“基因” 這個名詞的起源,也就是人類首次意識到基因這個物質存在的時候。第一個意識到基因這種物質存在的人,正是發現了遺傳學法則的孟德爾,但他並沒有為它去創造一個新的名詞。
1854年到1863年,孟德爾利用22種不同的豌豆品種進行雜交實驗,發現豌豆不同的性狀(比如種子顏色、形狀,豆莢顏色、形狀等)是由不同遺傳物質控制的,這些遺傳物質來自父母雙方,而且來自父母雙方的遺傳物質在產生生殖細胞時會發生分離。現在我們知道,這些遺傳物質就是基因。但在只有普通光學顯微鏡的十九世紀,人們對生命的認知還停留在細胞水平,雖然知道了細胞核的存在,但並不知道染色體,更不知道DNA。
面對控制豌豆性狀的神秘遺傳物質,孟德爾在他的《植物雜交實驗》論文裡採用了兩個不同的詞來描述 [1]。
在論文結果部分的 “雜交種的生殖細胞” 單元,開頭一段有如下描述:
圖1 孟德爾《植物雜交實驗》論文截圖 | 圖源:biodiversitylibrary
“ ……就經驗而言,我們發現每一種情況下都證實,只有在卵細胞和受精花粉具有相同的天性(Anlage)時才能形成不變的後代,正如純種植株的正常受精一樣…….”
德語 “Anlage” 一詞有七種含義(包括創造、投資、設施、裝置、結構、天性、材料),在孟德爾上面的文字裡,翻譯成 “天性” 可能相對貼切一些。在這裡,孟德爾用 “天性”(Anlage)這個詞來描述豌豆花粉細胞和卵細胞裡含有的遺傳物質,因為這一段之前論文已經描述了單個和多個性狀雜交的情況,這裡的遺傳物質並不是指單個基因,而是多個基因或者是整個生殖細胞裡的所有遺傳物質。
有趣的是,“天性”(Anlage)這個詞孟德爾在整篇文章裡只使用了這一次。等到文章的結語部分討論控制性狀的遺傳物質的時候,他用了另外一個名詞 “Elemente”,而且用了10次之多。Elemente有三種不同的含義:基本成分、特質、因子。從孟德爾論文的語境來看,這裡的 “Elemente” 翻譯成 “因子” 更合適一些。
圖2 孟德爾《植物雜交實驗》論文截圖 | 圖源:biodiversitylibrary.
而這裡的 “因子”(Elemente)的具體含義,可以透過論文的這一段文字判斷出來。
“對於那些後代存在變化的雜交種,我們也許可以假設,在卵細胞和花粉細胞的差異因子之間發生了某種協調,以至於作為雜交種基礎的細胞的形成成為可能;但儘管如此,不同因子之間的平衡只是暫時的,並沒有持續到雜交植物的整個生命中。由於植物的習性在整個植被期沒有變化,我們必須進一步假設,只有當生殖細胞發育時,差異因子才有可能從強制結合中解放出來。在這些細胞的形成過程中,所有現有的因子都參與了一個完全自由和平等的分配,只有這樣它們才會相互分離。這樣一來,所產生的卵細胞和花粉的型別在數量上就和因子所可能形成的組合一樣多。”
從這一段文字來看,孟德爾不僅談到了來自父母的差異 “因子”(Elemente)的分離,也談到了不同 “因子” 的組合。所以,這裡的 “因子” 指的就是單個的基因。而上面的 “天性”(Anlage)指的則是細胞內整個的遺傳物質。正是因為這一微妙的差異,孟德爾選擇了兩個不同的單詞進行描述。
儘管孟德爾用了這兩個詞對遺傳物質在整體層面和單個基因層面進行描述,但因為其經典論文《植物雜交實驗》長期被忽視,這兩個詞就更不可能走進人們的視野。直到1900年,荷蘭植物學家胡戈-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德國植物學家卡爾-科倫斯(Carl Correns)以及瑞士植物學家埃裡克·切爾馬克(Erich Tschermark)分別在《德國植物協會通報》(Ber. der Deutschen Bot. Gesellsch.)上發表關於植物雜交的研究論文,各自獨立地部分重現了孟德爾的發現 [2-4]。在這三個 “孟德爾的發現者”(注:學界對三人在這一主題上的貢獻有爭議,這裡不仔細討論)裡,有兩人也對因子(Elemente)這種神秘的物質進行了描述。
科倫斯的 “天性”(Analge)
科倫斯1864年出生在德國慕尼黑, 28歲那年在德國圖賓根大學獲得植物學講師職位,並在那裡花了六年的時間進行植物雜交實驗,重現了孟德爾的部分結果。在 “孟德爾的發現者” 的三人中,科倫斯對孟德爾的發現最為了解。他1900年發表在《德國植物協會通報》上的論文,標題就是《關於品種雜交後代行為的孟德爾法則》[3]。
在這篇論文裡,科倫斯詳細地討論到控制性狀的遺傳物質。有趣的是,科倫斯用的詞是 “天性”(Anlage), 而不是 “因子”(Elemente),而且整篇論文裡一共提了22次。比如,在下面這段文字裡:
圖3 科倫斯《關於品種雜交後代行為的孟德爾法則》論文截圖 | 圖源:biodiversitylibrary
“為了解釋這些事實,我們必須假設(就像孟德爾那樣),在生殖核融合之後,一個性狀,即隱性性狀(在我們的例子中為綠色)的天性被另一個性狀,即顯性性狀所抑制,因此所有的胚胎都是黃色。然而,雖然隱性性狀的天性 ‘潛伏’ 著,但在生殖核的最終形成之前,兩種性狀的天性完全分離,所以一半的生殖核接受隱性天性,即綠色;另一半接受顯性天性,即黃色……”
從文中的語境來看,科倫斯用 “天性” 描述的其實是控制性狀的單個基因,而不是所有遺傳物質的總和。所以,他雖然用的是 “天性” 這個詞,但和孟德爾用的 “因子” 這個詞一樣,代表的都是基因。科倫斯之所以選擇 “天性”,而沒有使用 “因子”,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受他的導師慕尼黑大學植物學家卡爾·威廉·馮·內格里(Carl Wilhelm von Nägeli)的影響。就在科倫斯進入慕尼黑大學的前一年(1884年),內格里發表了他的鉅著《生命進化的機械生理學理論》(Mechanisch-physiologische Theorie der Abstammungslehre),裡面談到遺傳物質的時候,使用的就是 “天性”(Anlage)這一名詞。但信奉融合遺傳的內格里用 “天性”(Anlage)一詞描述的不是基因,而是整體上的遺傳物質。
無論是孟德爾,還是科倫斯,兩人都清楚地意識到基因這種物質的存在,但並沒有為它去創造一個新的名詞,而是試著用已經存在的名詞對其進行描述。
真正嘗試為基因去創造新名詞的,首先是德·弗里斯。
德·弗里斯的 “泛生子”(Pangene)
德·弗里斯1848年出生在荷蘭,30歲生日那天他獲得了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植物生理學教授職位,並在同年當選為荷蘭科學和藝術學院的會員。1899年,德·弗里斯寫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細胞內泛生論》(Intracellular Panenesis)一書。雖然是荷蘭人,德·弗里斯的這本書是以當時科學界更為普及的德語出版的 ,出版社是位於德國耶拿的GUSTAV FISCHER [5]。
“ ‘泛生論’(Pangenesis)一詞包括兩個希臘單詞:Pan和Genesis,前者的意思是全部(泛),後者的意思是出生和起源(生)。這是達爾文1868年提出的一個有關遺傳的理論,它的核心是融合遺傳(Blending inheritance)。按照泛生論,生物體各部分的細胞都帶有特定的自身繁殖的 ‘微芽’(後人也把微芽稱微泛生子(Pangene)),這些 ‘微芽’ 可由各系統集中於生殖細胞,父母生殖細胞的 ‘微芽’ 會相互融合從而形成新的子代 ‘微芽’。和泛生論不同,由孟德爾開創的現代遺傳學的核心是顆粒遺傳(Particulate inheritance),即控制性狀的基因是獨立的單位,來自父母的兩個等位基因並不會發生融合,在下一代形成生殖細胞時還會相互分離。”
德·弗里斯在1898年提出的 “細胞內泛生論” 則有些特別,一方面它依然是泛生論,另一方面它拋棄了融合遺傳,提出了顆粒遺傳的概念。正是因為提出了顆粒遺傳這個概念,德·弗里斯以達爾文創造的 “泛生論”(Pangenesis)一詞為基礎,提出了 “泛生子” (Pangene)一詞,並對這一概念進行了描述:
圖4 德·弗里斯的《細胞內泛生論》對“泛生子”(Pangene)做了詳細註解 | 圖源:biodiversitylibrary
“……每個生殖細胞都必須潛在地包含構成相關物種性狀的所有因素。因此,可見的遺傳現象,都是隱藏在生命物質中的最小不可見粒子的特性的表現。事實上,為了能夠解釋所有的現象,人們必須為每個遺傳屬性假設特殊的粒子。我將這些單位稱為泛生子(Pangene)。這些泛生子小得無法看見,但它們的化學分子的順序完全不同,這些泛生子能夠隨著細胞分裂而增殖,並且可以分佈到生物體所有或幾乎所有的細胞中。它們要麼是潛伏的,要麼是活動的,但可以在這兩種狀態下繁殖……”
從上文可以看到,德·弗里斯所提到的 “泛生子” 其實就是基因。德·弗里斯提出的細胞內泛生論最有價值之處,就是提出了顆粒型遺傳這一概念,否定了之前的融合性遺傳。德·弗里斯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在這之前進行了六七年的植物雜交實驗,並且重現了孟德爾關於分離法則的發現。這讓他意識到來自父母雙方遺傳物質並不會融合,而是依然會在產生生殖細胞時分離。
雖然 “泛生子”(Pangene)是為基因創造的一個新名詞,但這個詞的字首(Pan)用來描述基因並不合適,可以說有畫蛇添足之嫌。1909年,丹麥植物學家維爾海姆·路德維希·約翰森(Wilhelm Ludvig Johannsen )在 “Pangene” 一詞的基礎上,進一步提煉出了 “基因”(Gene)一詞。
約翰森的 “基因”(Gene)
維爾海姆·路德維希·約翰森(Wilhelm Ludvig Johannsen)1857年出生于丹麥的哥本哈根,1905年獲得哥本哈根大學的植物學教授職位。1909年,他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精確遺傳學理論的要素》一書。和德·弗里斯的《細胞內泛生論》一樣,約翰森《精確遺傳學理論的要素》一書也是由德國耶拿的GUSTAV FISCHER出版社用德語發行 [6]。
圖5 約翰森的《精確遺傳學理論的要素》一書的截圖 | 圖源:biodiversitylibrary
這本書由約翰森的一系列講義組成,在其中的第八講,他創造了 “基因” 一詞。同時,約翰森還創造了 “基因型”(Genotyp)、表型(Phaenotyp)、“純合子”(Homozygote)、“雜合子”(Hetrezygote)等今天常用的一系列遺傳學術名詞。
關於為什麼要創造 “基因” 一詞,約翰森在書中是這麼說的:
“性細胞含有 ‘某種東西’,它決定著透過受精而產生的生物體的性狀。這種 ‘東西’通常被稱為 ‘天性’(Anlage),但這種說法相當含糊。達爾文提出的 ‘泛生子’(Pangene)一詞,經常被用來代替 ‘天性’(Anlage)。然而, ‘泛生子’(Pangene)這個詞的選擇也並不令人滿意,因為它是一個雙重結構,包含了 ‘Pan’ 和 ‘Gene’兩個詞幹。這裡只需要考慮後者的意義,因此,從達爾文這個眾所周知的詞中分離出我們唯一感興趣的最後一個音節 ‘Gene’,以便用它來取代糟糕的、模稜兩可的 ‘天性’(Anlage)一詞……”
在上面這段文字裡,約翰森對基因是什麼的描述比之前的任何一位學者都更清晰,即細胞裡的 “某些東西”,能決定生物的性狀。他也指出,之前用來描述基因的詞 “天性”(Anlage)以及 “泛生子”(Pangene)都有不足,前者太模糊,後者前面帶了多餘的修飾詞。所以,約翰森把 “Gene” 從 “Pangene” 中剝離了出來。
接下來,約翰森還進一步說明了使用 “基因”(Gene)這個詞的優勢:
“…… ‘基因’ 這個短詞有很多優點,因為它可以很容易地與其他名稱組合。如果我們想到由某個 ‘基因’ 決定的屬性(比如財富),我們就可以很容易地說 ‘財富的基因’,而不需要使用 ‘決定財富的基因’ 這樣更繁瑣的短語。”
不知為什麼,約翰森在提到前人描述基因所用的詞彙時,關於 “泛生子”一詞的發明,只提到了達爾文,而沒有談到德·弗里斯。還有,約翰森也沒有提到孟德爾首次用的 “因子”(Elemente)這個詞。不過,約翰森沒有忘記把發現基因這一里程碑式的發現歸功於孟德爾:
“…… ‘基因’ 的性質,目前還沒有足夠充分的依據。然而,這對遺傳研究的有效性沒有任何影響;只要確定存在這樣的 ‘基因’ 就足夠了。它的發現是格雷戈爾·孟德爾開展的植物雜交實驗研究的最重要成就之一……”
在1909年 “基因” 這個詞被創造出來的時候,正如上文約翰森提到的,人們對基因的自然屬性還並不瞭解,只是知道它的存在,知道它是生物性狀的決定者。但這已經足夠了,因為這開闢了一個全新而且重要的研究領域。後來,人們知道了基因是染色體上的一部分;再後來,人們知道了基因是編碼一段多肽的DNA片段……
從 “Gene” 到 “基因”
把 “Gene” 翻譯成中文 “基因”,不僅同時做到了意譯和音譯,而且提高這個單詞在含義上的準確性。就像上面提到的,“Gene” 這個詞來源於希臘語,本來的意思是 “出生” 和 “起源”,這和 “決定生物性狀的遺傳物質” 的本意不太一致。但當把它翻譯成 “基因”(基本因子)後,就和本意靠近了很多,因為 “基本因子” 同時涵蓋了孟德爾的 “因子”(Elemente)、科倫斯的 “天性”(Anlage)、約翰森的 “基因”(Gene)。從某種角度上來說,將 “Gene” 翻譯成 “基因” 是對原詞的一個提升和超越。
那麼,是誰做了這樣一個完美的翻譯呢?
根據加拿大曼尼託巴大學醫學院謝永久教授的考證 [7],目前能查到的中文資料裡,最早翻譯“Gene”為“基因”一詞的是潘光旦先生,他在1930年發表的《文化的生物學觀》一文中寫道 [8]:
“關於遺傳這一點,我們不預備多說。遺傳的幾條原則,什麼韋思曼的精質綿續與精質比較獨立說、孟特爾的三律、跟了韋氏的理論而發生的新達爾文主義或後天習得性不遺傳說、杜勿黎的突變說、約杭生與摩爾更的 ‘基因’ 遺傳說——是大多數生物學家已認為有效,而且在生物學教本中已經數見不鮮的。”
潘光旦在1930年(可能更早)首次將 “Gene” 翻譯成 “基因” 並非偶然,1922年23歲的他留學美國,並於1926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生物學學位,那裡的教授裡就有著名的遺傳學大師摩爾根。雖然潘光旦後來成為了一名出色的社會學家,但他早期從事過一些優生學的研究,比如在1923年就發表了《優生學在中國》(Eugenics and China)的英文論文,並在隨後將優生學引入到中文世界。或許正是因為他的自然和社會科學的雙重背景,成就了 “基因” 的完美翻譯。
參考文獻:
1. Mendel, G., 1866 Versuch e über Pflanzen-Hybriden. Verh. naturf. Ver. Brünn 4: 3–47.
2. De Vries, H. Das Spaltungsgesetz der Bastarde. Ber. der Deutschen Bot. Gesellsch. 18 (3): 83, 1900.
3. Correns C. G. Mendel’s Regel über das Verhalten der Nachkommenschaft der Rassenbastarde. Ber. der Deutschen Bot. Gesellsch., 18 (4): 158-168, 1900.
4. Tschermak, E. Über Künstliche Kreuzung bei Pisum sativum. Berichte der Deutsche Botanischen Gesellschaft 18: 232-239, 1900.
5. de Vries, Hugo. 1889Intracellular Pangenesis. Gustav Fischer, Jena.
6. Johannsen, W., 1909 Elemente der exakten Erblichkeitslehre. Gustav Fischer, Jena.
7. http://home.cc.umanitoba.ca/~xiej/genetranslation.pdf
8. 《潘光旦文集》第二卷,潘乃穆,潘乃和 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ISBN 7-301-02571-8, 318-319 頁.
製版編輯 | 盧卡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