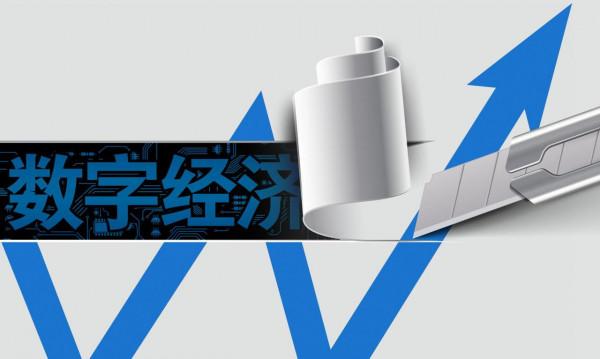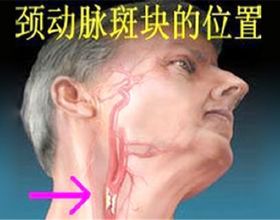陳永偉/文
轉眼之間,2021年已經匆匆過去。據說,從天文學意義上講,2021年是有史以來最短的一年,因為由於地球自轉的原因,它比平常的年份少了65毫秒。但是,對於中國的數字經濟而言,這個“最短的一年”卻顯得無比的漫長,有太多的事情都發生在了這一年。
巨頭的黃昏
2021年上半年,普華永道曾經根據3月的市值釋出過一個全球百大公司的排行榜。當時,中國有兩家公司位列前十,其中騰訊以7530億美元位列第七,而阿里巴巴則以6150億美元位列第九。不過,這次亮相幾乎就是2021年內中國數字經濟巨頭們的最後一絲榮光。因為在不久之後,嚴監管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就降下了。
4月10日,市場監管總局對阿里巴巴的“二選一”行為作出了行政處罰,對其開出的罰單高達182.28億元。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都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天價的處罰。如果對比中國本土的反壟斷處罰歷史,那麼這個處罰金額不僅毫無疑問地位列第一,而且比之前所有處罰金額的總額還要高上一半(注:根據市場監管總局的資料,從2008年到2018年,反壟斷罰款總金額為110億元;而根據《中國反壟斷執法年度報告》,2019年和2020年兩年罰款總金額分別為3.2億和4.5億,也就是說在處罰阿里巴巴之前,中國反壟斷的處罰總金額大致上在120億元左右)。即使放在國際上進行比較,這次處罰的金額也僅次於2018年歐盟對谷歌的處罰,位列歷史第二。當然,和一個具體數字相比,這次處罰的象徵意義是更為重要的,它意味著我國對數字經濟發展的態度已經從“讓子彈飛”轉向了全面規範發展。長期以來被監管部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壟斷和資本無序擴張行為將會遭到全面的遏制。
果不其然,在對阿里巴巴的處罰之後,市場監管總局又陸續對各大數字經濟巨頭開出了一系列罰單,騰訊、美團等公司幾乎無一倖免。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系列處罰中,有一些罰單是針對現行的問題的,而另一些則是針對歷史問題的。比如,大量未集中申報的問題,就都在這一年統一被處罰了,可謂是補齊了歷史舊賬。
在反壟斷不斷推進的同時,與數字經濟相關的法律法規建設、部門規制也不甘其後。備受關注的《數字安全法》和《個人資訊保護法》先後於9月和11月實施,《網路資料安全管理條例》也公開向社會徵求意見。這標誌著巨頭們任意採集、使用使用者資料的日子從此一去不復返了。而工信部對巨頭之間互聯互通問題的介入,則表明了巨頭之間高築圍牆、以鄰為壑的局面可能也不會持續。除此之外,各部門關於演算法的規制,則給巨頭們利用演算法吸引使用者、誘導消費、進行“殺熟”的行為套上了緊箍咒。
在一系列的反壟斷和規制的組合拳之下,過去風光無限的數字巨頭企業都在2021年收斂了笑容。而它們的股價也集體開啟了跳水模式。到2021年12月31日,阿里巴巴的市值已經收縮到了3220億美元,相比於年初上榜時幾乎跌去了一半;騰訊的下跌幅度相對較小,但也比上榜時跌去了1/4,僅剩5628億美元。而對比之下,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數字巨頭們的身價則是一路暴漲。就在2022年的第一個交易日,蘋果的總市值就一度超過了3萬億美元。而緊隨其後的微軟、谷歌、亞馬遜市值也分別超過了2.5萬億美元、1.9萬億美元,以及1.7萬億美元。
面對中國數字巨頭的暴跌,以及與美國競爭對手之間差距的不斷擴大,“中國的數字經濟向何處去”就成為了人們關心的一個問題。從各大媒體上不難看到,現在有不少人對此的態度是比較悲觀的。在他們看來,隨著監管的不斷趨緊,中國的數字經濟在未來幾年內將會舉步維艱,這個本來足以與美國一較高下的領域很可能會就此一蹶不振。那麼,情況真的是這樣嗎?我想,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恐怕還要取決於我們究竟怎樣看數字經濟。
重新理解數字經濟
過去的二十年中,網際網路一直在中國的數字經濟版圖當中佔據中心位,因此當我們在討論數字經濟的時候,總是不知不覺地將它和網際網路經濟等價了起來。而眾所周知,網際網路經濟又是“數一數二,不三不四”的經濟,在自由競爭狀態下,只有頭部的一兩家巨頭才能生存,因此我們又下意識地把網際網路經濟等同為了少數的頭部巨頭。這樣一個邏輯鏈下來,數字經濟就等於巨頭,數字經濟發展就等於巨頭市值增長的觀念就不知不覺地植入了我們的心智。
但事實上,數字經濟當然不只是網際網路經濟,更不只是巨頭們的經濟。從廣義上講,數字經濟可以分為很多不同的領域。以在學界比較著名的Bukht和Heeks的分類方法,它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核心層,它指的主要是傳統的IT/ICT部門,包括軟硬體製造、電信等;第二個層次是狹義的數字經濟,它包括電子業務、數字服務,以及平臺經濟等;第三個業務則是廣義的數字經濟,包括電子商務、工業4.0、精準農業、演算法經濟等。按照國內比較流行的說法,那麼這裡的第一個層次大致上可以歸結為“數字產業化”,而第二、三個層次則大致上可以對應為“產業數字化”。
無論是在性質、地位,還是發展的方式上,數字經濟的以上三個層次都是有很大差別的。在三個層次中,核心層無疑是最為硬核,也最為重要的。在一定意義上,它可以被視為是第二、三層次發展的基礎。這個層次的發展,依靠的主要是技術的研發,只有掌握了相應的核心技術,核心層才可能被髮展得比較好。而第二、三層次呢,則是建立在第一層次之上的,是第一層次的產品的應用。和第一層次的發展主要依靠技術研發不同,這兩個層次的發展主要是依靠技術的應用和擴散。
在第二、三層次中,有一些模式的發展是極端依賴於規模的。比如平臺經濟、比如電子商務,這些模式的發展主要依靠數字技術開啟需求端,因此其發展就強烈依賴於市場規模,只有市場足夠大,平臺經濟才能夠壯大,運營平臺的企業的市值才能飛漲。我國目前的數字巨頭的業務,主要是集中在這些模式上。
但與此同時,二、三層次中還有一些模式,其規模效益是比較難以體現的。比如工業4.0、比如精準農業,雖然數字化也可以幫助它們大幅提升效率,但這種效率的增進主要體現在供給端。儘管從單個企業的角度看,引入數字化可以讓它們的成本大幅降低,利潤大幅提升,但由於沒有強大的規模效應和網路效應,因此數字化的總體收益在這些領域是比較低的。也正是這個原因,這些領域到目前為止,都不是數字巨頭們太青睞的領域——其中道理也很簡單,既然可以透過做大規模賺快錢,為什麼要花力氣去啃硬骨頭,掙辛苦錢呢?於是,數字化在這些領域的滲透水平就遲遲難以得到提升。
在有了以上概念之後,我們不妨把中國和美國的數字經濟進行一番對比。中國信通院在2021年9月曾經發布過一個《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對世界各國的數字經濟發展狀況進行過一個比較。結果顯示,在世界各國中,數字經濟體量最大的是美國,其2020年數字經濟的規模是13.6萬億美元;中國排名第二,數字經濟規模是5.4萬億美元,德、日、英分列三到五位,它們的數字經濟規模分別為2.54萬億美元、2.48萬億美元,以及1.79萬億美元。而從佔比上看,德國數字經濟佔GDP的比例是最高的,為66.7%,美國居於第二,為66%,第三是英國,為65%。而與這幾個國家相比,中國的數字經濟比重則要低得多,僅有38.6%。
咋看之下,這實在是一個令人震驚的結論。長期以來,我們一直以為,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是居於世界前列的,即使暫時和美國不能相比,壓過歐洲也是綽綽有餘的。從各種新聞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各種能夠佐證中國數字經濟發展高過歐洲的報道:比如,歐洲人會感嘆,中國的一個app可以同時完成很多功能,而落後的歐洲的一個app卻只會有一個功能;在歐洲,人們出門不得不帶著現金,很麻煩,而在中國,只要有一個手機就夠了;在歐洲,要進行網購,可能要很久才能送達,而在中國,網購不僅便利程度更高,而且成本也更低……而如果要比企業,那麼中國有阿里巴巴,有騰訊,有美團,即使在經歷了2021的暴跌之後,它們的市值也可以輕鬆地把歐洲的所有數字企業都比下去。怎麼在統計裡,德國和英國這些歐洲國家的數字經濟佔比就超過中國了呢?
問題究竟在哪兒?其奧秘,就在我們前面說的數字經濟的結構上。事實上,只要我們回味一下剛才指出的那些可以證明中國比歐洲更有優勢的數字經濟領域,就會發現它們都屬於第二、三層次中那些可以依靠規模迅速做大的行業。在規模這一點上,歐洲是無法和中國相比的。雖然從總量上看,歐洲的人口規模並不少,但是這些人口分散在幾十個國家裡。單從歐洲拿出任何一個國家,都很難支撐起一個像中國的數字巨頭那樣龐大的平臺,其類似的業務當然也很難發展。但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歐洲國家在發展數字經濟時,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對中小企業的扶持上,這使得它們在很多難以賺快錢的領域(如工業、農業等),反而率先普及了數字化。因此從總的數字經濟佔比看,它們反而要比中國勝出一籌。
然後我們再看看數字經濟的第一層次的中外比較。一比之下,我們就更清晰地看到,無論和美國,還是歐洲相比,中國在這一領域上都還存在著十分顯著的差距。美國自不用說,不僅數字經濟的歷次重大革命其源頭幾乎都可以追溯到美國,就從現實講,從晶片到作業系統、到主要的應用軟體,美國的企業都佔據了主導的地位。歐洲雖然在總體技術力量上無法和美國相比,但也掌握著不少關鍵的技術,比如荷蘭的ASML就是最重要的光刻機生產商,如果我們要生產自己的晶片,那就幾乎無法繞過ASML。相比之下,我國在關鍵技術的掌握上,就要弱得多。雖然如果從專利數量來看,我們的數字巨頭比起歐美的同行並不遜色,但我們的專利幾乎都是應用層面的,很多都需要它們的技術,也很容易被它們卡脖子。到現在為止,我們在晶片、作業系統等最關鍵的技術上,還在受制於人。不僅如此,甚至連主要的工業軟體,我們也不得不用國外的產品。其差距之大,不言而喻。
好了,經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就不難知道,雖然從數字經濟的總量上看,中國是世界第二,但在整個數字經濟版圖中,中國主要發展的是那些應用層面的產業,依靠的主要發展力量也是規模,而不是技術。如果任由這樣的發展模式進行下去,那麼雖然我們的數字經濟規模還可能繼續龐大,甚至有一天超過美國,但大而不強的問題就將繼續存在。而所有的一切,也都會和沙灘上的城堡一樣脆弱,一旦外部環境有變,就會迅速崩塌。
2021年,我國在數字經濟領域監管的驟緊,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其中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要透過監管引導我國的企業放棄那些“賺快錢”的低端玩法,逐步轉移到拼研發、拼技術上來,讓我國的數字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只有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可能看明白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數字經濟的可能發展方向。
未來去向何方
那麼,在拐點之後,中國的數字經濟究竟會何去何從呢?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恐怕要從四個方面來著手。一是從技術方面看,我們會取得怎樣的突破?二是從商業模式上看,我們可以實現怎樣的創新?三是從監管的層面看,會有怎樣的變動?四是國際環境究竟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1)技術變遷的方向
從根本上看,技術變遷是決定經濟發展的最本質動力。在數字經濟領域,這一點是尤其明確的。回顧過去幾十年,數字經濟的幾次起落,其實都和技術變遷的週期有著很大的相關性。網際網路的普及直接導致了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的這一輪數字經濟發展,而過去十多年的這一輪數字經濟大發展則是由移動網際網路的發展所帶動的。那麼,數字經濟要再次實現巨大的邁進,就應該首先有一輪技術的突破。
說到這裡,也許有人會說,在數字經濟領域,技術的創新幾乎是無時無刻不在發生的。幾乎每一天都有大量的技術被開發出來,有大量的技術專利被申請,難道技術會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一個問題嗎?
針對類似的提問,我想我們首先要對技術的分類有一個更深入的瞭解。技術和技術之間是不同的,有的技術可以被應用到所有的領域,而有的技術則可以被應用到特定的領域。在文獻中,前面一類技術通常被稱為“通用目的技術”(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簡稱GPT),而後一類技術則被稱為“專用目的技術”(Specific Purpose Technology,簡稱SPT)。一般來說,只有GPT可能成為重大技術變遷中的關鍵引領技術。只有它們,才能夠產生足夠大的“創造性破壞”,讓整個社會生產從既有的正規化裡走出來,徹底上一個臺階。而SPT則只能在它的基礎上錦上添花,在某一個方向推進效率的增進。
對照這一標準,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網際網路,還是移動網際網路,它們都帶有很大程度的GPT性質,其影響足以滲入所有的領域,有了它們作為“火車頭”來進行牽引,其他的SPT才有用武之地。但現在的問題就在於,下一個重要的GPT又在哪兒呢?
關於下一個重要的GPT,之前我們已經有過了很多的猜想。比如人工智慧、區塊鏈、5G,都曾經被認為可能會扮演這個角色。但至少到目前為止,這些備選項似乎都沒有發揮出曾經預想的作用。比如人工智慧的使用範圍倒是挺廣,但其對於既有技術基礎的“創造性破壞”作用並不明顯,更多還是扮演著SPT的角色。除此之外,由於現在的人工智慧走的主要是機器學習路徑,其對於資料的依賴十分強烈,因此可以預見,當與資料相關的各項規制越來越嚴格後,人工智慧的發展很可能迎來一個瓶頸。從這個意義上看,人工智慧應該不太會成為足以引領下一輪重大技術變遷的技術。區塊鏈呢,這幾年也有了一定的發展,但總體來說,其應用的普及是低於人們的預期的。其影響主要集中在“鏈圈”,似乎短時間內還很難普及到整個社會。至於5G,目前還有待進一步的普及,其效力還需要進一步的時間檢驗。多年前,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aylor Cowen)曾經預言過,現在的人們已經摘掉了技術發展之樹上所有“低垂的果實”,要找到下一個關鍵技術恐怕會很艱難。儘管我們不願意承認考恩的這個悲觀預言,但在檢視了幾個重要技術的發展狀況後,我們似乎不得不承認,至少在數字經濟領域,情況確實如此。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就是雖然我們短期內很難找到一個單一的關鍵技術來引領技術變革,但是卻可以依靠一個技術叢集來完成這一切。比如,現在“元宇宙”的概念被各方熱議,就是這一思路的集中體現。從技術角度看,要實現元宇宙,需要有眾多技術的協同發展。不少評論認為,所有的這些技術在其各自的發展過程中,都會遭遇各種各樣的瓶頸,但如果將它們集中在一個概念之下共同發展,就可以產生非常好的外溢和協同效果,實現共同推進。這個思路聽起來不錯,但究竟能不能走通,或許還要過一段時間才能看出。
具體到中國,我們面臨的問題可能還不僅是能不能找到關鍵技術,還包括這個關鍵的技術是否能為我所用。以現在的元宇宙熱為例。在支撐元宇宙的技術當中,有幾樣是十分關鍵的。首先是擴充套件現實技術,也就是XR(包括虛擬現實VR、增強現實AR,以及混合現實MR),這是進入元宇宙的入口。從表面上看,這類技術似乎並不難,但落實到應用上,卻有大量的技術細節需要處理。比如,VR對於延時的處理,VR外設的質量等,都會影響到其普及。而從現在看,最為先進的XR技術都掌握在蘋果、臉書、谷歌等幾大科技巨頭手裡,而中國企業在這方面的技術積累則相對薄弱。儘管從一定程度上,這個差距可以透過併購來部分解決(例如位元組跳動對Pico的收購),但一些核心的技術差距依然很難徹底解決。當然,和XR技術相比,晶片技術對於元宇宙的發展其實是起到了更為本質的作用。由於在元宇宙當中,需要大量的3D建模和實時渲染,所以對晶片的算力要求非常高。事實上,像英偉達這樣的晶片巨頭之所以能成為元宇宙的主要先鋒之一,原因也正在於此。遺憾的是,現在的晶片技術也依然都掌握在歐美髮達國家手裡,而我國在這個領域上則仍然是受制於人。如果這種局面繼續持續,即使用元宇宙這種技術複合體來拉動新一輪技術變革的設想是可行的,但我國的數字經濟究竟能不能在這輪變革中有自主性,能不能在其中足夠的利益,依然會是一個問題。
(2)商業模式的創新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中國之所以可以誕生這麼多世界級的數字經濟巨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充分利用了平臺模式的優勢。藉助平臺的連線,中國巨大的人口優勢就變成了強大的需求動力,正是這種力量撐起了一個個市值超過千億的公司。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雖然中國的數字巨頭和美國的數字巨頭幾乎都是利用平臺模式做大的,但細細比較之下就會發現,中美兩國的平臺是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的。總體上看,美國的巨頭雖然也搞多元化,但基本上只會有一個主攻的業務方向——亞馬遜主要做零售,谷歌主要做搜尋,蘋果主要做手機;而相比之下,中國巨頭們的業務則更為分散,尤其是頭部的幾家企業,幾乎所有的領域都能看到它們的影子,這兩年經常被提及的“資本無序擴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的這種現象。
應該說,如果單獨來看,中國平臺的多元化是有不少優勢的,它可以很好地利用各領域之間的協同來促進自身業務的發展。然而,如果所有的平臺都選擇了多元化,那麼就會陷入一個尷尬的“囚徒困境”。由於每一個企業都希望在短時間內實現在所有領域的破局,因此“重數量、重規模”就會成為發展的主要思路,而相形之下,技術的積澱就變得不那麼重要了。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雖然中國的很多數字巨頭在規模上曾經一度和美國的巨頭很接近,但比起硬核技術,卻要少得多。
除了以上現象外,還有一個更為關鍵的問題需要重視。那就是當所有的數字巨頭都迷戀著賺快錢時,一些需要慢功夫的領域卻被忽略了。應該說,現在我國在面向C端的應用,已經相當充足,甚至相當內捲了。但是,反觀面向B端的應用,尤其是面向工業、農業的應用,又完全是另外一個局面。前不久就有報道說,中國的大批工業軟體都是歐美的,工業企業的數字化還高度依賴歐美。這是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就是在工業領域,每一個應用的適用範圍都很狹窄,很難形成規模,平臺模式很難有用武之地,因此數字巨頭們都不太願意進入這些行業。
基於以上原因,在我國數字經濟的未來發展中,平臺模式可能會面臨一定的變革。一方面,過去一個平臺做所有領域的現象很可能會成為過去,類似於美國的相對專一模式可能會成為平臺的選擇。另一方面,除了平臺模式之外,我國或許還會醞釀出一些新模式,以推進工農業等實體經濟領域的數字化。
以我個人的理解,這種新模式很可能是一種模組化的組合模式。儘管每一個具體產業對於數字化的訴求是不同的,但這些訴求都可以拆解為一系列細分的具體需求。這些細分的需求通常會是通用性的,可以形成規模優勢。因此,如果每一個細分領域都能獨立形成一個產業,有幾個代表性的小巨頭企業,分別生產出各種數字化的元件,那麼當某個產業進行數字化時,就可以很輕鬆地購買自己需要的元件,來滿足自己的需求了。
(3)監管的走向
在考慮數字經濟走向的時候,監管當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在一連串的反壟斷重拳之後,2021年數字經濟領域的反壟斷可能進入一定的緩和期。但這背後的主要原因更多是因為很多重要的案件都已經在2021年得到了處理,相關的壟斷行為也得到了糾正,問題的存量已經大幅減少了。但是,跳出具體的執法層面,我國反壟斷的各項規章制度已經比一年之前遠為規範化、細緻化了,如果不出意外,《反壟斷法》的修正案也會於今年透過,這決定了要想回到過去的寬鬆階段,從制度上就不可能。
以上還只是反壟斷層面。事實上,正如前面所說的,在過去一年中,與數字經濟領域相關的《資料安全法》、《個人資訊保護法》等相繼出臺,各部門的配套制度也都陸續出臺,整個嚴監管的框架已經被鎖定了。因而綜合來看,如果不出特別大的意外,對數字經濟的嚴監管應該是未來幾年的主基調。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對於整個數字經濟行業來說,嚴監管未必就是不利的。固然,它可能讓一些數字巨頭在短期內遭受巨大的挫折,但從長期看,它是有利於幫助這些巨頭更好地認清方向,走出低質量的內卷的。不僅如此,在巨頭的力量遭到了一定的遏制之後,一些更新的企業就更有可能長起來,這對於繁榮整個行業生態也是有好處的。最為重要的是,在寬鬆監管的環境下,所有人都預期可能會有相應的監管措施出臺,因而做事會畏首畏尾。而現在,監管的靴子終於落地了,所有的企業都有了穩定的預期,這對於行業發展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4)國際環境的變化
在考慮中國的數字經濟走向時,國際環境這個外部變數也是不可忽略的。
一方面,這個因素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我們的數字經濟發展可以用哪些技術、不能用哪些技術。如前所述,目前中國的數字經濟有很多關鍵的技術都還掌握在歐美髮達國家手裡。舉例來說,行業內有一句著名的話,說現在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是“缺芯少魂”,這裡的“芯”指的就是晶片,而“魂”就是作業系統。除此之外,像XR等支撐元宇宙的關鍵技術,以及各種工業軟體,我國也都受制於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國際形勢真的有變,那麼中國的數字經濟就會面臨極為嚴峻的考驗。
另一方面,這個因素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的企業走出去。現在,很多的中國企業為了避免國內的過度內卷,已經積極選擇了將海外業務作為自己的重要發展目標。比如,阿里巴巴和騰訊在東南亞的投資,以及位元組的Tiktok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都取得了很好的業績。但是,這些業績都是以整個國際環境相對穩定為前提的。如果真的出現了什麼“黑天鵝”,那麼相關企業遭受的損失可能是巨大的。
結合以上兩點,個人認為,我國在發展數字經濟時,也必須做好兩手準備。從國家層面上,應當要做好隨時應對國外可能的“卡脖子”的預案;而從企業層面看,則應當權衡好對國內外資源的投放比例,努力做好收放自如。
結語
從任何一個角度看,現在的中國數字經濟都站在一個歷史的拐點上。究竟在這個拐點之後,數字經濟是會迎來新一輪的強勢發展,還是暫時陷入一個低谷呢?這恐怕還要取決於技術、商業、政策,以及國際環境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拐點之後的中國數字經濟一定會是和拐點之前完全不同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