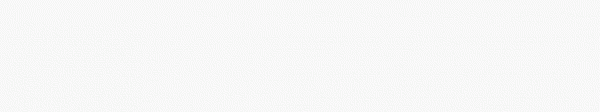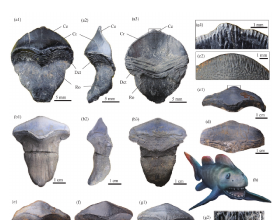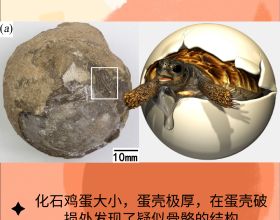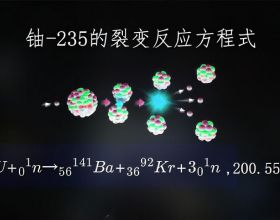本文來源於 真實故事計劃(id:zhenshigushi1),歡迎關注及投稿,符合者將獲得【1800元或2500元/每篇】稿酬。
今天故事主人公是一名在精神病院工作的護士。在她負責的病區,有超過60位女性精神病患者,這些女性受困於不健康的家庭關係,精神被撕裂,只得寄身於精神病院度日。
如同菜葉的孤獨晚年
病房位於醫院長走廊的兩側,沒有門,房間並不寬敞,裡面有四張床,排列整齊,床單被罩是統一的條紋色。所有病房裡擺放的都是女性生活用品,髮卡和頭繩,紅色拖鞋,花色襯衣,潔白的牆面看起來有些寒光。走廊的兩道大門緊鎖著,金剛網窗戶密密麻麻,站在走廊裡,不時能聽到一些女性歇斯底里的喊叫聲。
這裡不是一般的醫院,而是一所位於濟南市文化東路的精神病院。院裡有多個病區,我所在的病區有60多位女性精神病患者,工作7年來,看著她們進進出出,最多的時候達到上百位。在本地土著的黑話裡,我們醫院被叫作“馬家莊”。“你剛從馬家莊跑出來吧”,是當地人罵人的話。
生活中,人們對精神病院和精神病患者有太多誤解。影視劇看多了,有人會認為這裡的瘋子都關在鐵籠子裡,他們面目痴呆,會有瘋狂的舉動和陰謀,例如挖地道、翻柵欄逃走。其實這裡跟別的醫院沒多大區別,鎖兩道門是為了防止病人跑出去,窗戶安裝金剛網是害怕病人跳樓,病房沒有門,是為了方便觀察病人的情況。
上班的第一件事,我要挨個走進每一間病房,詢問病人情況,檢視護理記錄,點點人數。60多位女性患者中,年齡從十幾歲到七十幾歲不等,患的病也很雜,癔症、躁狂、抑鬱、精神分裂、人格障礙等等。每個人的臨床表現也不一樣:有的天天無理取鬧,要跟護士打架,這時候要把她們束縛在床上;有的不吵不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自顧自地胡思亂想。
病區裡住著一類退休的老年女性,她們因為退休後無所事事,加上離異或老伴去世,子女也不在身邊,一個人孤獨生活,久而久之便患上嚴重的抑鬱症。她們的面色毫無生氣,陷入一種人生的虛無,認為一切都無意義。
將近60歲的宋姨就在退休後生活踏空。她離異,女兒在國外,長期一個人生活。有段時間她一直躺在床上,身邊沒有朋友聊天,感覺很孤獨,什麼事也不想幹。從陽光高照躺到星月降臨,一天天過去,直到買的菜爛了,她才意識到自己患了病。
人生不該像菜一樣爛掉。宋姨用盡全身力氣從床上爬起來,當腳踩到地上的那一剎那,久違的腳踏實地的感覺從腳底傳到大腦。於是她出門把爛掉的菜丟到垃圾桶,就像把虛無的人生丟掉那樣,然後跨上電動車,戴上頭盔,瀟灑地來到精神病院。
宋姨是主動來我們精神病院的,這種情況非常罕見。她曾是位公務員,帶著眼鏡,看上去就像個文化人,精神狀態尚佳。她來住院那天我剛巧值班,負責在門口記錄病人資訊。平常其他病人都會有家屬陪護過來,而她隻身一人,騎電動車,下車後,揹著一個看上去能壓垮她的大包,手裡還拿著一個頭盔。
住院前要先體檢,於是我幫她登記、測體溫、量血壓,最後測心電圖時,我納悶地問了她一句:“你怎麼自己來的,老伴呢?”她躺在做心電圖的床上,對我苦笑了下,支支吾吾地說:“他有事,要照顧他媽。”心電圖室陷入寂靜,沒人再多問些什麼。
宋姨只在這住了十幾天,我們病房都挺喜歡她。她沒有什麼抱怨,也沒有過分的要求,我每次推著小推車到病床旁邊,她都會主動拿藥,用水送下去之後,跟我說一聲謝謝。遇到特別鬧的病人,她也不嫌煩躁,從不因此要求換病房。
直到出院她都是一個人,沒見過什麼親人來,也沒請護工,那個大包裡都是她自己置辦的生活用品。與多數病人相比,她的生活完全能夠自理,還能自己洞察到自己的病情,這讓她康復得很快。出院那天,她要回頭盔,說了一聲謝謝,然後騎著電動車瀟灑地走了。
她以主動出擊的方式,試圖挽救自己晚年的孤寂。
63歲的許老太是另一個極端病例。她患上的是陣發性狂躁症,元旦前住進來,做了兩次電休克,第二天才能走路。她有兩個兒子,一直是二兒子在這照顧她,老伴也癱瘓在家,由二兒子的媳婦照顧,大兒子則什麼都不管。許老太的病因正是源於他。
農村有句老話,叫“疼誰誰不中用”。許老太向來寵愛大兒子,寵得無法無天,今年大兒子偷偷用她的身份資訊抵押貸款,卻還不上,很快催債人到了家門,接著又收到法院的傳票,賬戶被凍結。許老太這才知道實情,一氣之下精神失常。她不吃不喝,身體木僵,躺在床上像植物人一樣,半夜又突然詐屍般坐起來,二兒子趕緊把她送來住院。
住院幾周來她的病情加重,身體持續木僵,肢體任人擺佈,睡眠欠佳,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在醫學上,這種木僵屬於心因性木僵,是精神運動性抑制的一種,一般是由嚴重的精神刺激引起。所以這些天,許老太的狀態可用“空氣枕頭”形容,就是把枕頭去掉,她的頭部仍然能保持懸空。
心病還需心藥醫,大兒子至今也沒出現。她病情加重了。醫生說,目前她的病情不容樂觀,需持續住院觀察,可能要在醫院過年。
困在婚戀中
作為精神病院的護士,我一天最重要的工作,是根據醫生下的醫囑核對藥物,為病人發放藥品,主要是精神類的藥。必須端著水,拿著藥,看著她們吃下去。這時候要小心著病人藏藥,她們有人會壓在口腔裡,故意不嚥下去,還有人故意吐在茶漏裡。吃完還要檢查一遍,讓病人張開嘴,拿棉籤按壓她們的舌頭。
偶爾,我會帶恢復狀態好的病人去康復科的院子遛遛彎,接觸新鮮的空氣和明媚陽光,能曬掉一些發黴的情緒,對病人康復有很大作用。剩下的病人留在病房餐廳,看看電視聽聽歌。
美子是我們院幾十年的老熟人,1986年就已住進來。她胖乎乎的,雖然叫美子,其實已經是中年的阿姨了。但她一直覺得自己是個小姑娘,管還不到三十的我叫護士姐姐。
她的病症是精神分裂,腦海裡都是天馬行空的想象,一見到我,她就會熱情地打招呼,讓我去她病床旁邊坐一坐。在她那簡單快樂的世界裡,她就是世界首富,天天要買東西,豪氣地說,從賬戶上扣錢。她還坐擁很多機場,每天就看著飛機起飛,吃飯的時候都要嘟囔著“123,123,飛。”
每次給她發藥的時候,她都說要給我們發別墅,獎勵我們兢兢業業工作。問她別墅在哪,她會樂呵呵地說:錢已經到賬了。
精神疾病很多都是由遺傳導致的,若是家庭中有情感性精神障礙、精神分裂的情況,則後代患有精神病的可能會大大增加。醫學專家們發現,如果父母一方患有精神分裂症,子女發病機率為15%左右,若父母雙方都患有精神分裂症,則子女發病機率在40%左右。
美子的病源於家族遺傳,發病於1985年。病史上寫著,1985年她與同學發生矛盾後,漸起病情,表現為敏感多疑,總覺得有人說她壞話,別人吐痰則認為是針對她。後來她開始無故自笑,言辭誇大,稱自己能考上清華大學,能當大官。1986年4月,她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首次住進我們醫院。
好在她有醫保供著,住院花不了太多錢。丈夫對她很好,經常來探望她,每次來都帶一箱奶、好多水果。在我看來她是幸福的,雖然出不了這裡的大門,她的思維早就飛出九霄雲外,在潔淨的天空中翱翔。
家族遺傳是內因,促使精神病患者病發的外在因素多種多樣,對於中年女性來說,婚戀問題是誘因之一。32歲的小高,曾分別於2009年、2010年、2012年三次光顧我們院。第一次發病是在她失戀之後,表現為暴躁易怒,半夜不睡,撕咬妹妹,被診斷為“癔症”。
結婚後她的生活並不愉快,2017年與丈夫吵架,她服下200片“利培酮”企圖自盡,及時送到醫院洗胃、輸液才算脫險。此後,她的生活並沒多大改觀,家人對她缺少必要的關心,與丈夫的矛盾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步。
有一次,她把丈夫從摩托車上推了下去,說是鬼讓她乾的,丈夫上輩子欠那個鬼很多。丈夫忍受不了這種生活,選擇與她離婚,幾乎同時她又被公司辭退。雙重打擊下,她出現言語紊亂、手舞足蹈的情況,於是再次被送來我們院。
住進來後她的病情一直反反覆覆,很難徹底根治,只能靠藥物維持。前夫沒來看過她,與美子相比,她還非常年輕,可未來卻是一片灰暗。
懷孕期間的女性情感相對脆弱,如果得不到足夠的關愛,很容易誘使病發。23歲的小趙與小高的經歷有些類似,她患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症,看起來有四十來歲,完全不像個青年女性。
2017年,她在妊娠期間與婆婆關係鬧僵後起病,敏感多疑,懷疑丈夫有外心,稱他與外面的女人有不正當關係,於是經常和他吵架。精神緊張的她不願工作,不願外出,很少與家人交流,長期服用一些藥物後,病情才漸漸穩定下來。
小趙來我們病房是因為病情再次加重。她每天無緣無故發呆,憑空自言自語,小聲嘟囔。問她在說什麼時,她回:“說丈夫的骯髒事。”
原生家庭的傷
來自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的資料顯示,我國有17.5%的人患有精神障礙,小到長期失眠、人格障礙、物質依賴、酒精依賴、安眠藥依賴,大到精神分裂。
針對不同的病症,精神病院提供的治療方法也各不相同,大部分是以口服藥治療,還有肌肉注射。當然還是會有電擊治療的應用,例如MECT(無抽搐電休克治療),就是病人在全麻的情況下,對大腦進行電刺激,導致其意識喪失。這種方式主要是治療一些嚴重抑鬱或狂躁症患者。楊永信那種懲罰式電擊治療,曾經也存在過,不過早就在精神衛生法頒佈後成為歷史。
精神疾病很多是由社會環境和心理上因素造成的,而這當中有一部分歸咎於原生家庭。
我們院不乏一些年輕女性。22歲的小卷,本科畢業於某醫學院,在實習期間被診斷為雙相情感障礙,於是辭職,來到我們院治病。她看似很合群,每天在病房指導別人吃什麼藥,說得頭頭是道。
其實,這是一種表演性人格。
實際上,小卷性格擰巴,不會表達任何情緒或者想法,舉動有時也很反常,那天她從背後突然一把抱住我,嚇我一大跳。還有一次,她早上準備去治療,要禁食,不能吃早飯。我們給她留麵包當早餐,可她卻偷別人麵包裡的防腐劑,揣在衣服口袋裡。害怕她會吞食異物,我們立馬找到她,她才拐彎抹角地說不想吃麵包。
病史上詳細寫著她的患病歷程。2015年患者與學校老師發生矛盾後起病,表現為情緒低落,少言少動,不願與別人交流,喜歡安靜獨處,時常哭泣。2016年,她開始在網上瀏覽消極資訊,用小刀劃傷手臂。大學期間,她開始悲觀厭世,研究自殺,上網查詢相關資料。去年十一月,她服下50片碳酸鋰,被家人送至醫院,經“輸液排洩”等搶救後脫險,同時,被診斷為“雙相情感障礙”。
小卷自我分析能力很強,認為自己的病是原生家庭造成的。她兒時是一名留守兒童,爸媽離異,由爺爺奶奶帶大,從小就缺乏爸媽的關心。她來的時候,整個小臂佈滿刀痕,這種自殘行為是為了引起他人的關注。
出院那天母親來接她,我們囑咐小卷要按時吃藥,她母親一副淡漠神情,衝我們說:“她自己知道吃什麼,別管了。”這話噎得我們無言以對,只能祝小卷好運。
由原生家庭導致的精神疾病,在孩童身上體現地更為直接明顯。前段時間,病房裡來了一個叫星星的小女孩,說是小女孩,其實已經上初中。但是她看起來只有七八歲,個子很小,乾瘦乾瘦的,眼神暗淡無光。
她父母離異,爸爸天天酗酒不著家,媽媽改嫁,已經有了全新的生活,爺爺奶奶偶爾拉扯她一把。在這樣家庭環境下,她的精神出現嚴重問題,不吃不喝,好幾天沒去上學。老師發現後,這才送來治療,被診斷為急性短暫精神障礙。
一住下她就成天大吼大叫,情緒很不穩定,吵著鬧著要回家找媽媽,不好好吃飯,水也不喝。家委會帶著果籃隆重地來看過她一次,也就是覺得她可憐,此外沒有其他人來過。
有一天我來到她的床邊給她喂藥,她說什麼都不吃,開始歇斯底里地罵人,坐在地上扯著頭髮,我也沒辦法控制住她。我生氣地罵了她一頓:“星星,你冷靜一點,世界那麼大,有趣的事情那麼多,你就在這裡自暴自棄?你十幾歲了,難道要一直靠別人可憐活下去嗎?”
她愣住了,一直沒有說話,可能從來沒有人這樣說過她。過了一會,她默默地把藥吃下去。
我一時衝動,可沒想到這麼一罵還真起作用了。她變乖了,後面幾天開始按時吃藥,吃飯。我偶爾也能跟她聊聊天,講講故事,或者陪她看看她喜歡的恐怖片。每次她的雙眼都撲閃撲閃地盯著我,像她的名字,星星,直抵人心。
這樣住院住了一個月,星星的情緒趨於穩定,也該出院回去上學了。臨走那天,她蹦蹦跳跳地向我跑過來,說:“謝謝你,護士姐姐,這段時間我真的很溫暖,很開心。”鬧著要我抱抱她,我完全被她觸動到了,給她一個大大的擁抱。
走的那天,是媽媽來接的,這對星星來說非常重要。這意味著她有一天可以和媽媽相處。我在心裡默唸,願她不要再來這裡。
*本文根據當事人口述撰寫,人物有模糊
- END -
撰文 | 亓自牧
編輯 | 吳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