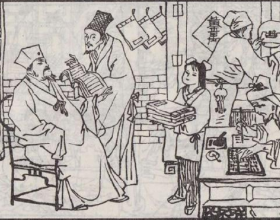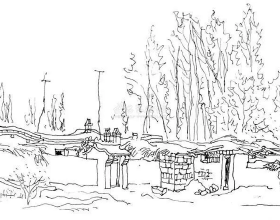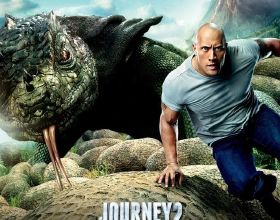作者:小呀小貓咪
著作權歸作者所有。商業轉載請聯絡作者獲得授權,非商業轉載請註明出處。
我是前朝公主,被囚禁在這裡已經有三個月了。
1
我在朱鸞殿發了好大一場火。
地上滿是破罐碎瓷,宮娥內侍在殿前戰戰兢兢跪著,我懷孕四月,根本無人敢上前阻攔,最後還是序昭聞訊而來,才安撫下我的情緒。
他一身大內總管繡金玄服,立在殿前仰面喚我:“長福殿下。”
我終於洩氣,跌跌撞撞走向他,撲進了他的懷裡。我問他:“陸晏為何不見我?”
序昭如兒時那般溫柔地撫摸我的鬢髮,頓了半晌,才輕聲回道:“皇上政事繁忙……”
“都是藉口!”我用力推開他,癲狂地站起身,“因為我是前朝公主,所以我肚裡這孩子就是前朝餘孽……”
序昭猛然傾身捂住我的嘴,我望著他,淚水決堤而下,浸溼了他溫熱的掌心,緩緩流入我口中,苦澀異常。
我探出雙臂,在滿室寂靜中抱緊了他,哽咽道:“序昭哥哥,我不想做皇后,我只想做長福。”頓了頓,我又道:“我想父皇母后了,可如今我只有你了,只有你了……”
我已經很多年都沒有這樣叫序昭了,當真是太多年了。
隨著日子不斷消散的,除了我日漸衰敗的身體,還有我對故國的記憶,那些或繁花似錦,或滿目瘡痍的記憶。
我是前朝大元的長福公主趙玉瑾,皇后唯一的嫡女,自出生起便享受了整個大元朝最尊貴的待遇。
父皇賜我封號“長福”,希望我此生都能福喜安樂,他待我比一眾兄弟姐妹都要好,打從我記事起,便能破例在頤安殿陪他批閱奏摺。
有回幾位大臣找父皇議事,我坐在一旁聽著聽著便睡著了。
醒來時天色已暗,頤安殿內燃起燭火縹緲,父皇坐在案臺前的身影偉岸模糊,我軟軟叫了一聲:“父皇。”
他看向我,笑著朝我走來,將我抱在懷裡高舉兩下,又捏了捏我的鼻子:“朕的小長福終於醒了。”我被他逗得咯咯直笑,就伸手拽他鬍子,與他鬧作一團。
那些稀疏平常的美好日子,在漸漸遠去的時光裡,彷彿早已變作大夢一場。
我遇見序昭,是在七歲那年的盛夏。
夏雨將歇,我那貪玩的三皇兄拉我到御花園挖蟬蛹,他在幾個兄弟間最是平庸,我父皇常罵他胸無點墨,他卻不在意,仍是好玩多動,只是怕受罰,每次都要拉上我。
我正值頑童年歲,對他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兒也頗感好奇,便陪他蹲在林子裡挖小洞,不多時,就挖出了許多蟬蛹。
可就在這時,我聽到一陣低聲嗚咽。
“誰在那兒哭?”我問。
三皇兄丟掉手裡鏟子起身往林子裡走去,回來時告訴我:“一個小太監,估計是受了委屈,不用管,我們繼續挖蟬蛹。”
我沒聽他的,拎著裙子便往林間跑,隔著重重樹影,就看到一個單薄的少年坐在一塊石頭上,正掩面而泣。
他的脊背很直,顯得身子瘦削如竹,我悄然走到他面前,問:“你哭什麼?”
他被我嚇了一跳,慌亂地望向我。
四目相對時我愣了愣,即便生於宮中,我也從未見過這般好看的人,他面板瑩白眉眼細長,唇色如三月桃花,淚眼婆娑時,竟讓人一時難辨雌雄。
他忙跪到地上,不安回道:“衝撞了貴人,是奴才的大錯。”
我回過神,蹲下身子好奇地看著他,又問了一遍:“你哭什麼?”
雨後的林間氤氳著泥土的潮氣,他愣愣抬頭,漂亮的眼眸閃著碎光,良久都沒有回我。
後來序昭同我說,那日我蹲在他身旁問他哭什麼的時候,黑白分明的瞳仁毫無雜質,一身華服宛如神祇,他說,入宮後,便再沒人那般關切地詢問他了。
可那日直到最後,序昭也沒有告訴我他為什麼哭,也是從那日起,大元長福殿下身邊,多了一位名叫序昭的內侍。
我也不明白自己為何會將他帶回朱鸞殿,興許只是不想再在他漂亮的容顏上看到淚水。
他比我年長七歲,又是謹小慎微的性子,將我照顧得妥帖周到。好像自他來到我身邊後,我便鮮少犯過大錯。
他像我的影子,又像我的日光。
後來我纏著序昭偷偷叫他哥哥,他正為我沏茶,聞聲後手中玉壺驟然摔落。
那是我第一次在序昭平靜無波的面上看到惶恐,他說:“殿下是主,序昭是奴,雲泥之別,萬不可以親人之稱相喚。”
可我卻毫不在意,直到某次我喚序昭“哥哥”時被二皇兄聽到了。
二皇兄仗著母妃靜妃受寵,在宮中向來跋扈橫行,藉此為由揹著我重重杖責了序昭。
我得到訊息趕去時,序昭已奄奄一息躺在地上了。
夕陽餘暉自天邊縹緲而下,我踉蹌著撲到序昭身邊,大聲哭喊著讓人去尋太醫。鮮血滲透衣裳沾滿我的雙手,殷紅刺目。
序昭緩緩動了動唇,我貼近他,才聽到了那細小的聲音。他說:“奴才血汙,殿下莫要髒了衣裙。”
我握緊他的手,淚水大滴大滴滑落,那時我偷偷發誓,我在宮中一日,便護序昭一日,絕不讓他受半分疾苦,哪怕日後我嫁出宮外,也定要將他帶到夫家,享一世榮寵。
2
可我再也沒等到嫁出宮外的那日。
陸晏起兵造反時,我父皇根本沒有半點防備。
陸家世代守衛邊疆,忠心耿耿為國盡瘁,那時誰都沒想到,西北的兵權剛剛交到陸晏手中,他就敢揭竿而起,率大軍從西北一路直搗京城。
父皇遣人前去迎戰,卻沒有阻擋陸晏半分,西北大軍殺進京城那日,父皇以一根白綾結束了生命。
他是個好父親,卻不是個好皇帝,他根本沒有勇氣去面對這已經滿目瘡痍的江山社稷。
皇帝已逝,宮中更是亂作一團,自盡的自盡,逃命的逃命,宮人們搶奪殿中最後的財寶,妃子們跪在地上號啕大哭,那一日,我彷彿看到了人間煉獄。
我被序昭拉著躲進朱鸞殿的偏殿,縮在他懷中瑟瑟發抖,他溫暖的大掌輕輕闔上我的雙目,道:“不要看,很快就會過去了。”
黑暗中,我的淚水浸溼了序昭乾燥的掌心。
陸晏破城,定會將皇族趕盡殺絕,父皇不在,更無人能保我,不管是我母后,還是無能的三皇兄,亦或是恃寵而驕的二皇兄,他們都不會活下來。
我抱緊序昭,貪戀這一生最後的溫暖,低聲喃喃道:
“如果有來生,我們就變作尋常人家的兄妹吧,你扛著鋤頭在地裡種田,我走在田埂間為你送飯,我賀你娶妻生子,你揹我出嫁為婦,一生福喜,兩人安樂。”
序昭雙臂微微用力回抱我,輕聲回道:“我們會活下去的。”
陸晏留下了我的命。
整個大元皇室,他只留了我一人。
我被人押著跪在長興殿前,鼻端盡是鮮血腥臭的鐵鏽味,我只覺一陣陣噁心,卻還是倔強地昂起頭顱。
我是大元的長福公主,即便是死,也不能丟了皇家顏面。
眾兵擁簇陸晏走出長興殿,他一身銀白鎧甲,手持長槍,居高臨下地望著我。
我以為我會破口大罵,再不濟也要朝他吐一口唾沫,可在他出現的那一瞬間,我只覺得害怕,原來大義赴死,並非所有人都能坦然面對。
陸晏一步步朝我走來,待他行至面前時,我已然渾身冰冷。他頓了頓,突然笑了一下,問:“你就是長福?”
我沒有回答,他猛然掐住我的下巴迫使我抬頭,四目相對,我終於看清了他的面容,就如我所想一般冷硬粗獷,不同的是,眉目間多了幾分輕佻。
他戲謔道:“長得真好看。”
我沒想到他會這樣說,一時愣住,就聽他又說:“長得這樣好看,給我這新帝做皇后怎麼樣?”
我只覺得諷刺至極,狠狠掙開他的禁錮,怒道:“做夢!”
陸晏也不惱,只風輕雲淡地笑,在他輕蔑的目光中,我只覺得自己所有的抵抗都像是困獸最後無用的掙扎,整個人狼狽不堪。
“做夢?”他笑,“那我們便拭目以待,看看我是否是在做夢。”
我仰面望向他,只覺得幾近窒息。
大元已亡,我一個前朝公主,早就是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魚肉。更不要說陸晏即將稱帝,我是生是死,都在他一念之間。
3
我還是穿上了皇后的鳳冠霞帔被扔進新房。
陸晏登基,改國號齊。
我明白陸晏為何會要我做皇后,他師出無名,亂臣賊子的身份天下皆知,為了名正言順地坐上皇位,他便留下我——大元皇族唯一的血脈。
若日後我有了身孕,他的孩子也流淌著大元皇族的血液,就能堵住天下人悠悠之口。
可我又怎能讓他如願。
我用藏著的一塊碎瓷片深深割進手腕,隔著寬大殷紅的衣袖,根本沒人注意到,直到鮮血浸透裙襬蜿蜒流至腳下,才有幾個內侍慌忙按住我的傷口。
陸晏發了好大一場火。他是個骨子裡就透著暴虐的人,根本沒理會那幾位內侍的求饒,便命人將他們拖出去杖斃——看管不善,這就是唯一的理由。
我虛弱地躺在床上,殷紅嫁衣沿著床邊逶迤而下,陸晏捏著那塊瓷片居高臨下地望著我,冷笑道:“想死?可你這樣根本死不了。”
他猛然拽起我受傷的手腕,我痛呼一聲,就聽他又說:“這裡的血很快就會凝固,你若想死,不如直接割這裡。”他將冰冷的瓷片慢慢移到我脖頸跳動的血脈處。
“割這裡,血流如注,片刻便死。”
不知是失血太多還是過於害怕,我只覺渾身冰冷,片刻沉默後,瓷片“啪”一聲被陸晏狠狠扔到地上,他捏住我的下巴,眼神陰鷙,語氣冰冷:“趙玉瑾,再有下次,我讓整個京城的百姓給你陪葬。”
我對他的話沒有絲毫懷疑。這人暴虐嗜血,皇族都能屠盡,更不要說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
一種深深的無力感將我包圍,我只是笑,笑出了眼淚,又咳出殷紅鮮血。
我說:“陸晏,千年來暴君沒有一個好下場,你一定也不例外。”
他怒極反笑,輕輕拍了拍我的臉:“那我們便拭目以待,看看我有沒有好下場。”
又是這句話。
我只覺得五臟六腑都在扭曲,痛得喘不上氣,陸晏終是拂袖而去,留下殷紅喜房裡的一片狼藉。
我被迫委身於滅族滅國的仇人,還不能輕易尋死,巨大的痛苦日夜折磨著我,我很快消沉下去。
一日,我坐在梳妝檯前任宮人給我梳頭,銅鏡裡的臉無悲無喜,蒼白得嚇人,鏡中忽然出現另一個人的面龐,我倉皇起身,打翻了妝奩裡擺放整齊的步搖,踉蹌地朝那人懷中撲去。
我趴在他懷裡,淚水洶湧而出,嗚咽喚他:“序昭哥哥。”
我以為他早就死了,死在了陸晏破城那日,可如今他卻好端端地站在我面前。
我雙手攥緊序昭的衣袖,手下的布料精緻輕柔,這時我才發現,他身上穿的是大內總管的服飾。
我愕然望向序昭,就聽他低聲道:“新皇恩典,留下奴才……”
陸晏恩典?為何恩典?我猛然想到什麼,伸手顫抖地撫上序昭清雋的容顏,渾身血液彷彿逆流。
生在宮中,我怎能不知那些龍陽斷袖的腌臢事兒?
陸晏為人陰晴不定,保不齊有什麼怪異癖好,我伸手攥住序昭衣襟,一寸寸收緊,啞聲問他:“陸晏要你做什麼……”
“什麼都沒有。”序昭清澈的眼睛早已看透我的想法,“放心,殿下。”
我長舒一口氣,卻還是疑惑,為何陸晏會留下序昭,還讓他做了大內總管?
可這些疑惑統統被重遇序昭的喜悅衝散。我拉著他的手,像怎麼都看不夠,我說:“真好,我們都活下來了,序昭哥哥,真好……”
那時我還天真地以為,在這飛簷拱柱紅牆綠瓦的冰冷皇宮中,他會是我唯一的溫暖。
此後序昭常抽空陪我,我不知他在陸晏身邊過得怎麼樣,總怕他受傷委屈。
日子久了,我發現似乎是我多慮了,陸晏沒有為難,序昭過得很安穩,大內總管的身份,更無人欺他。
夏至,我們如兒時那般在御花園裡相攜漫步,這裡草木山水似乎沒有任何變化,可滄海桑田,天下已經易主。
我拉著序昭走進一處林子,行至一塊石頭前,我仰面問他:“當年我遇到你時,你為何坐在這裡哭?”
他望著我,清涼夏風吹散淺淺燥熱,良久,才回道:“那時我從家鄉得到訊息,我的母親得了重病。”
“那她現在可還安好?”我猶豫問道。
“已經逝世了。”
氣氛一瞬間彷彿凝結。我伸手緩緩握住序昭長袖下的手,想要轉移話題:“你還從未提過你的家鄉呢,不知你家鄉在哪兒?”
可這句話似乎又觸及了序昭傷心之處,他沒有回答,只抬頭望向遠處繁花似錦鬱鬱蔥蔥的夏景。許久,才喃喃回道:“我的家鄉……在西北……”
我微微一愣。
“我也記不清了。”序昭轉身望向我,夏風吹亂他鬢角髮絲,“我很小就被家人賣到京城了,關於家鄉種種,已經模糊了。”
我抬手撫平他鬢邊髮絲,緩緩靠在他懷裡,輕聲道:“沒關係,從此之後,我們便是家人,你是我唯一的哥哥,我是你唯一的妹妹,我們都要活下去。”
良久,才聽他聲音悶悶回道:“好。”
那時我根本沒有覺察到任何不對,也不明白序昭隱瞞了些什麼,我只知道,序昭讓我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
不管滄海桑田,不論山河已變,只要序昭還在,我遠遠望見他,便只想活下去。
活下去,哪怕我已經嫁給了滅國滅族的仇人。
4
可陸晏的所作所為,卻讓我看不明白。
他給我皇后應有的尊貴和禮遇,賞賜恩典從未斷過,隔三差五便宿我宮中,還在一眾宮妃面前對我舉止親暱。
可我們之間又橫亙著血海深仇,我只當他是做戲給旁人看,直到那個初秋的深夜。
那夜我早早便睡下了,卻聽到有人通報皇上來了。
陸晏喝得醉醺醺地闖進殿內,跌跌撞撞走到床邊,一把將我從錦被裡撈出來擁進懷中,頭軟軟靠在我的頸窩上。我驚呼一聲,耳側傳來他低沉的聲音。
他問我:“玉瑾,我封你為後,給你錦衣玉食榮華富貴,讓你寵冠後宮,可你為什麼還是不高興?”
我的心一點點沉下去,冷聲回道:“我沒有不高興。”
他突然直起身看著我,鼻尖幾乎與我相碰,往日深沉的眼眸透著迷茫,良久,才低聲喃喃道:“可你從來都不對我笑。”頓了頓,他又道:“你只對序昭笑。”
我譏諷反問:“原因難道你不清楚嗎?”
我張張嘴,又想再說些什麼,卻被陸晏突然傾身吻住。他的唇冰冷,呼吸間盡是酒氣,不知為何,我的淚水突然決堤而下,順著臉頰流進嘴裡,苦澀異常。
寒涼秋風猛地吹得窗戶“啪——”一聲大開,屋內燭火搖曳後隨之熄滅,悽白月光透過窗欞漫進屋內,黑暗中,我只能依稀看清他亮得出奇的雙眸,彷彿是空中星光,自始至終閃爍明亮。
這眼神讓我感到害怕,就好像我無意間窺探到了陸晏的秘密,那讓我感到不安和痛苦的秘密。
這個秘密,在之後的中秋宴上徹底明朗。
中秋佳節,月如銀盤,宮中一派沸反盈天的喜慶氛圍,我面無表情地坐在陸晏身旁,自始至終都如置身事外。
起先宴席上都是君臣和氣的場面,座下群臣大多是陸晏在西北時的舊部。
酒過三巡,有人膽子大起來,吵吵嚷嚷地說起了我:“如今天下民心已定,皇上身邊的體己人,當是知根知底的才好。留些至貳姓之人,怕是私藏禍心啊……”
陸晏自始至終都在笑著,頭頂驟然亮了半邊天,我仰頭望去,大朵大朵煙火在夜空炸開,火樹銀花,絢爛輝煌。
出神時,左手忽然被人握住,我將視線下移,焰火的光斑太過灼亮,我們交握的雙手隱在桌下只能依稀看到剪影,不知為何,在這喧鬧沸嚷的宴席裡竟透出一股寂靜相守的安寧祥和。
陸晏的笑容一直沒變,直到頭頂焰火停歇,他的臉才慢慢冷下來,沉聲問:“御林軍呢?”
宴席上的大臣面面相覷,兩名御林軍遵命上前,陸晏笑了笑,指向剛剛那位影射我的大臣,冷聲道:“拖下去,杖責。”
眾人噤聲,連大氣兒都不敢喘一下,不遠處傳來那位大臣鬼哭狼嚎的聲音,沒過多久連慘叫聲也沒了,只有杖板拍打在皮肉上的揪心聲音。
誰都沒想到陸晏會這般護著我,滿席肅靜中,他輕笑著貼近我,安慰道:“不要怕。”
可我還是怕,怕到渾身發抖,在陸晏盈滿笑意的雙眸中,我終於徹底明白了他的秘密,連同整個宴席上的朝臣也讀懂了這個秘密。
陸晏心裡有我。
原來他給我錦衣玉食,讓我寵冠後宮,並非是讓我成為眾矢之的,而是因為,他心裡有我。
可我根本不知道,陸晏究竟是何時將我放在心上的。
我猛然想起,曾有一年冬至,他攜一束紅梅冒雪來我宮裡,我藉故發難,將那束隨意扔到地上。
我以為他會拂袖而去,卻不想他只是輕輕笑了笑,將紅梅從地上撿起,望向我的眼神悠遠而綿長。
他說:“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原來從那時起,他心裡就已經有我了。
我本以為可以無悲無喜地過完此生,哪怕為了苟活委身於仇人,哪怕我早就對不起大元的列祖列宗。
可陸晏的心意讓我日夜難安,我開始整夜整夜失眠,偶爾睡去,夢裡也盡是破城滅國那日的慘狀。
我不敢再睡著,怕在夢裡遇見父皇母后,怕他們質問我,被仇人裝進心裡是否感覺十分欣喜?
我想讓陸晏也恨我,就如我對他滔天恨意那般,好像只有這樣我才會覺得良心稍安。
這個念頭像毒蛇一樣在我心頭瘋狂纏繞,等我回過神時,已經任由心中惡念肆意蔓延把我變作一個狠毒的婦人。
我將陸晏的一個宮妃從朱鸞殿前的百尺玉階上推了下去。
她懷孕五月,滿身是血地躺在臺階下,我縮在廣袖下的手顫抖不已,將淚水狠狠憋了回去,我知道她的孩子一定保不住了,我造的孽,來生來世必要為這個孩子還債。
這是陸晏的第一個孩子,他聞訊從頤安殿匆匆趕來,驚慌失措地抱起那個宮妃,大聲喚著太醫,我望著他倉皇的模樣,竟惡毒地感到一陣報復的快意。
可自始至終,他都沒有抬頭看我一眼。
5
我被陸晏關了禁閉。
謀害皇家血脈,這已經是陸晏給我最輕的懲罰了,這懲罰讓我日夜難安的內心平靜不少。
父皇母后雖不再入夢,可當我再閉上眼,卻總能聽到孩童嬰兒一聲聲的啼哭,那哭聲逐漸尖利,如斷頭臺上鋒芒畢露的鍘刀,一下又一下凌遲著我早已脆弱空洞的精神。
雪上加霜的是,在朱鸞殿禁閉的第二個月,我被查出了身孕。
那時將要入冬,序昭偷偷過來看我,兩月未見,我所有委屈都在見到他的瞬間爆發。
我蓬頭垢面消瘦不堪,縮在他懷中肆無忌憚地落淚,訴說我的惶恐不安,懺悔我犯下的罪過。序昭溫柔地為我拭去眼淚,輕聲道:“若有來生,這些罪過都放在奴才身上,讓奴才替殿下受罰。”
我淚眼朦朧地搖頭,就聽他又說:“這是奴才欠殿下的。”
寒風從堂前穿過,吹亂我滿頭青絲,恍惚間我看到其中幾根銀髮,未等嘆息,便只覺一陣頭暈目眩,捂住心口低頭乾嘔幾下,眼眶鼻腔酸澀不堪。
痛苦間,我哽咽道:“序昭哥哥,我難受,我好難受……”
待我抬頭看向他時,他望來的目光悲慼而絕望。他問我:“你這般乾嘔……有多久了?”
我突然沉默下來,滿室寂靜中,只有窗外寒風嗚咽不停。
這沉默直到太醫匆匆趕來後才被打破,滿頭白髮的老者跪在我面前,一聲聲賀道:“恭賀皇后娘娘懷子——”
在宮人們此起彼伏的恭賀聲中,我緩緩起身,一步步走到序昭面前,啞聲問他:“我懷孕了,能讓陸晏來見我嗎?”
序昭沉默著,良久,才答道:“好。”
可直到深冬,陸晏也沒來見我。
我的惶恐不安隨他的冷落逐漸加深。
如今陸晏登基兩年,手段雷霆暴虐,震懾四方,沒有人說他出師無名,更無人因此起兵造反。
他當年封我為皇后的理由似乎早就已經沒有了意義,而我又在此時懷有身孕,若他不喜,隨時可以除掉這個流淌著前朝血脈的孩子。
我不斷地發火,朱鸞殿裡瓷瓶瓦罐早就被摔得乾淨,序昭來過數次,可每一次都沒有帶來陸晏,我問他陸晏為何不來,他只是安慰我說皇上政事繁忙。
懷胎五月時,我的肚子已經明顯凸起了。
可我瘦弱的身體好像根本無法給肚裡的孩子充足養分,整日被他折騰得寢食難安,加上陸晏冷落不見帶來的憂慮,我日漸消瘦,什麼都吃不下。
直到那日隆冬大雪,序昭又來看我。
我正躺在貴妃榻上小憩,聽到動靜起身趿拉著鞋就往外殿跑,可只有序昭裹著一身寒氣掀簾而入,陸晏並沒有來。
我苦澀笑了笑,轉為欲序昭備一杯暖茶時,忽然發現他手中拎著一個食盒。
序昭從食盒中取出一盅湯,緩緩倒入一隻玉碗中朝我遞來,道:“殿下身子虛,奴才特向太醫署求來養胎湯。”
我毫不生疑接過玉碗,將飲入口時,刺鼻的藥味讓我忽然頓住,恍惚間記憶回到六歲那年。
父皇一位有孕的宮妃被人下了落子湯,我隨母后去她宮中探望,那個女人絕望地臥在床上,我早就記不清她的模樣了,可那滿屋刺鼻的藥味卻如夢魘般,深深刻在了我的記憶裡。
那遙遠的味道與面前這碗湯藥逐漸重疊,我木然抬起頭,怔怔望向序昭,問:“這到底是什麼?”
許是我的目光太過蒼涼,序昭愣了一瞬,才沉聲答道:“養胎湯。”
玉碗被我重重摔到地上,碎玉迸濺湯汁飛起,我衝向他,雙手緊緊攥住他的衣襟,嘶吼道:“為什麼要這樣對我,為什麼要害我的孩子?!”
序昭猛然跪下。
這是我此生第二次在他平靜無波的面上看到惶恐。
我渾身冰冷地癱坐到地上,雙手顫抖著捧起序昭蒼白的面龐,啞聲問他:“為什麼?”
我不想落淚,也不願在他面前露出脆弱的神情,可溫熱的淚珠爭先恐後地滑落面龐,一滴滴洇溼了衣裙。
他望著我,清澈的眼眸漸漸蒙上溼意,伸出手一點點覆上我的雙眸,一如亡國那日。
黑暗中,我聽到他哽咽的聲音:“皇上說,留子去母,留母去子,殿下,你要活下去……”
窗外落雪寂靜無聲,殿內地暖燒得正旺,我的淚水不斷洶湧,直至號啕大哭。
我縮在序昭懷中,嗅著他身上熟悉的味道,心中好像有什麼漸漸坍塌崩裂,隱秘在內心深處的情感徹底爆發。
我探出手指一點點撫上他冰冷的唇,滿室沉寂中,絕望而痛苦地吻了上去。
6
我的孩子沒了。
我沒有喝下序昭的落子湯,可在他走後的那個雪夜,我趁宮人已經歇下,跳入朱鸞殿院後的青波湖裡。
大雪紛飛,黑暗冰冷的湖水很快將我淹沒,我不會放棄這個孩子,亦不相信我離開後陸晏會善待他,我摒棄了一切顧慮和擔憂,只想帶著他一起離開。
可我卻獨自一個人活了過來。
從朱鸞殿雕花大床上醒來時天已大亮,宮人內侍戰戰兢兢地跪了一地,我顫抖著撫上已經平坦的小腹,怔愣良久,直到陸晏裹一身寒氣匆匆而至。
我與他已數月未見,可再見面時,他只是站在床前冷笑,道:“趙玉瑾,這可能就是報應吧。”
我害死了他的第一個孩子,不怪他這樣說,所以我只垂下頭,什麼都沒有說。可他卻忽然上去捏住我的雙肩,掐得我生疼。
“你的孩子沒了!你難道一點不難過嗎!?”他朝我吼道。
我低垂著頭,苦笑一聲:“當然難過,可難過又有什麼用呢?”
“趙玉瑾,如今你的痛,便是我當初的痛。”
我怔愣望著他,啞聲問:“如果留下這個孩子,我不在了,你會好好對他嗎?”
“不會。”他冷聲答道。
我終於瞭然,這才是我認識的那個殘暴無情的大齊新帝陸晏,所以我輕聲笑了笑,在沉寂殿中透著幾分悽慘。
我說:“陸晏,你還真是個冷血的父親。”
嘩啦——
一旁玉瓶被陸晏推倒在地,碎瓷迸濺,聲響刺耳。我下意識側開臉,卻還是看到了他冰冷悲慼的眼神。
他上前攥住我衣裳的前襟,一寸寸收緊,雙目通紅,言辭間卻皆是狠意。他問我:“趙玉瑾,這也是我的孩子,你當真以為,我不會難過嗎?”
我木然地垂下頭,又聽他繼續道:“我剛剛坐穩帝位,若你此時誕下龍子,那些已經隱忍不發的前朝舊臣又將蠢蠢欲動,這些,你當真不知道嗎?”
“便是知道,又能如何?”我冷笑道,“我是前朝公主,而你是新朝皇帝,是我滅族亡國的仇人……”
我仰頭望向他,聲音寒涼:“所以,你應當殺了我,以絕後患……”
陸晏神情一頓,而後甩開我的衣襟,冷哼一聲,問道:“你死了,就不擔心序昭嗎?”我愕然望向他,又聽他繼續問:“在你心裡,序昭到底是什麼?”
我垂下頭,雙手攥緊錦被:“他是我的哥哥。”
“哥哥?”陸晏冷笑,“你皇兄眾多,怎不見你主動親吻任何一個哥哥呢?”
我如遭雷擊。
“趙玉瑾,你可知道序昭姓什麼?”陸晏不懷好意地望著我,故意拉長尾音,一字一頓道:“他姓陸。”
7
我找到序昭時,大雪已經紛飛了數日。
目光所及之處皆是一片慘白,我冒雪前去,狼狽地撞開他的房門。序昭正在房中飲茶,見我前來慌忙放下茶杯上前,問:“殿下怎麼來了?”
他伸手為我拂去身上碎雪,口中唸叨著我不仔細身體,我始終沉默,許久之後,他終於察覺不對,抬眸望向我。
我想一定是我的眼神太過冰冷和狠毒,四目相對時,序昭忽然怔住,良久,他像終於鬆了一口氣,目光蒼涼地問我:“你……殿下都知道了?”
啪——
隨我右掌重重落下,他臉龐隨之微偏。我往後退了幾步,身形晃了晃,突然大笑起來,笑著笑著淚水便洶湧而至,我癱坐到地上,哭得聲嘶力竭。
如果不是陸晏告訴我真相,恐怕我此生都要活在序昭為我編織的美夢裡。
他叫陸序昭,是陸晏同父異母的哥哥。
當年我父皇在世時,為避免遠在西北的陸家擁兵自重,曾派人前去西北破解陸家當權的局面,然而權力爭鬥又怎能光明磊落,他們的父親陸擎被人謀害冤死。
謀反奪權,推翻大元,便是從那時開始策劃的。
陸晏隱去鋒芒蟄伏西北,只待有朝一日奪回西北兵權。
而陸序昭,則是被埋進大元皇宮的一枚棋子,他去勢入宮,不惜成為一個太監,多年來與陸晏裡應外合,只為完成這場蓄謀已久的復仇。
他在我身邊十年,騙了我整整十年。
我終於明白,當年破城之日他為何說我們都會活下來,又為何會得陸晏恩典成為大內總管,連他曾安慰我的那句“這是奴才欠殿下的”,都在這時徹底明朗。
草灰蛇線,原來一切都有跡可循,是我視而不見,是我分毫不疑。
我如行屍走肉般回到朱鸞殿時,陸晏正在殿內等我。
雕樑上的帷幔在兩側堆疊逶迤,殿內很暗,遠遠只能看清陸晏居於上位的剪影。他朝我一步步走來,面龐逐漸清晰,最終停在我面前,冷笑問:“都說清楚了?”
我沒有理會他,面無表情地朝內殿走去,卻被陸晏從身後拽住,一陣天旋地轉,便被死死抵在牆上。
他望著我,聲音帶著幾分咬牙切齒:“趙玉瑾,你那序昭哥哥沒了,你現在只有我了!”
“是啊,沒有了。”我低聲喃喃,抬頭卻在陸晏眸中看到片刻驚愕。我頓了頓,笑道:“可就算是這樣,陸晏,我心裡也不會有你。”
陸晏終是拂袖而去。
空曠冷寂的朱鸞殿裡灌進寒風,窗外大雪毫無停歇地紛紛揚揚,我在雕花窗前許久,終於一步步走回內殿——這深宮裡再沒讓我留戀的事物,所謂掙扎半生,釋然不過須臾。
從此刻起,我不是大齊的皇后,也不是大元的長福,我是趙玉瑾,也只是趙玉瑾。
冬逝入春,京城下了好大一場雨,我策劃隱忍數月,終於在那個雨夜逃出皇宮。
馬車顛簸離開京城時,我只覺呼吸都蘊上雨水的溼氣,抬眼望向遠方無際夜色,長路漫漫,天地間彷彿只餘下我一人。
我痛苦掙扎的一生,好像終於得到了解脫。
可序昭領人攔住了我的去路。
春雷陣陣,我將青銅製手爐朝他砸去,他紋絲不動,昏暗雨幕中,只一遍遍同我說:“請隨奴才回去。”
8
可回去了又能怎樣?我要面對的,是陰晴不定的陸晏,是欺我負我的序昭,是滿目瘡痍荒涼蒼寂的深宮,是血海深仇江山更迭的命數。
我開始吃齋唸佛,每日到供奉佛像的淨心殿潛心誦經,祈求佛祖能寬恕我這荒誕狼狽的一生。
某日我途徑御花園,遠遠看到陸晏正坐在頌春亭裡提筆寫字,序昭立於一側,躬身為其磨墨,二人身後盡是暮春的暖意,李白桃紅在枝頭爭豔。
我在遠處站了許久,恍惚間想,兩人兄弟同心,不惜犧牲眾多籌謀多年,只為推翻大元謀反奪權,若序昭不是閹人身份,那此時定會被陸晏封作王爺。
可這兄弟恭親的場景卻深深刺痛了我,那因吃齋唸佛隱藏下去的恨意,一如這入目的春景般熙攘繁盛,肆意蔓延,再也壓抑不下。
露重更深,我留在淨心殿遲遲沒有回去,大殿內燈火通明,層層幔簾在夜風中飄忽不定。
燭火搖曳間,我緩緩跪到佛祖面前,仰面望向這座高大鎏金的佛像,喃喃問道:“如果我那樣做了,您會原諒我嗎?”
大殿寂靜無聲,只有穿堂而過的清風低低嗚咽。
“您會原諒我嗎?”我又問了一遍。
無人回答。我慢慢起身,一步一步朝殿外走去,簷下的燈籠搖搖晃晃,夜色深重,只有一輪彎月灑下朦朧清光。我仰頭望去,只覺得心口一陣陣淒涼。
我不求任何人的原諒,我不求。
我邀序昭來朱鸞殿時已經入夏了,他得了訊息匆匆趕來,立在殿前愣愣看了我許久,才輕聲行禮:“長福殿下。”
我一身少女時的打扮,夏風輕輕吹動淺粉衣裙,同色披帛在臂彎裡如蝶般翩躚,我輕笑著望著他,一如兒時那般喚道:“序昭哥哥——”
應當是這假象太過真實,所以在我邀他飲茶時他分毫未疑,舉杯一飲而盡。
軟倒在地上那一刻,序昭錯愕地望向我,他嘴唇微動想說些什麼,卻已經沒了力氣,終是昏了過去。
我蹲下身子,冰冷的手指一點點撫上他俊秀的面龐,沿著精緻的下頜探進他白淨的胸口,一層層扯開了他本就單薄的夏裝……
陸晏撞開內殿大門時已經入夜了,他一步步朝梨木雕床走來,伸手將我從錦被裡狠狠扯到地上,我衣衫不整,床上還躺著昏迷不醒幾近半裸的序昭。
陸晏掐住我的脖頸,聲音像是從喉頭裡擠出來一樣,吼道:“趙玉瑾,你做了什麼!?”
我被他掐得滿臉通紅,卻仍舊扯著嘴角笑了笑:“你不是都看到了……不過你也不必擔心,他是個閹人,有些事……”
啪——
我捂住臉龐偏向一側,很快紅腫起來,陸晏捏著我的雙肩,目眥欲裂,雙眼通紅,怒吼道:“你這蕩婦,我要殺了你!”我仰面望著他笑,沒有絲毫畏懼。
我等著他這句話,等了整整三年。
在他說出這句話時,我好像終於得到了解脫,雖然我做這些是想讓他們兄弟鬩牆,是想看陸晏與序昭疏遠。
可直到如今我才發現,我似乎高估了我在陸晏心裡的位置,我與序昭的背叛,只會讓他遷怒於我。
也是,他們親兄弟之間患難與共的情感,又怎是我這個可有可無的女人能相比的呢?
就在這時,序昭突然跪到陸晏身後,我不知他是何時醒來的,木然看去,就聽他說:“求皇上放過娘娘。”
陸晏的身形晃了一下,沉默良久才回頭看向序昭,冷笑道:“朕憑什麼放過她?”頓了頓,他像想到什麼,又道:“朕可以放過她,但你要代她去死,你可願?”陸晏笑得陰冷,一瞬不瞬地看著序昭,直到後者終於緩緩點頭。
我坐在地上突然大笑,笑出了眼淚,我越過陸晏望向序昭,像穿過了許多年的風雨波瀾,苦笑著問他:“序昭,你欺我負我,如今又何必做出這副假惺惺的模樣呢?”
淚水浸透我憎恨的目光,我朝他大吼,聲聲泣血:“便是你代我去死,我也不會謝你這份恩情,你是罪有應得,罪有應得!”
他也望著我,雙眸沁著一股溼意,卻並未落淚,只是輕輕笑了笑,說:“是我罪有應得,這是我欠你的。”
這是此生序昭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
他沒有自稱“奴才”,亦未稱我為“殿下”,他只是望著我,目光悠遠而綿長,一字一頓又說了一遍:“這是我欠你的。”
9
我在朱鸞殿裡坐了一宿,天色漸亮,我踉蹌著走出宮院,渾渾噩噩地朝序昭居所走去。直到快走近了,我混沌的思維才反應過來——序昭已經死了。
序昭已經死了,死在了陸晏下令的杖刑下。
我親眼看著笞杖一下又一下落在他身上,他悶聲不吭,鮮血卻逐漸滲透衣衫,一滴滴落在地上,很快蜿蜒成溪,不知過去多久,序昭已然奄奄一息,可那杖板卻毫不停歇。
最後一次重重落下時,面前場景恍然回到數年前那個黃昏,他無辜遭我二皇兄杖責,滿身是血地躺在地上。
黃昏下,我踉蹌撲在他身邊,卻聽他輕聲說:“奴才血汙,殿下莫要髒了衣裙。”
陸晏面無表情地看向我,問:“哭什麼?”
我顫抖著撫上臉頰,才發覺自己早已淚流滿面。
我對序昭的恨,似乎隨他漸漸消散的生命而去,我坐在朱鸞殿裡不斷地問自己,這就是我想要的結果嗎?序昭死了,我到底改變了什麼?
天已大亮,我瘋了一般奔向頤安殿。
陸晏沒有開窗,殿內很暗,帷幔堆疊,這裡的一切我都是那般熟悉,恍惚間似乎還能記起父皇坐在案臺前的模糊身影,他將我抱在懷裡高舉的場面,笑著說“朕的小長福終於醒了”。
穿堂風呼嘯而過,陸晏一步步朝我走來,衣袖被吹得獵獵作響。他突然問我:“陸序昭死了,你難過嗎?”
還未回答,我已淚流滿面,陸晏見狀不怒反笑,道:“有件事我一直沒告訴你,如今陸序昭已死,倒沒什麼瞞著的必要了。”
他頓了頓,繼續道:“他是我父親小妾生的孩子,自小便不怎麼受寵,去勢入宮,是因為我拿他母親做了威脅,他不得不從。”
陸晏慢慢走近,雙眸緊緊盯著我,不懷好意地問:“他騙你負你,不過都是被我逼的,這個真相,是不是讓你更加絕望了?”
他居高臨下地望著我,大殿裡迴盪著他陰惻惻的笑聲,他說:“趙玉瑾,陸序昭死了,如今你只有我了。”
我已經哭不出聲音了,只不斷地落淚,這些話與序昭曾經的回答逐漸重疊,那年夏至,我問他初遇時為何坐在那兒哭,他說因為母親病重。
原來從那時便開始錯了,這所有一切就已經錯了,他為我而死,他說這是欠我的,可到頭來,他欺我負我,卻也是迫不得已。
我癱坐到地上,瑟縮著抱緊自己,腦海裡不斷湧現曾經種種,從前朝公主到今朝皇后,我這狼狽倉皇的一生,早已不是寥寥數語能夠說清的。
被人害過,也害過別人,我從天真爛漫到心性扭曲,不過須臾數年。
我開始努力地想,為何我如今還活在世上呢?這麼多年,我到底為了什麼活下去?
殿外雲端漸暗,天色陰沉得厲害,磅礴大雨隨之而至。
恍惚間我忽然想到,七歲那年,三皇兄在一場夏雨後帶我到御花園挖蟬蛹。
如果那時在他說“不用管,我們繼續挖蟬蛹”後,我沒有闖進那個林子,那麼我就不會遇見序昭了,更不會有之後這麼多的愛恨糾葛。
我應當同父皇母后他們一樣,早就死在了破國那日。
可我沒有,我還是遇到了序昭,終究是遇到了序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