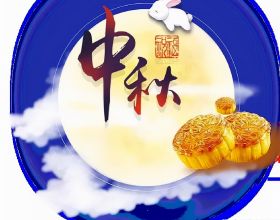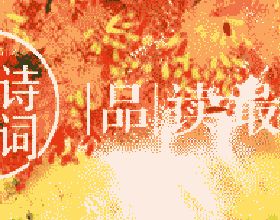文/錢路紅
轉眼,中秋又至。
“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中秋,是讓人思鄉的日子。
每到這一天,許多遊子紛紛趕回家中,與親人歡聚一堂,把酒言歡,共敘桑麻。而回不去的,唯有舉杯問月,今夕何年?酒尚未見底,淚已潮溼在他鄉。
一紙月華,無盡曼妙,染透塵世萬般。所以古往今來,月圓之夜,無數文人墨客揮毫潑墨,把中秋寫得蕩氣迴腸,催人淚下。而尋常百姓卻自得其樂,賞月品月,輕影相依,度過一段美妙的時光。
月影千年,夢迴人間。
“秋空明月懸,光彩露沾溼”,月夜至,思緒飛,抬頭凝望天,仍是懷念過去的那輪月。
那時的月亮又大又圓,即便星星滿天,也依然最為奪目耀眼。
那時的月光寧靜憂鬱,即便薄薄半簾,也依然美得令人傷心。
真的。
那時,每至十五月圓之時,家家戶戶必依照舊時習俗,陳月餅瓜果於庭,又涼水一碗,虔誠拜畢,方切成八塊,然後圍坐一桌,分食月餅。一時笑語喧譁,節日的氣氛在月光中彌散開來。
待曲終人散,萬籟俱寂時,唯餘明月高懸於深藍的天幕,月影如水,謂之美妙。偶有秋蟲唧唧,聽之神怡。狗吠忽遠忽近,聞之恍惚。夜鳥倏然飛過,似要離去人間,飛往月宮去。
“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只是不知,它是否一時興起?或者因為無聊寂寞?
一瞬眼,這月光,便掠過人們的心頭,隨風入了夢。
夢裡,仍是那輪月。
我夢見自己也在做夢。
夢裡的年代好像很遙遠。天地寂靜,離天明也很遙遠。我在夜色裡行走,一直走到無邊的荒野裡。涼月滿天,於一剎那照見了自己,也照見故鄉的月夜。
那時,我還小,父母還未老,外婆也仍健在。只是秋天過得太快了,一晃河水就瘦了,風就涼了,葉也落了,說不出的哀愁。所以,世界在我眼裡,是如此蒼涼,又如此美好。
中秋那天,父母提早收了曬場上的穀子。母親做飯,父親餵豬喂牛。外婆剝豆子。我變勤快了,幫著擇菜洗碗、打水掃地。晚飯後,我坐在門邊,兩手托腮,盼著天早點黑。
一年一次,能不盼嗎?
謝天謝地!風起了,太陽終於下山了。
暮色漸濃,夜幕悄然降臨。月亮慢慢地升起來了,先是薄薄的,似籠著一層面紗。不多久,月就明瞭,也漸漸圓了。月光灑滿了房屋山牆,又靜靜地瀉在院子裡。在僻靜的一隅,也透進一抹淺淺的碎影。
我興奮極了,奔至屋裡告訴父親。
如我之前寫的那樣,父親麻利地在院中支起一張桌子,供上月餅和水果,祭拜月之禮。
吃完月餅,母親在燈下做針線活,父親一旁坐著。許是因為收成好,加之吃飯時喝了點酒的緣故,父親打開了話匣子,講起過去的一些事情,還提到地裡的莊稼。他的神色開朗起來,眼睛裡泛著柔光。母親靜靜地聽著,偶爾點點頭附合兩句。
紗門“吱吱呀呀”開了,外婆從屋裡走出來。她倚著門框,對著天空看了好久,然後對我說,月亮上住著嫦娥仙子,雖然有玉兔陪伴,但她還是很孤獨。我凝望著她蒼老的眼睛,只覺得她也很孤獨。
我想問她,為何會認為嫦娥孤獨?可一看到她憂愁的眼神,就立即打消了這個念頭。
她默站了一會,拉住我的手,好像有很多話要跟我說。可過了半天,朝我呶嘴笑了一下,啥也沒說。她的眼白很渾濁,牙齒脫落了,頭髮也白了。她已經很老了,還經常生病。
嫦娥可以長生不老,但有一天她將會死去。人死後還會有生命嗎?另外就是,嫦娥可以漫遊月宮,人卻只能在地上行走,還要忍受病痛的折磨和塵世的苦楚。
一想到這裡,我就很難過。
這時,有人在門邊喚我,說出去玩。
我朝屋裡喊:“媽,我想出去玩一會。”
母親正與父親說著話,我這一喊,她突然一愣,隨即朝門外瞧過來,“唉唉,這麼晚了,別去了。待會還要去曬場上看穀子呢。”
那時,每到這一季,晚上都要去曬場上看穀子。
外婆也說,別去了,太晚了。
我雖然心裡不願,想了想,還是默默應了一聲,好嘛。
過會,母親也走出屋來,抬眼向四處望,咦,我的貓呢,跑哪去了?因不能出去玩,我心裡有點煩,於是噘著嘴,有點沒好氣地說,剛才還在呢,興許跑老屋裡去了。母親轉而望著我,臉色有些惘然,哦,是嗎?
那些年,家裡一直養貓。但母親總是說,我的貓。她每天用魚骨頭拌飯餵它,對它說話從來都是輕聲細語,像對待孩子一樣。也沒見它怎麼捉老鼠,還總把家裡弄得很亂。所以每次見了,我心裡就覺鬱悶。
風吹來,山牆上泛起一層落寞而溫柔的光,屋簷下的辣椒串隨風搖曳,豆角叮噹作響。這聲音,無論如何也讓人不再惆悵和寂寞了。我的注意力很快就轉移了。
母親繞了一圈,也沒貓的影兒,心裡有些悶氣。這時候,狗跑過來汪汪叫了兩聲,用嘴巴輕輕地碰一下母親的腿,似渴望得到點什麼。母親低斥道:“去去去!還沒吃飽吶?”它委屈地望一眼母親,然後默默地蜷到一邊去了。
風好似大了些,樹影斑駁,微涼。母親對外婆說,媽,回屋吧,天涼了,當心感冒。
外婆點點頭。
父親呆呆地站在廚櫃前,看著桌上爺爺的小石像。我喊了他一聲,爹。他回頭看我,眼眶紅紅的。我知道,他想爺爺奶奶了。母親心下嘆息,但什麼也沒說。
我不知道父親是否在夜晚哭泣過,我只記得有一次他微醉後說起奶奶晚年時,獨自住在老屋,誰家也不去,說是老屋裡有爺爺的氣息。彼時,她腿腳已不靈便,行走困難。有一天早晨,天剛矇矇亮,父親就去老屋看她,一進屋,就見她趴在門檻邊,身上髒兮兮的,膝蓋處還有點擦傷。父親瞬時淚崩,趕緊抱她起來,悲切問道:媽,昨晚你還好好的,怎麼就……但是他哽住了,說不下去了。奶奶眼睛紅紅的,什麼也不說,只緊緊地摟著他的脖子。父親明白了,低泣道,媽,我們回屋裡去。從那之後,奶奶就臥床不起,身體每況愈下。
當時,我想到一幅畫面:父親端來一盆熱水,給奶奶擦拭乾淨,笨手笨腳地為她換衣服時,奶奶充滿愁苦的眼睛溼漉漉地望著他。她伸出手來撫摸父親的臉,癟著嘴笑了……
過了好一會兒,父親走到門邊,拿起水煙筒,將菸絲捏成小團放到菸嘴口,想了想,又擱一邊了。他靜坐角落,似有無限惆悵。
母親擺弄著她的蒲蘿,提到穀子曬乾後要交公糧。她還說,今年收成好,鐵皮圍子估計有點兒裝不下。玉米曬乾了要剝粒才行,樓上已經堆不下了。父親默默點頭,聲音低啞地說一句停一句。
外婆默坐在燈影裡,神情有些困惑,彷彿在費力地回憶什麼。她的孤獨被拋在那個金色的秋天或冬天,她守著姨媽和母親,漸漸老去。她似乎已經遺忘了早年的顛沛流離,以及由此帶來的所有痛苦和惆悵。我想,如果她真能徹底遺忘,也不失為好事。
月光千古不老,時間卻匆匆流逝。風吹過樹葉,發出窸窸窣窣的響聲。夜晚降臨了。外婆已經睡了。
父親透過小窗往外看,滿地都是月光,大門頭上也像塗了一層銀霜。他說,時候差不多了,得去看穀子了。
“你白天不是吵著要去嗎?怎麼說吶。”父親轉過頭來,微笑著問我。
“我要去。”一想到可以伴著月光入睡,我就興奮不已。
“嗯,那就走吧!”父親提了水煙筒,走到院中。
“好。”我拿塊月餅追出來。
母親抱著被子出來,聽說我也要去,又回屋去拿了條薄毯、一個小枕頭。
曬場周邊,有人已經打了地鋪或是睡在架子車裡。父親白天就在曬場邊上用木頭支架搭起一個臨時帳蓬,鋪個席子作床。
帳蓬不寬,稍微有點擠,但我很開心。月亮掛在天上,房屋緘默,樹影橫斜。秋蟲的私語,在耳邊低低地迴盪。農田、菜地、谷堆和草垛,在月光下顯得生動輝煌。
母親忙了一整天,不多時便睡著了。父親也累,但他心事很重。也許,他在悄悄流淚。那會,我真希望來一陣風,吹落父親的眼淚。沒了眼淚,他就不再憂傷了。
這麼想著,不覺眼睛就潮溼了。
遙遙傳來幾聲狗吠,顯得有些空幻。我忍不住又朝天上望去,望著望著,憂愁就慢慢消失了。
夜涼如水,天空地淨,夜晚沉醉在幻覺之中。空氣裡有稻穀瓜果沁人的香味,星光沉寂地閃爍,很美。
夜霧,像夢一樣,不知什麼時候漫了上來,漫過曬場,又被隔在帳篷外了。
於是,夢靜靜地來了。風也來了。夢裡,我走得遠了,飛越關山,又回到了從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