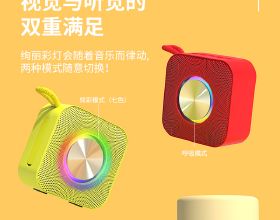直到我成為一個母親,才深深感受她的那種痛。
從自傳體長篇《飢餓的女兒》到《好兒女花》,兩本書相差十年。這兩本書寫自己和母親,寫原鄉和逃離,想弄明白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不同的是我個人的身份發生變化,以前我是作為一個女兒去寫母親,而現在是作為母親,寫母親,聽者是我的女兒。
以前看見了母親為我、為這個家庭做出犧牲,她作為普通女性中的一員,成為了這個時代的犧牲者,我想得還不透徹,不理解她的犧牲到了何種深度。
直到我成為一個母親,才深深感受她的那種痛。
母親身上的悲劇延續,最讓她無法承受的,不是來自於她的敵人,而是來自她的親人。
對待孩子,我和母親還是不一樣的。我的情況比母親好很多,我沒有經濟方面的擔憂,也會減少和外界、家人的諸多問題。她當年面對比我嚴酷得多的困難險阻,獨自承擔一個會向她壓倒下來的天地。母親比我勇敢,比我無畏。
生存
家人給我的一個版本是母親晚年過得非常好,不愁吃穿,有兒孫孝敬。當我在喪禮上時,知道母親晚年撿垃圾時震驚不已。家人的解釋是母親有阿爾茲海默症。母親是有意識地在做這樣一件事情,被虐待,吃不飽飯,餓著肚子,她找不到一個人可以傾訴內心鬱悶和說說心裡話,她要走出家門,去透透長江邊的新鮮空氣,她去江邊撿垃圾,賣錢,可以購包子和花捲吃。
母親一生中有兩個黑暗時期:第一個黑暗時期是在她懷上我時,1961年,那時處於飢餓困難時期,丈夫在船上工作,因為身體營養差,沒吃飽飯,從船上掉下江裡受了傷,被送進醫院。沒法傳達訊息。母親很長時間沒有他的訊息,處於一片絕望之中。她帶上所有的孩子,讓每個孩子都去撿能夠吃的東西。五個孩子和她飢餓難忍。那時一個年輕的男子是母親做臨時工挑沙子的記工,當別人欺負她時,他站出來幫助她,他把自己的口糧給母親,自己不吃,都給孩子們。兩人相愛。母親的生活很艱難的,但心裡有一點光亮,那是這個男人的愛情照亮了她,她因為有這樣的光,敢懷上我,敢生下我這個私生女。
第二個黑暗時期,母親晚年撿垃圾,撿垃圾這件事首先是在家裡得不到兒女的理解,再就是她餓,自然而然就去尋找食物,撿垃圾。
母親陷入對往日的回憶中,已逝去四十多年的黑暗給了她一種對照。一個很孤獨的老人,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將結束,她透過回想一生當中最浪漫最有激情的時期,那就是回憶和我生父在一起的點點滴滴,度過眼前的絕望,對現實的黑暗進行抵抗,當成一個出口。
母親這樣生存,好多年,我都不知。
懲罰與獎賞
母親從未打過我,但總是冷眼看我,彷彿她一生的不幸都跟我有關,這是我十八歲前的真實感受。十八歲生日那天我知道了緣由,因為我是私生女,她得承受家裡、社會對她終身的懲罰。
有一年她的生日,我專程從英國趕回去,給她在鵝嶺公園大辦生日,她說那是我給她生我養我的獎賞。我別過臉,不敢讓她看到我眼睛紅。
我第一次聽到“黃金棍下出好人”這句話,是來自我的初中化學老師,他在家裡打逃學的兒子。老師宿舍就在我們的教室東北方向,有一坡二十多步的石階。他邊打兒子邊說這句名言。當時正是課間休息,他在氣頭上打兒子,不知石階下面有那麼多觀眾。多年後,我遇到一個同學,說起舊事,她說化學老師的兒子考上了重慶大學。
我女兒出生後,我給她講這個故事,她做錯事後,主動伸出手來,要我懲罰她。我沒有。我對她說:我會懲罰自己,把自己關在屋子裡,你在屋子外思過。
空間阻隔,讓兩個心繫一起的人,獨自思想,所發生的事。這樣的結果比體罰有用。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我從未得到過母親或是父親的獎賞。我也很少得到學校裡的獎賞。就像前段時期,有雜誌約稿,說到他們有兩年一度的獎,我說我從未得過獎。他很吃驚。我是邊界外的人,從這一點來看,也未必不是好事。(虹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