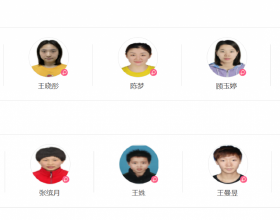#我是大美河北推薦官##河北文旅看圖識景##頭條帶你樂享河北#
元中都博物館。
元中都出土的螭首。
雪,如約而至,崇禮太子城遺址,正笑迎世界。不遠處的她,佇立於北國的雪域草原,亦為之嫣然凝眸。
上承宋金,下啟明清。作為城池,她湮沒於塞北冰雪中長達七百多年;作為皇宮建築群,她以龐大體量鮮活地體現了元代宮殿建造藝術;作為都城,她堪稱草原都城史上的絕唱,對於認知我國古代都城制度的淵源演變極為重要;作為遺存,她破解了元代諸多宮廷秘史,印證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歷史程序。
她,被列入199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是我省在壩上開展的首個都城考古,是我省首個正式掛牌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元中都遺址。2021年11月公佈的我國《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中,元中都遺址被列入“展示提升工程”。
一
旺兀察都:穿越歷史的“活化石”
雪,再一次落在這片草原。史書記載,此地曾經被稱作“旺兀察都”。
坐北朝南,高逾丈許,穿過青黝的南門,風雪灌入脖項,冰冷巨石交接處,纖細而堅韌的“吉祥草”,在漠北風霜中兀自搖曳。“這草別處沒有,當地老鄉給它取了兩個名字——‘宮牆草’‘皇城草’。”幾位頭髮斑白的考古學者蹲在這幾棵小草旁,愛憐地撫摸著,不無感慨地說:“顧名思義,這座城其實早該被尋到的。”
尋找失落之城,永遠令人神往。但類似元中都這樣,儘管頹垣斷壁,卻一直殘存於地表,可又偏偏被遺忘和誤讀的古城,怕是極少的。“小隱隱於野”,然而,這尚未竣工就冷清的古城,卻鐫刻、封存和見證著一個馬背民族的鐵血與輝煌。
蒙元王朝曾有四座都城,分別是哈拉和林、上都、大都以及中都。
蒙古人建立政權之初,並沒有固定的都城——大汗氈帳搬到哪兒,哪兒就是都城。哈拉和林,水草豐美。曾經,匈奴、突厥、回鶻等,多次設都城於此。為了處理日漸繁複的軍政大事,1235年,窩闊臺也在此營建都城。工匠大都來自被征服的西域各國和一些中原戰俘。這是一座充滿遊牧特色的都城。
上都和大都,均由忽必烈下令營建。主持營建者是邢州人劉秉忠。他是這兩座都城的設計者,更是元朝政體的最主要設計者。
中都,營建最晚,位置居中,存世也最短。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即位不久的元武宗孛兒只斤·海山下令:“建行宮於旺兀察都之地,立宮闕為中都。”
都城,對於一個王朝和國家意義非凡,如長安城之於漢唐、北京城之於明清。但這些都城及其建築在後世考古學、歷史學、建築學上來說,存在一個難點,即古今文化層疊加。那些浩瀚交織的資訊,唯有進行真正大規模系統性發掘才能提取,需要仔細分析考證才能逐步弄清其演變真相。
那麼,有沒有這樣一座城,不但歷史地位重要,而且資訊明確單純,同時又能夠準確而集中地反映中國古代都城的營造制度呢?顯然,短暫的元中都提供了絕佳範例。
然而,她究竟藏身何方呢?元亡後數百年間,世人並不清楚其具體位置——明代人寫《北征錄》提到“沙城”,明成祖說“即元之中都”。據此,應該就在張北,但到底在哪兒,地方誌記載多是以訛傳訛。
張北版圖,形似一隻玉兔,蹲踞西南,朝拜東方。“白城子”,進入考古人視野。1997年,關於“白城子”就是元中都的論爭到達頂峰。當年7月,著名考古學家宿白以及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徐蘋芳、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長劉世樞、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長任亞珊等前往白城子實地考察。
隨後,河北省一批風華正茂的考古人匯聚壩上,開啟了這個草原都城考古的新篇章。
發掘工作從“角樓”開始,是一個標誌性的選擇。《元史》曾載,武宗下詔修建角樓,中書省官員以農事忙、蝗蟲災、百姓困苦為由勸止。武宗卻說:“皇城若無角樓,何以壯觀!先畢其功,餘者緩之。”若記載無誤,那麼角樓將昭示其都城地位。
角臺,是角樓臺基,與城牆相連。自1998年開始連續三年,對西南角臺的發掘分期進行,一種在元代考古中前所未見的角臺結構顯露出來——角樓臺基平面呈曲尺形,從西南角起向東、向北呈三級縮折後分別與宮城南牆和西牆連線,蔚為壯觀!
“三出闕!”那一刻,年輕的考古工作者張春長驚呼起來。這是闕制中的最高等級——“天子之制”,是顯示其天下獨尊的標誌性建築形制,為證實白城子是元中都遺址提供了有力論據。經比較,西南角樓與元大都皇宮“十字角樓”如出一轍,大量形制巨大的琉璃龍、鳳、行什等鴟吻和走獸,與浮雕龍紋的瓦當、滴水均表明了角樓建築的皇家性質和氣派。
此後,中心大殿臺基的發現,進一步證明其至尊地位。殿址位於宮城中心略偏北,呈南北方向水平放置的葫蘆形。臺基分上下兩層,上層承載宮殿主體部分,從南向北排列有月臺、前殿、廊柱、寢殿、東夾室、西夾室和暖閣,下層為宮殿迴廊部分,臺基周圍有七條上殿通道。藉由臺基結構,考古工作者發現,這座佇立於草原的皇家宮殿,採用了一種典型的中原宮殿傳統建築佈局形式——“工字殿”。
“這種‘工字殿’佈局形式,在唐代渤海國上京遺址就有發現,宋金元明清均有此種建築形制。如南宋臨安大內的部分宮殿、金中都大安殿、元大都大明殿都有類似的平面佈局,它蘊含著‘五行’‘擇中’的傳統設計思想,反映了中華民族的智慧。”張春長說,這是目前發現元代大型重要建築“工字殿”的唯一例項。
歷史細節逐漸清晰。中都佈局和建築特點,與中原傳統都城典範的大都更相似。無論是三套城垣配置、中軸對稱的佈局特徵,還是三出闕角樓、“工字殿”的建築風格,均是一脈相承。但是,中都也有自身特點,如中都正殿1號臺基位於宮城的幾何中心,比元大都更合乎《周禮·考工記》的都城規制原則。
“元中都遺址考古是我省在壩上的首次都城考古發掘專案,其成果非常豐厚。”張春長說,作為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後又返回草原所建的都城,元中都匯聚草原和農耕兩大文明,對於瞭解我國古代都城制度的淵源演變極為重要,尤其在研究元代都城建設理念、城市規制、建築特徵以及雕塑工藝方面,發揮了標本作用。
二
風雪中都:曇花一現的悲情絕唱
再大的雪,終有消融之時。
沿殘兀的土牆踏雪而行,是一種截然不同於北京城的感覺。這個位於壩上草原邊緣的失落之城,頹廢突兀,恢宏而低沉,像一個盛極而衰的背影。
目之所及,終歸於一片茫茫雪色。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六月初一,27歲的元武宗下令營建中都時,豪情壯志溢於言表。彼時,這位鎮守漠北的年輕人,剛剛揮師南下在帝位爭奪中勝出,登基不過數日,緣何立刻在兩都之間營建新都呢?
考古注重實物,歷史講究文獻。然而,從性格、心理和環境等層面,不妨探究一下武宗的所思所慮所圖——某種程度上,大歷史程序中一些決定,往往預兆於那些細微而瑣碎的枝節上。
一切,恐怕還得先從冰雪山川談起。
中都,位於大都和上都之間的驛道上。東、北兩面是廣闊草原;西靠狼尾巴山;南臨野狐嶺,是燕山陰山會合部的一座天然山口;西北不遠處有鴛鴦泊,是壩上最大的湖泊……相比於上都,中都更偏西,位於草原邊緣,向南可居高臨下鉗制華北平原,向西北可聯絡和鎮守草原遊牧民族各部。空間佈局上,在此建都,既可成為上都和大都之間的聯絡點和支撐點,還可以構成一個更緊密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網路。
地利形勝,確實如此。此前,成吉思汗正是在這一帶建立豐功偉績。金大安三年(1211年),成吉思汗揮師南下,以不足十萬人馬大敗金軍四十萬,史稱“野狐嶺之戰”。這是決定蒙金命運的決定性戰役,更深遠影響了此後中國歷史的走勢與格局。
而今,自野狐嶺南望,雪色影綽,江山無限。
元代汗位繼承,是一種奇特的蒙漢雜糅的方式——嫡長子繼承與“忽裡臺”大會公推大汗的雙軌制。前者,是自上而下指定,後者,是諸王自下而上推選。這一成吉思汗煞費苦心確立的皇位“雙保險”,往往會“不保險”,因為最終是軍事實力決定候選人。長期鎮守漠北的海山,有軍隊和漠北諸王的推戴。但當時的大都、上都,是其帝位競爭對手、弟弟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勢力範圍。
元成宗死後,1307年,鎮守漠北十年的海山以奔喪為名,兵分三路南下,駐足野狐嶺,繼而進至上都,迫使弟弟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拱手讓出剛剛與安西王爭搶得到的皇帝寶座。為避免兄弟相鬥,在兄弟倆的母親斡旋之下,雙方約定皇位“兄終弟及”“叔侄相承”,史書對此美飾為“武仁授受”。
天命既已歸,人事不可廢。野狐嶺,對於海山而言,是“龍興”之地,有著別樣情懷。他毫不掩飾地表示,“徘徊太祖龍旗九斿,剪金於斯,肇基帝業,為城中都”。同時,出於局勢之慮,也亟需從東、西兩面有所部署——不但建城,行政上也迅速跟進,升隆興路總管府為中都留守司兼開平路都總管府,享受和大都、上都一樣的行政級別。而某種程度上,其祖忽必烈在灤河上游的閃電河流域建立新城——開平府(上都),廣攬西域各族及漢人英才,形成“金蓮川幕府”,最終在汗位爭奪中勝出的輝煌創舉,也可視為一種冥冥之中的心理召喚和安撫。
這種先祖崇拜和另類的“循規蹈矩”,往往在那些自命雄才大略的帝王身上格外凸顯。古今中外,大抵如是。然而,建成一座都城,豈在頃刻之間?
真實歷史,被一點點印證。考古發掘中,出土80多個螭首,形象生動,刻工精美,可嘴部卻沒有開孔。螭首是用來裝飾排水口的,俗稱“螭首散水”,沒開孔能有何用?其營建之倉促可見一斑,而海山心境之緊迫亦可想見。
1311年正月初八,巍峨的大都,“帝崩於玉德殿”。弟弟繼位,是為元仁宗。隨即,以財力不足為由宣佈“罷城中都”,撤銷中都留守司。
元中都,隨即終止了成為帝都的短暫命運,降格為皇家行宮。
中都冷落,暗流湧動。至治二年(1323年),泰定帝在此做了一次佛事。泰定三年(1326年),又打了一次獵,“次中都,畋於江火察禿之地”(《元史》卷30《泰定帝紀二》)。天曆二年(1329年),文宗圖帖睦爾與其兄明宗和世 產生爭鬥,兩人皆為海山之子。圖帖睦爾以將帝位相讓為由,將和世 從漠北騙回,在父親營建的這處行宮,以毒酒弒兄(《元史》卷33《文宗紀二》),史稱“明文之爭”。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閏七月二十八日夜,元朝最後一個皇帝元順帝逃離大都,於八月初九逃至荒廢的中都,短暫休憩觀望後,又逃至上都。翌年正月,中都地震,彷彿天象一般,給予其心理最後一擊。此後,這位武宗一脈、明宗長子遠走西北故地,病逝於應昌(今內蒙古達裡諾爾西南)。
縱觀元代,中都之肇興和湮滅有其必然性。張養浩曾作《山坡羊·潼關懷古》哀嘆“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既是“觸目傷懷”,亦可謂“一曲成讖”。武宗年間,身為監察御史的張養浩曾三次進諫,歷數時政“十害”,其一便是“土木太盛”。其實,營建中都不僅耗資巨、勞役重,民怨沸天,同時官僚機構之膨脹和吏治之腐敗亦無以復加,而且,從已確定的“兩都制”來看,無論重要性上,還是地理位置上,居中營建均無必要,即便真正啟用,執行成本也會非常高。
風雪中都,遺蹟靜默。
也許,這注定是一個夢幻般的錯誤。這座曇花一現的元代都城,像一部濃縮版的元史,印證了許多難解之謎,成為草原都城史上的悲情絕唱。
三
遺址公園:草原星空的昨日重現
“不研究草原文明,就說不清中華文明。”此種說法基本已成共識,這關乎中華文明程序。整個北方遊牧民族歷史文化研究始終是一個世界性課題,他們大大影響了歐亞大陸的歷史程序。元中都考古的意義,不僅在於確定所在地,尋覓到古代都城營建及建制的“活化石”,更深遠的是填補了史料空白,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
霧凇,冰雪,朔風,曠野……漫步在這片塞北雪域,豈能無感?
“一座中都城,半部元朝史。”回溯歷史長河,中都城的營建和在此發生的事件,應當上升到元王朝中後期國運的高度來認識。那些看似突兀的片段,有著根深蒂固的歷史慣性,更真實地反映著入主中原的草原王朝四顧徘徊的彷徨處境,折射著自身傳統和多種文化融合的艱難發展之路。
屬於歷史的,早已化作塵煙;關乎未來的,又該何去何從?
元中都遺址發掘以來,被列入199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01年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基於其重要性,在任亞珊、張春長、齊瑞普等人埋頭髮掘了十年後,2008年省古代建築所的劉國賓等人開始著手實施元中都遺址修復保護工程,2017年12月入選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是在國家推進大遺址保護程序中出現的新生事物。2009年12月,國家文物局制訂《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管理辦法(試行)》,將其定義為“以重要考古遺址及其背景環境為主體,具有科研、教育、遊憩等功能,在考古遺址保護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國性的示範意義的特定公共空間”。
2009年,元中都一號大殿遺址實驗工程;2013年,元中都一號大殿遺址保護工程;2014年,元中都皇城南門、宮城南門西馬道和門內廣場保護工程;2015年,元中都宮城南門、西南角臺建築遺址夯土保護及排水系統工程;元中都遺址環境整治工程;2016年,元中都遺址宮城西城牆南段保護工程……
“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主旨,是讓文物活起來,透過保護和有效展示,讓文化的魂與根產生現實影響。”省文物局專案管理處處長賈金標說,圍繞遺址公園建設,編制了《元中都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規劃設計書》《元中都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文物影響評估報告》和《元中都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專案建設計劃書》等。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正分五期建設,總投資約3.87億元,以保護遺址真實性和完整性為原則,科學展示考古資訊和文物遺址資訊,構建起元中都遺址生態、文化、景觀大格局。
“以園護遺,以園示遺”,合理整治環境,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元中都遺址保護區管理處保護研究科科長趙學鋒介紹,張北縣已投入資金5000多萬元,使遺址本體得到有效保護,整個園區風貌也得到改善。還委託河北和新疆等地文物古蹟保護專家到遺址調查、取樣化驗,制定設計保護方案,採取裂縫灌漿、土坯支護的方法對城牆進行保護。此外,還成功申報了數字化保護專案,藉助資料採集與處理技術,使遺址在文保方面與現代科技接軌。
作為我省首個掛牌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元中都遺址的保護利用對目前已在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中立項的中山古城遺址、鄴城遺址等意義非凡。據悉,下一步,將結合《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努力實施大遺址展示提升工程和大遺址研學精品工程,在實證文明起源、彰顯文化傳承、見證民族融合、印證文明互鑑領域努力發揮大遺址展示利用成效,提升其展示利用水平。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順歷史軸線遠眺,七百多年前,劉秉忠根據《易經》,給這個真正意義上入主中原的新王朝取國號“大元”。真正的“大”,其內涵是什麼呢?
七百多年來,世界格局已發生鉅變,包容開放的中華文明始終巍然屹立。走在元中都的廢墟和野草間,皚皚白雪自腳下發出“咯吱”聲,彷彿已經推開歷史、現實和未來的“三重門”。歷史上,平等開放、融合發展的理念是漸漸形成的,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誌,而真實的歷史程序早就超越自身侷限,孕育著更開放的視野。
草原星空,璀璨閃爍。昨日重現,歲月更迭。如今,不管是歷史風雪中的元中都遺址,還是慷慨悲歌的燕趙大地和生生不息的中華文明,正在書寫著新時代新徵程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