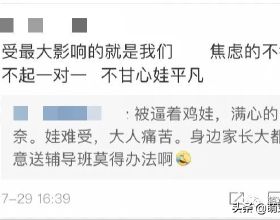夜走乾州古城
文/匡列輝
空調扇呼呼地不停吹著,起身關了。窗外,又傳來了別處空調嗡嗡地響,混著遠邊車子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的飛馳聲,不歇氣地來來回回在耳邊擊衝。心裡有點煩,覺也睡不著了,翻身起來,坐會兒,閉上眼,乾州城的夜色又清晰地浮在腦海中。
到吉首來,聽朋友說,這裡的古城值得一逛。可是,白天坐在會場裡邊正襟聽著,一坐就是一天。實在太困了,便用連衣的帽子遮著頭睡了過去,也不知是什麼時候,迷迷糊糊聽見安靜的會場起了一陣躁動,開啟眼睛卻是會議結束大家起身都在往外走。我一機靈,趕緊將帽子往後一掀,揉一下迷朦的睡眼跟著人流出了大門上車。
吉首城市不大,往前看是山,往後看也是山。很難得大山下有這麼一個平地,建起了這麼一座城。整個城就像是被大山圍著的一個搖籃,除了車流的嘈雜,看一眼那山,以及這搖籃裡大大小小的建築,和街上不緊不慢走著的行人,感覺一切都十分的安靜。我們從大山外面來,城市裡人們的行色匆匆,街上的老樹枯枝與扯動枝條的凜冽風聲,似乎一下子都不見了。甚至到了深冬的時節,這道旁的樹有好多都還是青青翠翠的,照著陽光時候,葉子全能發出許多的亮色來。
心裡念著的古城,離住處其實不遠,還沒有看夠街頭的那些綠,還有那灰屋一角一閃而過露出的幾枝深淺不同的紅色梅花,車就停了。
此時,天卻暗了下來。燈亮起來了,眼前是高大的古城門樓。駐足抬頭,只見燈火之下的門樓顯得格外穩重厚實,城樓之上,插著的紅黃三角旗隨著微微晚風在輕輕地動,讓人一下子想起了三國或是水泊梁山裡的那些場面。這厚厚的齊整壘起來的磚頭是不是現代人用水泥磚堆起來的?便悄悄地問邊上的同伴,同伴老家隔這裡不遠。他說哪裡,這是四千多年就有的古建築啊,早有了呢,只是隨著歲月風雨的侵蝕,有些毀壞了,但是當地的人懂得愛惜和保護,壞了就及時修繕,才有了今天的模樣。
我將信將疑地靠近城牆,用手輕輕一推,紋絲不動。仔細瞅了瞅,發現真是匠人們就地取材用打磨好的麻石條磚一塊塊砌起來的,磚與磚結合得緊緊的,沒半點縫隙。每一塊磚的表面,又佈滿了無數的小突起,那是師傅們手握鐵錘,在鐵與石頭不停碰撞的暗紅火星飛濺中,一下一下鑿出來的。
到全國逛過不少古城,模樣大底都差不多,路徑也有相似處。都是進了高大的城門,然後不急不慢地看那些有古意的建築,而那些建築呢,真是古代的少,往往是仿古,頂多的是在門前擺個有年代的石頭柱子、槽子或是石獅之類的,沾上一點舊意就挺不錯了。可是這大山裡的古城,卻找出些別樣的不同來了。
進城門得踏上好幾級石頭做的臺階才能跨過去。沿石階而上,經過那城樓的甬道,突然眼前暗了許多,只有樓外昏黃的燈有一點餘光斜著漏了進來。我想趕上前邊的隊伍,又擔心著腳下的臺階,眼睛盯著下面,高一腳低一腳地邁著,突然前額猛地被撞擊了一下,我哎喲叫出了聲。額頭馬上腫起一個小塊來,一邊輕揉一邊心裡暗暗地罵著,這麼矮的牆。一抬頭,發現城牆上頭還遠著呢。原來剛進來時沒有發現城門底下有起重機朝門內伸著長長的鐵臂,我的頭碰著了臂盡頭吊著的鐵疙瘩。像是遭遇了當頭棒喝,便記著了危險無處不在,行事得處處小心。我趕緊偏著頭離開了。
進了古城,街面卻是十分平整,燈光一下子亮了很多,有穿苗服的年輕姑娘從身邊輕盈走過,像一陣春天桃林裡的微風,除了輕輕的悅耳銀飾小器件發出的脆響,風裡還有悠悠的香味,一絲絲的香不費力地潛進了你的鼻中。我無意看見了那燈光下年輕的面龐,是那樣的恬靜又是那樣的美,黑的雙眸映著燈光,像夜空裡微笑的精靈,輕輕靈靈地來,還沒有等看得清,又倏然地前行著,消失在人來人往中。只有那香,好像還不曾遠去,若有若無地縈繞在身邊。
乾州古城夜景。圖/匡列輝
肚子餓了起來,接待的單位十分的客氣和周到。吃過飯,走下曲曲折折的樓梯,繼續前行。
夜行,有一種好處,能夠用暮色幫省略去好多白天裡不自覺地得看清的諸如門牌窗欞等許多細節的東西。朦朧的燈光下,在高的樹影的遮擋下,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樣寫意與迷朦。如果是晚飯後,喝上幾杯,趁著酒意,在這青石板鋪成的街面上,讓路燈忽左忽右地將身影拉長,聽一聽那晚風中的歌謠,看一看那同樣是逛街的年輕面龐,然後,沿河的石上坐定,看著蜿蜒的河水靜靜地繞著山城流遠,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用做,那將是愜意的夜晚啊。但是,今天我們沒有喝酒,眼睛也就顯得清醒了許多。黑的石板上,有四邊形的圖案,深深地刻上了振翅飛翔的蝙蝠,四隻連在一起,像是手牽著手在跳著歡快的圓圈舞蹈。在這邊城,到處都有各種的雕刻。在從城裡走出去的著名藝術家博物館前,就立著兩個白色石頭雕刻的石人,嚴肅地立在那裡,出了鞘的寶劍緊握在手下,威風凜凜的,看腳底介紹,才知道這一立就是一千多年了。也有流水的欄杆上,柱頭刻滿了捲毛的小獅子,獅身的溝壑裡早已佈滿了青黑的塵埃,可是獅頭卻被人摸得格外光滑。
不遠處,是一個木頭做的大屋,木的柱子,木的窗欞,木的牆壁,牆壁上雕刻出了龍和鳳等不同形狀和姿勢的圖案。那些龍,很小,但是一鱗一爪都很精細,它們似乎沿著牆壁在奮力向上,向上,要突破那黑的屋頂,直上九重霄。鳳凰呢,舞動著長長的尾羽,舒展著飄逸的雙翅,卻沒有絲毫要飛走的意思,倒像是好客的主人,紛紛熱情迎接遠方的遊人。我看了看這琳琅滿目的小動物,感覺這木的紋理和顏色,約摸都有一定的年月了,但動物們的神態、姿勢,一直保持著,是如此的栩栩如生。也許是天太晚了,屋子的門緊緊地關著了,正門高掛著一個鼓著圓眼吐著長舌和獠牙的猙獰面具,那是儺戲裡的人物吧。門邊掛著一塊長牌,寫著“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雕刻”等字樣。
關門的地方不想久留。同行的出門幾天了,他們三三兩兩地湧進了那燈光正透亮著的地方小吃的商鋪裡邊,挑選著有特色的糖玩具之類去了。我的腳步停在了一個銀飾店前。店內櫃檯裡,滿滿的各種銀器在雪亮的燈直射下迸出醒目的光。模特的身上穿著喜慶的刺繡織錦,頭上手上戴著閃閃發光的精美銀飾。湘西的苗家姑娘,可能曉事起,就在為以後還長著的出嫁日子裡的美麗嫁衣動了心思。十幾年風裡雨裡,只為著往後能夠漂漂亮亮嫁出去的這衣服而一點一滴積攢著努力了。我不敢湊近仔細地去看,像是怕驚動了這櫃前的姑娘,明明知道她只是個永不會說話的含羞的擺樣人兒。我更怕弄出點聲響,因為櫃裡還坐著一位在燈下,戴著厚厚的眼鏡,手拿尖嘴小錘的老藝人,他正敲擊著一根細長又彎曲的銀條,一下一下,是那樣的專注。長年累月地用眼,厚厚的鏡片快滑下他的鼻尖,貼到那銀條上邊去了。好久,他抬起頭來,看到了遠處看他的我,眼神從眼鏡框外射過來,似乎有一種寒光,銳利得很。然而,馬上,他又低下了頭,重新拿起小錘。
夜更深了,路上的遊人少了很多,黑的路面顯得寬了許多。路盡頭是有欄杆迴廊,同伴們還在挑選東西吧,倚著欄杆等同伴。目光廊下望,幾丈之下,是黑黑的河流,靜靜地淌著,路燈的光在河裡拖出了昏黃的火苗,搖曳著,無聲地不停閃動著。不知從水邊哪間青磚黑瓦的房子裡,傳來了如同這闇火苗微光般的歌,聲音低低沉沉的,隨著這靜夜裡的流水,渺茫地飄在了起著寒意的古城的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