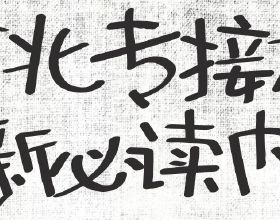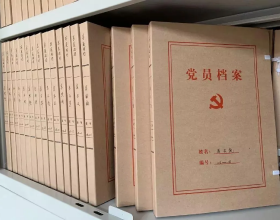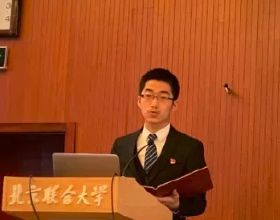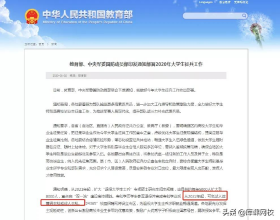文/宋玉華
青山如環抱,老村不沉寂。古松翠挺立,千年守望直。
在城市化快速發展的程序中,見證和承載著歷史的古老民房都已所剩無幾,就連鄉鎮的老街道、山村的老民居也顯得荒涼,甚至被清一色的現代樓房所佔據,先輩們居住的古村落已實屬罕見了。所幸在陝西留壩縣的許家山還隱留著一個古老村落,2019年被國家住建部評選為“中國古村落”。一個天朗氣清的冬日,我們探訪了江口鎮許家山村,這是一次感懷鄉愁之旅……
從江口鎮柘梨園街上透過244國道上行一公里處,有一座飛架於紅巖河上的百米鐵索橋。過橋後穿過田園間的道路,來到形似筆架的翠綠山岩下,兩山對峙中僅有幾米寬的山口可進入溝內,只見一條萬古流長的小溪從溝裡潺湲流出,匯聚於紅巖河中。
溝深狹長,山勢逼窄,只有丈多寬,一條小路沿小河溝蜿蜒而上。河溝兩旁野竹婆娑,山上林木蔥茂,畫眉鳥成群飛舞鳴唱。行走十多分鐘後,眼前山巒豁然開朗,只見一處環狀平緩的黃土坡地形呈現在我們面前,黃土山巒之間直徑達千米寬,形似一把偌大的藤椅安放在這裡。“椅坐”處建有十多座土木結構的民宅,這些民宅高丈八頂九,寬階沿、木門窗,木板樓,這處群山懷抱中的村莊就是許家山。
一座座老式民房儲存完好,它遠離塵世,因只有過鐵索橋才能進入村裡,所以沒有車輛穿梭的喧囂,沒有鋼筋水泥的衝斥,便成為深藏在秦嶺南麓腹地的一位隱者,更像是一處與世隔離的桃花源,顯得十分清幽恬靜,只有時而傳來清晰悅耳的鳥鳴聲。沿古村落小路上行百米遠的低凹處有一口古井,是這裡祖祖輩輩人們的生命之源。十多年前各家都通了自來水,古井雖然閒置,卻依然清澄可鑑,映照著古往今來的歲月。
我們來到一家院子坐在寬暢的階沿上,一位窈窕女子熱情地端上茶來,主人張明和介紹說這是他女兒,已從大學畢業在家複習準備報考公務員。在同張明和交談中得知:許家山共住有18戶人家,都姓張氏。我問到:“名為許家山,何故都姓張?”他說:“幾百年前是姓許的家族在這裡住,就叫許家山。許家在這裡住了多年發了財搬遷去了關中,來了張姓在這裡已居住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
據說,村莊四周山坡上的梯地有300多畝,大多是“農業學大寨”時期整修的梯地。這裡黃土層深厚、土地肥沃,糧食產量較高。大集體時,許家山年年超交公購糧,生產隊裡儲備糧豐足,春荒不接時,山下的生產隊來這裡借糧度荒。現在這些環繞山腰梯地裡十多年前都栽了從雲南買來的核桃樹苗,樹雖然長大了但總是不結果,這也許就是“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原由吧。加之青壯年都去了城市打工,平展展的梯地就少有人耕種了。
同行的陳偉說,張明和家存有一塊清代的古匾。我便問主人可否看之?他引我登上板樓,只見靠山牆處立有一塊長2米,寬1米的牌匾,正中刻“長髮其祥”四個大字,右上方豎刻兩行題序:升用知府特授留壩撫民分府隨帶二紀録天歲進士張貢老爺武疇新營蕐居恭賀。左下方刻:峕同治十年(1872)陽春三月。其意是:升任為知府的官員,特授予留壩撫民分府已有兩次授獎記載的貢生張武疇,修新房屋賜予此匾予以恭賀。這塊古匾證實了張家祖先在這裡已居住有150年的歷史了。
許家山的平緩坡地從何時開始耕種?清代編纂的《留壩廳志》無有記載,但從《三國志·蜀記》中可予推測: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伐魏率10萬大軍從褒斜道進軍,因街亭失利退軍時,派趙雲、鄧芝率3萬軍士駐守褒斜道上的赤崖一帶屯田,既是為了防守魏軍攻入漢中,又在這一帶開地種糧做二次北伐的糧草籌備。赤崖位於紅巖河的下游地段,河道兩邊山岩陡峭如削呈赤色故名,這一帶河流兩岸川壩不甚寬闊,3萬軍士沿赤紅崖河岸紮營應有10多里之長才夠。許家山距赤巖僅有兩公里,這片幾百畝的緩坡土地,很可能是趙雲當年率部下開墾耕種,距今已有1700多年了。
坐在張家階沿前方遠眺,對面約200米處的山脊樑上,一棵高大的松樹,像一把翠綠巨傘撐開挺立,分外顯眼,一條山坡環路直通山樑。走近這棵古松,其形態奇偉,樹幹需三個大人雙臂合圍。樹中長出九根直徑達一尺多粗的枝幹,向四面八方撐展,虯枝揮舞,像九條巨龍凌空騰躍,仰望蒼穹;有的手臂相牽,不離不棄;有的相聚而立,蓬勃向上;有的匍匐著地,親吻大地。
村裡老人講這是棵一千多年的古松,斗轉星移、歲月更替,古松飽經了露冷霜寒、乾旱酷熱、狂風暴雨、電閃雷鳴的洗禮,它從容應對,歷練得如此蒼勁挺拔、氣宇軒昂,彰顯著極其旺盛的生命力。
這古村、古匾、古松,山巒、小溪一切都是那麼的古樸悠遠,似乎也覺得那麼的親近和熟悉,它們默默地在這裡悲歡抗爭、等待守望,述說著千古變遷的故事,期盼著世外來客的心靈共鳴和資訊傳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