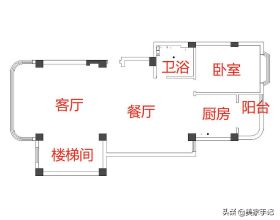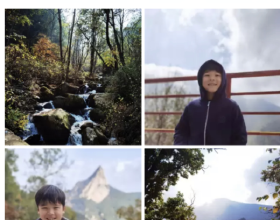明人宋應星在《天工開物》序的開篇即劈頭一句:“天覆地載,物數號萬,而事亦因之,曲成而不遺……”
天下之大,人窮其一生,也走不完的路。美國諾獎作家約翰·斯坦貝克在其《橫越美國》一書的封底他橫越美國的地圖邊上留下一句話:“世界是一本書,不旅行的人只讀了一頁。”
國人出境遊成為熱點之後,歪果仁(外國人)遊中國的遊記書籍遂成熱門讀物。幾年前窩在重慶涪陵教英文的美國人何偉出了本《江城》,投放市場,大受歡迎,繼而出了《徒步中國》、《甲骨文》、《奇石》等書也一路熱銷。
新近,美國熱門旅遊作家保羅·索魯《搭火車旅行記》,有了中文譯本,叫《在中國大地上》,一下又成了讀書界的熱門話題。用自己的眼睛看不過來,用別人的眼睛看自己,看看別人眼中的自己的樣子,別有意味與情趣。
保羅·索魯
保羅·索魯是個熱門旅遊作家,一個美國人,靠一支筆漫遊世界,居然惹得很多國家都花錢顧他到本國旅遊,然後讓他寫觀感、遊記,藉助保羅·索魯的眼睛看自己,從而招徠更多的遊客,以促進本國旅遊事業的發展。在國內,我們稱此等文字叫“軟文”。顯然,保羅·索魯的筆是很有號召力的。
保羅·索魯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期兩度赴華,他興致盎然地搭上綠皮火車旅遊,穿越歐亞大陸,經前蘇聯、內蒙古,而進入中國大地,這本《在中國大地上》即是他在中國旅行的文字與情感的結晶。索魯來中國不是“僱用”,他是被誘惑的,他書中第一句就開宗明義寫道:“中國大得令人稱奇,幾乎自成一個世界。”這麼大一個世界,誘惑他一路“坐鐵公雞”(索魯稱火車)奔波,他周望四處,又筆走龍蛇,一如他在書中所引法國象徵派詩人波德萊爾詩句“真正的旅人只是這些人,他們為走而走”,“他們並不管為什麼,總是說‘走’!”一過內蒙二連浩特,迎面遇見了中國人的笑臉,他被這笑臉感染,寫道:“很久沒見過別人笑了。蘇聯人從來就沒笑過。我要把這拍下來。”遂又記起“蘇聯的陰鬱、蒙古的貧乏和波蘭的戾氣,那些自我否定又貪得無厭的人民,那些糧食短缺的窘況,還有那些破破爛爛的汽車……”
因而,一進北京,他隨即感慨:“整個城市比以前更大、更吵,而且更加明亮和繁榮。”他二次遊北京之後,更大發感慨:“整個國家比以前更加青翠蔥鬱,顯然也更加歡快和充滿希望。”保羅是個愛說實話的遊客,他眼光刁鑽、口味挑剔、說話刻薄、行文尖銳,他去英國旅遊後撰文罵得英國人直跳腳。罵了,英國人仍給他出書,並頒了他一個英國旅遊文學大獎,好像就為他一個罵。當然,他看中國眼光也很挑剔,罵服務人員的“冷漠無情”,“官僚體制往往帶有許多虐待狂的意味。”書中很多刻薄的文字,中文版照單全收。中國自然敞開了大門,就不怕人興風作浪,何況一個挑剔的作家。
不過,說到底索魯對中國還是很客氣的,他到上海,正趕上上海城市大建設的時代,到處是工地,到處是打夯機的聲響,到處是噪聲,那是八十年代中期特有的城市聲氣。於是,他的旅遊生活也被帶入這種聲氣的節奏,“我的生活節奏被一種粗暴蠻橫的噪音所主宰。中國!——中國!我呼吸、走路和吃飯的方式都被受到了影響:雙腳隨著它的節拍收放,勺子也隨著它的節奏起落。中——國!中——國!中——國!我還按照這樣的節奏吐字說話,寫字時會有規律地停頓,就連刷牙時都能發現牙刷在跟著打樁的節奏聲擺動。”
他寫到上海的英語角,碰到一雙雙對外面世界的渴慕的眼睛,索魯也參與了學英語者的交流,並由此謀的一所夜校英語老師的職位,更加深入地介入了上海市民的生活,一種人人昂揚向上的生活。當然,他也不禁對中國人惡習的揶揄,比如隨地吐痰:“中國人的吐痰卻遠不及他們清嗓子你那樣讓人難受;他們猛咳一生,500碼之外都能聽見,跟雨季時下水道排水的聲音如出一轍,而吐痰只是這種行為所帶來的煞風景的結果而已。”之後,索魯南下廣州,走去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前沿陣地,之後,西北、西南、東北,他坐著火車幾乎將整個中國遊了遍。因本文篇幅所限,不再一一追記,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索魯一觀,想來會從別人眼睛中看到一個新奇的自己。
索魯說:“旅遊文學也可以說是一種非主流的自傳形式。”
故而,作者將自己置身於整個旅程的記述之中,將其喜怒哀樂也一併傾斜而出,除了給本土讀者陌生化異樣的驚奇,讓本土人對已爛熟而已至麻木的生活,一經外人發現和指出,突然有一種會心的驚喜與欣悅。
我想,這也是目下旅遊文學大行其道的真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