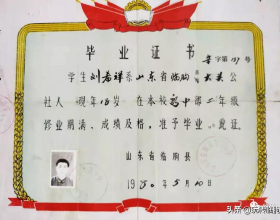第一章
下午三點,太陽直射在金都市中心的鄭州路上,寂靜而又空蕩。
鄭州路是一條小路,商鋪不多卻很熱鬧,道路不寬但四通八達,只是此刻彷彿燃燒了的空氣讓先前逗留的人們沒了蹤影。
路邊的磁帶鋪里正放著一首火爆舞曲《路燈下的小姑娘》,“親愛的小妹妹,請你不要哭泣,你的家在哪裡,我會帶你,帶你回去,哦…,不要不要悲傷,哦…,不要不要哭泣,我會用我的愛溫暖你的心靈……。”
店老闆是一個二十八九歲的小夥子,頭髮梳理得一絲不苟,油光可鑑,整個人的扮相看上和這條老街不太相襯,此刻他正在興致勃勃地追擊著一隻蒼蠅,一邊還隨著音樂節奏扭來扭去。
馬路對面的大槐樹下面,這條街道上最為著名的高老二正躲在樹蔭底下透過樹葉看天。
只見他頭靠樹幹,嘴裡有氣無力地念念有詞:“一朵紅花紅又紅,劉胡蘭姐姐十四歲,從小生在舊社會,長大是個女英雄,叛徒叛徒蒲志高,你是人民的狗強盜,你是人民的狗強盜。”
高老二先生之所以出名,其一是因為他前些年遭遇到了專政強有力的問候,導致精神異常,由一位儒雅博學的大學講師變成了瘋癲在街頭的精神病患者;其二是他神經後更加好學強記,在四處遊蕩中學習了一肚子的兒歌童謠以及俗言俚語,常常立在附近街頭,時不時的唱上幾句來兩段,讓人覺得既新鮮又好玩,所以遠近聞了名。
大槐樹的另一側,穿著白褂子的白大媽在白色的太陽傘下伏在白色的冰棒箱上打著瞌睡,她身後是一間門臉兒不大的腳踏車修理鋪。
鋪子裡邊李澤星師傅的兒子李多強和他的同學錢廣,正蹲在後屋的地上往鋼砂槍裡填火藥,鞭炮的碎皮紙屑在腳邊撒落了一地。
中午時候楊布拉過來告訴李多強說,昨晚你在白雲觀附近砍傷的那幾個小夥,已經知道了你就住在鄭州路上,今天已經約好了人,今天下午就殺過來找你的麻煩。
楊布拉還說,給那幾個小夥來幫忙的是西站曾經威名赫赫的羅建華,羅建華揚言一定要替他朋友的兄弟討個貨真價實的公道。
李多強知道楊布拉說起的這個羅建華確是很有名,去年這個時候剛從新疆坐完監獄回來。此人在83年嚴打以前號稱“西站四傑”之一。其人傳奇故事一大筐。傳說最廣的是他曾在西站什字獨自一人提著一把馬刀,一舉砍翻了橫霸多年西站的何建國,當時何建國兄弟一夥七八人,個個帶傷掛彩,於光天化日之下在警察崗樓下人仰馬翻,好不狼狽,多年混出來的名聲就此掃地。
這件事後有好事者送了外號“今世孟賁”給羅建華。
這個有外號有出處。是他千年以前的本家英雄羅士信之稱號,羅世信乃隋唐演義裡的第一猛,與第一條好漢西府趙王李元霸之武功不相上下。
何建國乃金都地界上最早幾個混出名聲的社會大哥之一,斯人在天安門的接見中振臂高呼過,在武鬥中衝鋒過,還上過山下過鄉,廣闊天地中曾有非常作為。其人與新中國同齡,所以家裡給他起了建國這個極賦正能量的好名字,這個名字很感人,它寄寓了我們自上而下的夢想,也是歷史的見證,幾乎每個城市成千上萬的人都擁有這個響亮的名字,雖然他們的父母對他們寄託了無限希望,希望他們長大後建設這個苦難的國家。可是,以何建國為例,名為建國的這些中華兒郎們,不但從來沒有參與過建設國家的行為,反而自少年時代起一直熱情高漲的投身在打砸搶活動當中,為非作歹禍亂周圍,直至中年以後才逐漸安分了起來,國家沒有毀在他們手裡算是萬幸,直至如今,這些已逾花甲之年的“建國建華”們,一邊領著退休金和收著房租,一邊還大罵著特罵著社會他孃的耽誤了他們,國家虧待了他們。
所謂“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大概齊說的就是他們當中一少部分人吧。
李多強聽完楊布拉的話皺著眉頭想了一會兒道:“羅建華這個人我知道,確實不好惹,當年與我哥齊名,也是個刀斧手。曾經揣著顆軍用手榴彈衝到他現在的媳婦家裡,說是如果你姑娘要是不嫁給我,就和你全家人同歸於盡。姑娘家裡也是老實人,而且在這件事情上多少也有些理虧,因為羅建華當年是為了他們姑娘才坐了幾年牢。所以一怕羅建華狗急跳牆,二怕自家姑娘丟人現眼,百般無奈之下便把姑娘嫁給了他。但是如果是去年的今天他說出這話我可能會怕他,但現在不會了,因為他結婚後不久染上了大煙,有家不回成天和大煙鬼們混在一起,四處坑蒙拐騙,媳婦懷孕都不聞不問,今天卻來替別人抱打不平,找我討公道?他比我能打還是比我年輕?開國際玩笑!一個大煙鬼也來和我叫板!讓他來,我就不信了,放羊的還陪不住打柴的。”
這是一九八七年的夏天。
這一年的夏天有個電影製片廠來到了金都市,要在這裡拍攝一部名為《彭大將軍》的電影。
那一年的金都,文化生活很枯燥,生活在這裡的人們除了看看電影和跳跳舞之外,剩下的也就是打打麻將撲克了。公園只有兩處,分別座落在光禿禿的南北兩山上,兩山從遠處看幾乎沒有什麼綠意,雖然數十年來人們響應國家號召大力植樹造林,但由於氣候的原因收效甚微,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金都人民的山頭上想要綠起來還得有待時日。
也許是太乏味,喝酒始終是他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內容,很多人從小就開始了喝酒,一喝就是一輩子,喝死都不悔,酒好象是這座城市的第二生命,如果離開了酒,這座城市估計就會失去靈魂,變得死氣沉沉。
人們在盼著電影的開拍,他們看到了鐵橋橋頭修好的工事和碉堡;看到了麻袋在四處堆集,各式模樣的火炮和十幾挺輕重機槍已經架了起來;鐵絲網也拉上了,演員們也換好了服裝;還有不少大牲口也被牽到了現場。但就是遲遲不見動靜,他們在焦急中又等了幾個散亂的夜晚。
終於有了動靜,“路透社”訊息說解放軍強攻鐵橋的重頭大戲就在這兩天的天黑以後開拍。
於是晚飯後,亢奮的人們從四面八方湧向西關奔向橋頭,濱河路上萬頭攢動,愛看熱鬧的民族永遠是這樣的激情澎湃。他們排除了萬難,一定要親自去看一看,看一看那個神秘的電影是怎麼稀里嘩啦拍出來的?看一看我們的家鄉金都市,究竟是如何被噼裡啪啦解放的。
老頭老太太們步履蹣跚、搖著圓圓的竹扇、牽著頑皮的孫子去了;伯伯嬸嬸們穿著花花綠綠的大褲頭、搖搖擺擺地去了;叔叔阿姨們一前一後、三三兩兩的去了;哥哥姐姐帶著弟弟妹妹們蹦蹦跳跳的去了;一些大小流氓和想趁著人多撈稻草的壞人們也去了。
假如那一年你正好身處金都,是否還曾留有記憶?你還記得那人潮擁擠的壯觀場面嗎?還記得你娃的鞋子是怎麼擠丟的嗎?還記得你豐滿的屁股在混亂中被誰摸了幾下嗎?還記得你裝著裸體撲克的錢夾子怎麼丟的嗎?還記得在苦苦等待中,電影遲遲不開拍的焦躁難安嗎?如果你當時果真在場,一定忘不了,因為那年那月那些人,還有那個特殊場面代表了一個樸素純真的年代。
人們在摩肩接踵的擁擠中橋頭兩側等待著電影的開拍,久久不願回去,再等等看吧。可是那個革了國民黨反動派命的電影總是不開拍,等待已經變成了痛苦的煎熬,悶熱更使人心情煩燥,有人擠進來又有人擠出去,就在這來來回回踩踏當中,接連不斷地吵罵聲已經開始,此起彼伏不絕於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