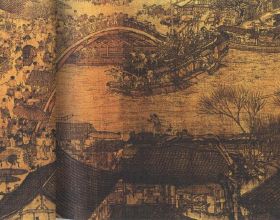經濟觀察報 陳芝/文 馬丁·唐頓的《信任利維坦:英國的稅收政治學(1799~1914)》一書涉及的乃是自拿破崙戰爭到一戰這個時間段裡,與英國財政和稅收制度有關的構建與變化,尤其著重介紹了皮爾與格萊斯頓政府是如何使一直飽受國民抨擊的英國財稅體系,重新獲得公眾信任,並具有更強的資源動員能力以從容應對包括戰爭在內各種危機的挑戰。
在殘酷的拿破崙戰爭過後,只有一個國家,也就是英國的財政經受住了考驗,沒有因為戰爭而崩潰,這是因為英國是少數在絕對主義時代保留議會制度的國家,提供了一個不同利益集團與政府討價還價的上訴渠道,國民對稅收充滿認同,較少抗稅避稅,於是能在不出現政治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增加稅收。
同時,由於擁有複雜的資本市場和信用網路,它還能借到規模空前的鉅款,這與它較晚參與歐陸爭霸有關,而沒有英吉利海峽保護的歐陸國家,在之前三個世紀的戰爭與生存危機刺激下,以及因為專制君主缺乏國會制衡的緣故,無限制借貸,結果普遍負債累累,根本不可能償還債務,不得不反覆宣佈破產、違約,導致信用低下,借貸成本高昂。
再加上光榮革命以來的經濟繁榮,雖然人均稅負是它最大敵手法國的2~3倍,英國抗稅運動卻遠少於法國。於是英國能比其他國家汲取與動員更多的資源,為軍隊與盟友提供源源不斷的支援,最終打垮了強橫一世的拿破崙帝國。
但儘管英國在拿破崙戰爭中笑到了最後,長年的戰爭還是給財政帶來了沉重的壓力,這與它的稅收結構有關。整個18世紀,財政越來越依賴國內消費稅、關稅和印花稅等間接稅,最主要的直接稅土地稅在郡和自治市按1693年時的貢獻而不是現在的地區繁榮程度分配,導致稅收沒有考慮到近百年來主要地區的經濟調整和變化,也沒有反映出18世紀後期稅負水平的增加。這使得稅收收入沒有與經濟增長保持一致,並且稅負的壓力主要壓在窮人身上。
為了應對龐大的戰爭開支,小皮特政府進行了改革,並在1799年引入所得稅,但因為皮特最初採取的稅收評估和徵收方式依靠對個人所有來源收入的綜合評估,這種對收入事無鉅細的評估引發激烈反彈,當時人認為政府這是以調查罪犯的態度對待守法公民。
於是1802年的和平時期所得稅被廢除,在次年重新引入後,改為根據收入的不同形式將其列入不同的稅率表中,不必再彙總所有來源的收入。這緩解了政府與納稅人之間的緊張關係,稅收收入上升。
然而1814年末由於國內收入委員會停止向倫敦委派素來由民間人士充任的負責管理所得稅的外行委任專員,試圖收回控制權,激怒了倫敦市民。對一個侵犯性官僚機構的恐懼,再加上更重要的,對戰爭時期沉重稅負的不滿,引發了強烈抗議,促使所得稅戰後被廢除。
可是所得稅雖然被廢除了,戰爭時期累積的高昂國債對高水平稅收的需要依舊迫切——儘管利率下降了一半,但用來償還債務的金額從不足稅收的1/4上升至超過一半。這使戰後政府陷於兩難:政府意識到繼續徵稅的必要,也希望重新引入所得稅解決債務問題。但迴歸和平意味著大量開支失去正當性,人們同時也畏懼過於強大的中央政府威脅地方自治,打破權力平衡,危害國民自由,國內收入委員會的作為一定程度強化了大眾這一觀點。
債務也提供了反對所得稅的理由,因為所得稅收入被從生產者手中轉移到寄生性的食利者手中,用來供奉一個窮兵黷武、奢侈浪費,充斥龐大的領取養老金冗員的政府,是富裕資本家和地主對實業家與商人的掠奪,而後者自認為是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的支柱與根源。
拒絕支援延長所得稅,還被視為迫使政府節減開支的手段,特別是可以迫使政府減少補貼、消除冗員、壓縮軍事開支和減半支付政府官員薪水。於是對“舊式腐敗”的攻擊,成為戰後政治的核心:在過去,不同利益集團在國會協商,有利於建立合法性並獲得一致認同。但隨著戰後對食利者的攻擊,越來越多人認為國會代表著一種充滿偏見和失衡,為權力階層和既得利益者服務的政治制度。
對此,戰後的利物浦政府努力減少開支,並做出了成效,但單純的節流不足以解決支出問題。英國直接稅比重低於歐洲國家,可國內政局又是反對所得稅的。於是這陷入了一個惡性迴圈,1816年、1819年兩次所得稅引入失敗,使得財政更加依賴關稅和消費稅,打擊了商業和貿易,工人階級消費者揹負了更沉重的負擔。
而戰時債務的沉重負擔以及用累退性稅收支付食利者利息,也使財政制度的合法性在戰後遭到了更大程度的質疑,人們不相信其他納稅人為國家支出做出了應有的貢獻,也不相信國家的花錢方式在不同階級和利益群體之間是公平的。
攻擊政府低效臃腫不民主的激進主義運動於是在1820年代興起,在接下來的二三十年裡發展成憲章運動。在激進人士看來,真正需要的不是強有力的政府,而是一個活躍的公民社會,建立在合作社、工會、互助會和俱樂部等協會文化基礎上。他們還主張貧困和苦難從根本上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本質是稅收制度對窮人的不公,解決方法也應是政治的——為了確保對財政政策和國家支出的控制,應該引入男性公民的普遍選舉權和年度性的國會審查制度。
面對激烈的批評,政府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雖然戰後託利黨政府起初期望在不改變憲政制度的情況下,保持少數政治精英的統治,但在強烈的壓力下還是做出了讓步:1832年國會改革,重新分配選區,取消了衰敗選區的席位;1835年,經選舉產生的地方議會取代了內部產生的自治市議會,並對司法制度進行了改革,減少了英國國教的特權;開支下降,減輕了腐敗。
可這依舊未能重建國家合法性,而且在廢除穀物法對地主集團的保護、賦予成年男性普選權以使工人階級控制國家的壓力下,1830年代的公共抗議活動不減反增。
在這個背景下,新一代的統治精英登場了。作者指出,與老托利黨人不同,皮爾的保守黨政府認為,保持政治秩序和保護財產的最好策略,是制定能夠公平對待各類財產以及有產者與無產者的政策,透過限制國家開支,儘可能使國家不參與經濟利益之爭,就可以保護政治精英不受挑戰,並把國家塑造為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公平仲裁者。政治家應當克服個人貪婪和利己主義,應該拒絕利用國家透過打壓一個利益群體以支援另一利益群體的誘惑,無論這個利益群體是尋求保護的商業組織,還是謀求稅賦減免的社會團體。
這一觀念意味著國會在財政制度中的角色發生了轉變,在18世紀,國會是解決對抗性控訴的論壇,但在維多利亞時期,國會變為公共支出的審計員。
新一代人開始重建國家合法性與信任感,第一步還是減少開支,除了透過刺激經濟增長以減少政府稅收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和削減國債規模外,政府還採取了一些約束政府支出水平的限制措施,很多措施在漢諾威時期就已存在,現在被重新提起,並且要求更嚴格了。
結果雖然導致公共開支削減過大,國民福利下降,城市基礎設施、大眾教育、濟貧支出嚴重不足。但好處是政府開始重建話語體系,重建拿破崙戰爭後被嚴重破壞的對公共行動的信心和對國家的信任。在此基礎上,英國政府構建了一個詳細且技術性的會計準則,以實現國家中立和公共責任,縮減開支,保衛自由,並在大眾民主的時代約束為討好選民,許下種種不切實際諾言的政治家,做到同時限制國家和選民,使他們富有責任感且厲行節儉。
這一準則早在1830年以前託利黨就開始規劃,但到格萊斯頓時才成為一個詳細定義的制度。
首先是堅決反對稅收擔保,禁止指定將某種稅收用於特定用途。18世紀採用稅收擔保是建立人們對稅收制度的信任,使之相信政府有還本付息的能力。然而現在人們意識到這會導致政府職能的膨脹,使每種服務和功能都受到一個具有特定目的收入源的保障。
1857年,公共收入專門委員會建議“整體預算”制,主張稅收應是統一的,應當視為一個完整的資金池,與徵稅目的相分離。《1866年國庫和審計部門法案》正式任命一位總審計長,由其負責監督所有收入部門都將全部收入交給英格蘭銀行,這些收入在英格蘭銀行形成一個單一基金,而不再指定特定稅源的稅收用於特定目的。所有款項都從這一共同基金中支取,用於支付各個部門的支出,任何盈餘都要上交國家債務委員會。國家從各種渠道獲取的收入都集中到國庫,而不是再分散為多個附屬子基金,下院透過投票決定對某一特殊目的的“資金供給”。這使得國會可以直接控制支出,防止支出部門為了部門利益拼命多花錢,能清楚地掌握政府開支的總體情況。
其次是禁止相互調劑資金,即不可以把某一專案的結餘資金調劑用於另一個預算專案,這會導致量入為出,使支出水平不斷攀升。而這依賴於建立統一簡化採用複式記賬法的賬戶體系,讓財政部門重建拿破崙戰爭時失去的對支出部門的控制,不再任由各個部門自行管理具體開支,使賬戶中的錢款從徵收到最終用途都可以被追蹤,對公眾和納稅人來說,可以很清楚地知道錢從哪裡來,以及花到哪裡去了。
接下來就有必要讓國會每年對每項特定支出進行投票,支出計劃不應該跨年度,而國會需要時刻警戒行政部門的擴張野心。但為了排除利益集團的影響,稅收法律應儘可能一般化而不是特殊化,稅務機關沒有執行上的自由裁量權,如果政府想要鼓勵某些活動,應該透過外在的補助方式進行,並且這種補助要受到國會詳細審查,預算也由財政大臣單獨制定,在預算被提交給國會的前一刻,財政大臣才將預算作為既成事實向內閣進行說明。
最後為了避免財政大臣將可能出現的結餘留到大選時,透過減稅的方式討好選民,一個新的財政公約規定,任何結餘都不得結轉用於下一年。為了減輕國債負擔,自1829以來,所有結餘都被轉移到了償債基金,以保持國家信用,確保戰爭時期年度稅收不足時,公眾會借錢給國家。同時政治家一方面嚴格限制新增借款,另一方面努力償還既有債務。在這個過程中,國債從英國自由的威脅者,逐漸轉變成國家安全的守護者。在麥考萊的筆下,國債變成了繁榮的源泉和英國自由的保障,是商業社會中守信與節制的體現,因為政府會謹慎公正地處理借款,這得到了19世紀下半葉人們的認可。
作者指出,透過這些方法,利維坦被束縛了起來,專業的會計程式和下院的年度投票表決,逐漸發展成重要的憲政原則,這對英國的自由和國家認同是必不可少的。格萊斯頓時期,年度預算成為一件頗具戲劇風格,或者說頗具宗教儀式感的事情。格萊斯頓認為,國家財政是英國自由的基礎,並且依賴於國會對所有公共支出進行詳細的審查。行政審查、國會程式和洞悉英國限制支出誘惑的歷史,作為格萊斯頓財政憲法的說辭影響至今。
透過逐步重建的對政府的信任與認同,皮爾政府在1842年重新引入的所得稅,開始長期存在,並於格萊斯頓時期被人們接受。這大大改善了稅收結構與底層人民的處境,由於經濟的繁榮,所得稅的負擔又保持在比較低的水平。
這使得政府在日後能夠課徵遺產稅,甚至推行了累進位制的所得稅,在財政上獲得了巨大的自由空間,於是在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財政制度支撐一場世界性衝突巨大資金需求的能力強於其他任何參戰國家,英國政府建立在對國債持續償還上的良好信譽,使其在緊急狀況時一如既往地得到來自全世界的大量借款,提高稅收的代價也低於其他國家。
可以說,在穀物法廢除後,政府逐漸建立國家在各種利益集團之中中立的形象,越來越透明的會計技術、支出的持續下降和國家債務的減少使人們相信政府是公正廉潔的。19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政治動盪,於19世紀50年代之後逐漸消弭,攻擊政府腐敗、臃腫被視作過時迂腐的觀點,激進主義的風潮渙然冰釋,被體制收編,不再有剛性的激烈對抗。
然而令主張小政府的格萊斯頓意想不到的是,也正是因為他的這份成功,使人們日益接受利用這個高效廉潔的政府機器為人們謀利的觀點,並在19世紀90年代起付諸實踐,歷經兩次世界大戰,曾經以小政府為傲的英國,率先建立起“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這不得不令人感慨歷史的戲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