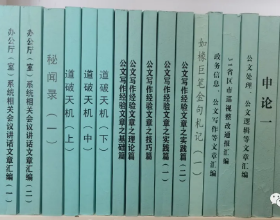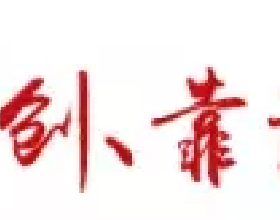作為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一名中國女粉絲,我萬分高興在許曉雯的詩集《花知道答案》中找到一個探討“輕”的青年女詩人。“輕”原指古代的一種車,特點是輕便,後又引申為“重量小”、“程度淺”、“不重要的”、“看不起”等諸多意義。總體來看,即使作為“重”的相對概念,“輕”依然是不敵“重”的。我們看到書店裡無數討論道德、宗教、人性等分量十足的文學名著,而那些生活化的,園藝、家庭、旅遊則被放置於通俗讀物的一角。在歷史悠久的男權社會程序中,即使在女權主義盛行的今天,“輕”依舊甩不開女性這一存在。可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詩人在自序中提到,義大利當代作家卡爾維諾說:“文學是一種生存功能,是尋求輕鬆,是對生活重負的一種反作用力。”因此難道作為女性的我們不能透過探討“輕”來了解自身生活,直達女性生命本身的含義?我正是懷著這樣的好奇和期許進入了許曉雯的詩歌世界。
《花開花自開,一切無因由》這首詩中,寫了一朵小野花遵從大自然的攝理,花開花落的生命過程。“一株野草、一朵小野花/春天來了,綠也就綠了,紅也就紅了/秋天至了,它也就敗了”,這種白描的手法,既無“當春乃發生”的感動,又無“感時花濺淚”的悲傷,只是客觀敘述野草、野花不卑不亢,自自然然的生命。我們彷彿可以窺視到,詩句背後站著一個純真美好的少女,對存在的一切繁榮亦或殆盡都樂觀得接受著。然而這種樂觀又不是盲目,無知的。“綠不知道為何而綠,紅也不知道為何而紅/黃不知道為何而黃”,詩人用一種否定的語言,似乎在表現著花草的無知,但是“不知為何”中暗含著“為何?”這一思索,對意義的懷疑,若不是詩人的揭示,怎會浮現在普通的花草身上?這似乎又是困擾米蘭昆德拉的重大主題:“人生不過是去往何方與來自何處的事情。”詩人接下去又向我們解釋她的理由,“反正春天去了它還會來/秋天到了也還會走/想開了就開,想敗了就敗/來無所來,去無所去”,這不禁讓我想到昆德拉深愛之尼采的“永恆輪迴”和“最沉重的負擔”的理論。末了詩人筆鋒一轉“沒有因由為什麼,也不需要為什麼”。這樣的表述,不禁讓我聯想起,日本國民詩人谷川俊太郎《樹》裡所描繪的,“樹正因為是樹,樹才能夠站在這裡,而樹為何物我卻無從所知。”所不同的是,年輕的女詩人沒有絲毫的懊喪,像野花野草一樣固執,然正是這樣的意氣風發,打破了哲學思索的窒息和寸步難行,體現詩人生命的坦誠、瀟灑和叛逆,在語言表現上又不乏果斷和俏皮。
《輕、重》這首詩只有短短三句,“大山舉起來/一片落葉在這山上的落地和飄飛/絲毫不會影響山的巍峨和沉重”。雖然短小但是我們不禁會問,是誰在舉起大山?落葉對於山,就像花草對於四季,而運轉它們的,可想而知是高於自然界之“自然”。因為太過渺小,似乎只剩下皈依。之所以可以皈依,又正是由於那渺小和“輕”。“野草”、“野花”和“樹葉”都是詩人在“輕”中的表象。正是因為輕如一片葉,輕如一朵野花,才可以將沉重的人之生命寄託於無窮的自然攝理之中。“草木無言,但又如史詩般奇妙/樹葉在天地間搖曳成一行行詩句/人類難以參透其中之幽微精深/在植物面前顯得尷尬而笨拙”(花知道答案)。這便是原因,因為人類的笨拙和大自然的神秘,所以詩人選擇一種謙卑的姿態,“我從來不敢在一片葉子上放最後的希望/樹葉的來去只為大地獻祭”(樹葉的來去只為大地獻祭)。
然而在這整部詩集裡,詩人除了喚起被“輕視”的花草、滴露、月光、溪流、雀鳥等這些輕物意象所散發出微弱而燦爛的光芒以外,同樣將目光投向了“輕”的另一種表象——“塵埃”。“假如靈魂是寵物/你希望你的靈神是什麼樣的精靈/猴子、貓、鼬鼠、兔子、狗熊、蛇、蝴蝶/或許是塵埃/飄忽不定散落在星際(十一行詩)。詩人不僅探討“輕薄”的生命,而且把這種探討延伸到超出時間以外的“靈魂”之上。詩人認為靈魂也許可以是“塵埃”。可是所有的“塵埃”都是詩人“輕”的代言嗎?顯然不是。“黃金羅盤打開了——/我們要消滅有毒的塵埃”。又如,“萬物的屬性、氣味、性質都不會無限誇大/它們在秩序的軌道上/用自己的方式成為自己的神/而一些有思想的個體卻因為吸收太多塵埃/成為了怪物”(魷魚不會變成琵琶)。可見,“塵埃”是有好有壞的。不難看出,詩人雖然可以瀟灑得拒絕詢問形而上的“為何”,卻用一種辯證的態度對待存在。她讚美有生命的“輕”,而對失去生命,成為“塵埃”的“輕”保持著清醒而審慎的批判態度。但是詩人終究對人的未來有著一顆悲憫的心,她相信,“花非花,霧非霧/穿過迷途,路的盡頭是否是晴空/但應該相信路一直敞開著” (路的盡頭是晴空)。我想,儘管前路未知,但從那些“輕薄”的生命中,詩人提取到最寶貴的財富——一種敞開、樂觀、生生不息的態度。
此外,本部詩集中仍有許多可圈可點之佳作。《影象與花朵》中詩人如是說:“事物的擴充套件、伸張/是靠氣執行往來的/宇宙是無序的,大自然的紋樣/也是千變萬化的/花朵是影象,影象也是花朵/花朵不是影象,影象也不是花朵/沒有絕對的是,也沒有絕對的不是/沒有絕對的完美,也沒有絕對的醜惡/沒有條理,也沒有章法 ”。詩人用一種看似“顛三倒四”的話法向我們展示出一副野生的,無秩序的,不完整的畫面,只因她觀察到生命本身的混亂和盲目,但讀者又不難體味出,詩人對所有“不確定”性的敞開和接受。《焦慮》中,詩人說 “焦慮 是鐵皮屋上的螞蟻”,用螞蟻(輕)在鐵皮上這一形象來比如人的焦慮(重),不得不說入木三分;而在《黑色覆蓋黑色》中,詩人又說“有人用黑色油彩/在白色的牆壁呈現各種圖案/色塊、線條在牆的肌理上蔓延/直至思想、精神滲透進牆裡縫合”。黑色的油彩(輕),白色的牆壁、肌理(重),如此詩人的思想正透過輕的表象融入到重的精神之永恆裡。
王小波在《青銅時代》故事的結尾說:一個人只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他還應該擁有詩意的世界。許曉雯正是在蒼白而平淡的“小”生活裡,用她的“輕薄”和富有靈感的詩性語言,為我們描繪出一個詩意的世界。我相信,她的詩歌會為當代寫作中普遍性的蒼白,帶來新鮮的血液和活力。(來源:中國詩歌網,作者:杜玉)
杜玉,91年生,日本東京大學現代文藝論研究室博士生在讀,專攻日本近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