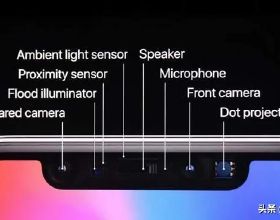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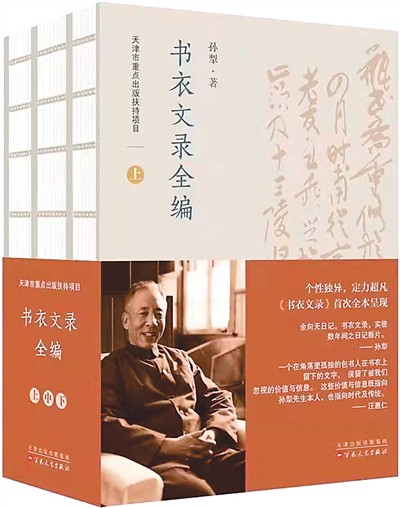
我和孫犁先生沒有過交往,這對我來說,是個無法彌補的遺憾。但換個角度,我現在時常這麼寬解自己:在精神層面我們還是相逢又相識了。並且,在這一過程中,至少近10年來,我因他保持了自己殘存的想象力——我在編輯《書衣文錄全編》時,感覺是非常奇妙的,我總是想象在前,然後在他的筆跡裡辨認出一個似曾相識的老人,我有時能聽見自己輕嘆:他果然如此,他果然如此。
前不久看四川作家馬平的一部長篇小說,裡面的主人公也是常常聽見自己在唱或者在說。世界足夠安靜,自己才有機會將自我物件化,才有機會反觀復觀自身,才有機會聽見自己的“思想”。書衣文錄中的孫犁,是自己收聽、反觀、復觀自身的孫犁。
書衣文錄中我們所能見到最早的段落,寫於上世紀60年代,那時的孫犁才50歲出頭。但是從那時起一直到他終止寫作,他的心理年紀和他自己感受中的身體年紀,給我的印象是老邁衰朽。他的體質應該不屬於強壯型,時常患小病,但絕不至於弱不禁風。但他總是說,自己老了,從中年說到晚年。劉禹錫酬白樂天詠老,首尾皆傳世佳句,“人誰不顧老,老去有誰憐”“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始於哀傷,止於振作,這可能適用於多數人的心理需求,卻不適用於孫犁。孫犁之嘆老,別有所指。這是屬於孫犁的時間自治,他有能力讓有所不為的晚境提前到來。在長達60餘年的寫作生涯中,孫犁的生活經歷了太多的大變化,有所不為的孫犁,透過時間自治,讓晚境另有所為,讓晚境別具隻眼。
時間自治,在寫作者那裡得以實現,紮實的現實的也許是最終的途徑是語言自治。孫犁是一個有能力呈現語言自治的作家——在現當代作家中,這樣的人並不多。書衣文錄中大量的段落是關於讀書的——藏書,愛書,最重要的,他真讀書。在天津市和平區多倫道的一個雜院裡,幾十年中,孫犁老人做得最多的事情是:讀書,購書,委託友人購書,修整舊書,包書,記錄讀書心得。應當說,從《白洋淀紀事》到《風雲初記》《鐵木前傳》,在革命作家群當中,孫犁已經顯示了他獨異的敘事天賦,尤其是在《鐵木前傳》裡,九兒、滿兒,這樣的女性,像未解之謎出現在孫犁的逸筆之下。如果止於此,語言自治意義上的孫犁遠未完成。他非常自覺地看到,僅僅依靠天賦,寫作難以為繼。所謂語言自治,當然不是指圍觀修辭,更不是以自我標榜來自證所謂個性,它是指在充足思想資源與充分技術準備下,寫作者最終建構言語系統的能力。在書衣文錄中,我看到一個困頓中謙遜的孫犁,他沿著以下幾個路徑在補課,四庫全書是一個路徑,魯迅薦讀是一個路徑,興趣雜項是一個路徑,蘇俄及法國文學是一個路徑。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一個經由命運磨礪、經典養育而使獨異敘事能力獲得新生長的孫犁出現了——他已經完成了語言自治,世界與生活,凡經他之敘述,便成為他之世界他之生活。
書衣文錄有著強烈的日記性質,藉此,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生活自治的孫犁。他是個倔強的人,奇怪的是,同時他能看見自己有些“壞”的脾氣,書衣文錄中人生反思的段落比比皆是,但是,他沒有改變自己。有個阿姨,幫他料理生活雜務,很多年了。某日,孫犁忽然生出一個念頭,是不是可以換個幫忙的阿姨。第二天,孫犁就把這個念頭和阿姨說了,但一開口,孫犁就哭了,阿姨於是也哭。阿姨沒有被辭退。他怎麼能改變自己呢,他一生的遭際,都是為了不改變自己,不改變這赤子之心。
(作者系百花文藝出版社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