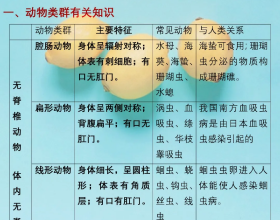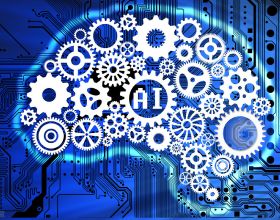【序跋】
作者:張莉
很喜歡汪曾祺的一篇散文《跑警報》。寫的是西南聯大的戰時生活。那篇文章裡說,有同學善於跑警報,只要看到萬里無雲,不管有無警報,就背了水和吃的,往郊外走。但大部分同學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對跑警報太有經驗了,從來不倉皇失措”。跑警報的時候,很多人會帶書或論文草稿,也有人會帶金子或情人的信。對於青年男女而言,跑警報還是個談戀愛的機會。但也有不跑警報的。有位女同學,一有警報就洗頭,因為別人都走了,鍋爐房的熱水可以敞開用。“另一個是一位廣東同學,姓鄭。他愛吃蓮子。這位老兄聽著炸彈乒乒乓乓在不遠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圖書館旁的鍋爐上神色不動地攪和他的冰糖蓮子。”文章最後,汪曾祺提到中國人身上的“不在乎”精神,而這種精神,“是永遠征不服的”。
汪曾祺的文字有一種神奇的召喚力,短短4000字,塵封的歷史從他筆下躍然而出。他甚至寫到了跑警報時小販賣的麥芽糖和炒松子如何好吃,以及空氣中的氣味。歷久彌新的文字如此珍貴,一代人的戰時生活記憶由此留存,又或者說,珍貴的民族記憶以一種生動的方式在汪曾祺筆下顯影、復活。再過三十年,這些記憶又用影像的方式被重述——電影《無問西東》中西南聯大的跑警報片斷,就來自這篇散文。
我由此想到作家們召喚記憶的方式。召喚記憶的方式有許多種,比如衣物、氣味、音樂、繪畫、影像等等,但散文,恐怕是最具魅力和最讓人心馳神往的。白紙黑字,作家神奇地構建起一個空間:在那裡,有我們真實經歷的過往,那些氣息、聲響、歡笑以及痛苦。在這部《即使雪落滿艙:2020年中國散文20家》裡,20位寫作者以卓有意味的書寫,分享他們在2020年度對生活、對現實、對歷史的感知。
有一種記憶關於此刻,它們是最新鮮的時代記憶。《疫時回鄉記》裡,鄧安慶寫下2020年春節從北京回到湖北老家的點滴;袁凌在《北漂記》裡平靜地寫下他的奔波,也寫下一個青年的內在成長;《雲彩化為烏有》裡,沈念記下的是一位平凡老船伕的生活,他的蒼老以及無法言說的痛苦;黎戈則記下生活的“平淡之喜”,是越來越清淡的口味,是是枝裕和的電影,是山路上見到的孤獨的樹。
寫下日常點滴是記憶,重新發現生活也是記憶。鮑爾吉·原野的《塞上曲》寫了草原上有趣的事,草原日常在他的筆下成為一種“熟悉的陌生”。《行雲》是關於坐飛機的經歷,那些隨時隨地的奔跑和匆忙最終在周曉楓筆下沉潛,化為一種對生存境遇的思考。
有一類散文關於歷史,是作家對塵封久遠的記憶的重新認知。《黍離》是久遠的詩歌文字,在《〈黍離〉——它的作者,這偉大的正典詩人》中,它被李敬澤重新發現:“喝下去的酒、仰天的笑,其實都有一個根,都是因為想不開、放不下,因為失去、痛惜、悔恨和悲愴,這文明的、歷史的、人世的悲情在漢語中追根溯源,發端於一個詞:‘黍離麥秀’。”《遣悲懷》是李修文的“詩來見我”,這篇文字使我們重新理解悼亡詩。悼亡詩哪裡只是詩呢,它是故人,它是情分,是人痛苦時的“大雄寶殿”。古代詩文是對記憶的一次打撈、一次淘洗,是從民族記憶的寶庫中重新探詢並解釋物之為物、詩之為詩、人之為人、情之為情的秘密。
有一種記憶,關於個人往事。梁鴻鷹的《午後的故事》和王堯的《琴聲如訴》寫的是歲月深處難以忘記的故事,讀來唏噓不已。還有一種記憶浸潤著切膚的痛苦,讓人無法直面。劉大先的《故鄉與異邦》寫到父親臨終的場景,深切的痛苦埋在深處。塞壬的《即使雪落滿艙》寫的也是父親,父親曾經入獄,父親曾經背叛母親,父親曾讓整個家庭蒙羞。寫塞壬與記憶的牽絆,寫她之於記憶的和解、生命的領悟。即使記憶裡落滿了灰塵,即使生命中曾經落滿積雪,終有一天我們也要仰起頭,試著去看天邊的明月。
記憶是掛牽。記憶是糾纏。記憶是輾轉反側。記憶是念念在茲。有許多種方式讓我們把記憶珍藏,有許多種方式將我們的記憶喚醒,也有許多種方式將我們的記憶調亮。如何最大可能地運用一切方式,將我們生命中念念難忘的部分顯影?某種意義上,寫作就是與人類的失憶搏鬥,寫作就是寫作者的一次次“刻舟求劍”。歲月已逝,而作家依靠寫作實現“夢想”——讓時間靜止,使記憶顯影,呈現我們生命中那些彌足珍貴的瞬間,一如汪曾祺寫下《跑警報》。
(本文為《即使雪落滿艙:2020年中國散文20家》序言)
《光明日報》( 2021年08月04日16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