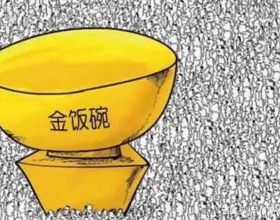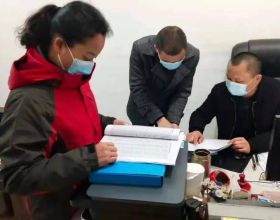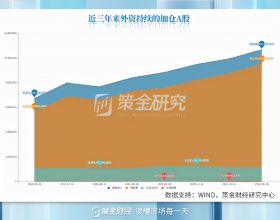我認為文學是吹牛的事業,但不是拍馬的事業,罵一位小說家是吹牛大王,就等於拍了他一個響亮的馬屁。
當小說家妄圖把他的創作實踐“昇華”成指導創作實踐的理論時,當小說家妄圖從自己的小說裡抽象出關於小說的理論時,往往就陷入了尷尬的兩難境地。
當然,並不排除個別的小說家,能寫出確實深奧的理論文章,一般地說、理論越深奧離真理越遠。
對大多數小說家而言,小說的理論就是小說的陷阱。小說理論開始時與小說家毫無關係,也與絕大多數讀者沒有關係。小說的理論產生於閱讀,小說理論的實踐是創作。
最純粹的小說理論只具備指導閱讀和指導創作這兩個功能,但現代的或者是後現代的小說批評,早已變成了批評家們炫耀技巧、玩弄詞藻的跑馬場,與小說批評的本來意義剝離日久。
橫行霸道的新潮小說批評早已擺脫了對小說的依存關係,並日漸把小說變成批評的附庸,這種依存關係的顛倒,使小說理論與小說創作變成了幾乎互不相干的事情。
小說已變成新潮批評家進行技巧表演時所需要的道具,這種小說批評的強烈的自我表演慾望和小說創作渴望被表演的慾望,就使得部分小說家變成了跪在小說批評家面前的齊眉舉案的賢妻,渴望被批評,渴望被強姦。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這種自成了體統的時髦小說批評,終究會因其過分陽春白雪,而走向自己的反面;而返璞歸真的小說批評,會因其比小說更樸素的率直與坦白永遠生存下去。
新潮小說理論操作方式是:把簡單的變成複雜的、把明白的變成晦澀的、在沒有象徵的地方搞出象徵、在沒有魔幻的地方弄出魔幻,把一個原本平庸的小說家抬舉到高深莫測的程度。
樸素的小說理論操作方式是:把貌似複雜實則簡單的還原成簡單的,把故意晦澀的剝離成明白的,剔除人為的象徵,揭開魔術師的盒子。
我傾向樸素的小說批評,因為樸素的小說批評是既對讀者負責又對小說負責同時也對批評者自己負責,儘管面對著這樣的批評和進行這樣的自我批評是與追求浮華綺靡的世風相悖的。
巴爾扎克認為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米蘭·昆德拉認為小說是人類精神的最高綜合,普魯斯特認為小說是尋找逝去時間的工具——
他的確也用這工具尋找到了逝去的時間,並把它物化在文字的海洋裡,物化在"瑪德萊娜"小糕點裡,物化在繁華綺麗、層層疊疊地對往昔生活回憶的描寫中。
我也曾經多次狂妄地給小說下過定義:
1984年,我曾說小說是小說家猖狂想象的記錄;1985年,我曾說小說是夢境與真實的結合;
1986年,我曾說小說是一曲憂悒的、埋葬童年的輓歌;1987年,我曾說小說是人類情緒的容器;
1988年我曾說小說是人類尋找失落的精神家園的古老的雄心;1989年我曾說小說是小說家精神生活的生理性切片;
1990年我曾說小說是一團火滾來滾去,是一股水湧來湧去,是一隻遍體輝煌的大鳥飛來飛去……
玄而又玄,眾妙之門,有多少個小說家就有多少種關於小說的定義,這些定義往往都帶著強烈的感情色彩,都具有模糊性因而也就具有涵蓋性,都是相當形而上的,難以認真對待也不必要認真對待。
剝掉成千上萬小說家和小說批評家們給小說披上的神秘的外衣,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小說,就變成了幾個很簡單的要素:語言、故事、結構。
語言由語法和字詞構成,故事由人物的活動和人物的關係構成,結構則基本上是一種技術。
無論多麼高明的作家,無論多麼偉大的小說,也是由這些要素構成,調動著這些要素操作,所謂的作家的風格,也主要透過這三個要素——
最主要的是透過語言和故事的要素表現出來,不但表現出作家的作品風格,而且表現出作家的個性特徵。
作家的故鄉並不僅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童年乃至青年時代生活過的地方。文學院裡培養的更多是一些懂得如何寫作但永遠也不會寫作的人。
上帝給了你能夠領略人類感情變遷的心靈,故鄉賦予你故事、賦予你語言,剩下的便是你自己的事情了,誰也幫不上你的忙。
遍翻文學史,上下五千年,英雄豪傑、浪子騷客如過江之鯽絡繹不絕,留下的和沒留下的詩篇裡,故鄉始終是一個主題,一個憂傷而甜蜜的情結,一個命定的歸宿,一個渴望中的、或現實中的最後的表演舞臺。
英雄豪傑的故鄉情融鑄成歷史,文人墨客的故鄉情吟誦成詩篇。千秋萬代,此劫難逃。
我認為文學是吹牛的事業,但不是拍馬的事業,罵一位小說家是吹牛大王,就等於拍了他一個響亮的馬屁。
放眼世界文學史,大凡有獨特風格的作家,都有自己的一個文學共-和國。
威廉·福克納有他的“約克納帕塌法縣”,加西亞·馬爾克斯有他的“馬孔多”小鎮,魯迅有他的“魯鎮”,沈從文有他的“邊城”。
而這些的文學的共-和國,無一不是在它們的君主的真正的故鄉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這些小說缺少一種很難說清的東西,其原因就是這地方沒有作家的童年,沒有與你血肉相連的情感。
有過許多關於童年經驗與作家創作關係的論述,李贄提出“童心”說,他認為:“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有了“最初一念之本心”,就能看到一個真實的世界。如康·巴烏斯托夫斯基說:“對生活,對我們周圍一切的詩意的理解,是童年時代給我們的最偉大的饋贈。
海明威有言:“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搖籃。”當然也有童年幸福的作家,但即便是幸福的童年經驗,也是作家的最寶貴的財富。
從生理學的角度講,童年是弱小的,需要救助的;從心理學的角度講,童年是夢幻的、恐懼的、渴望愛撫的;從認識論的角度講,童年是幼稚的、天真、片面的。
這個時期的一切感覺是最膚淺的也是最深刻的,這個時期的一切經驗更具有藝術的色彩,而缺乏實用的色彩,這個時期的記憶是刻在骨頭上的,而成年後的記憶是留在皮毛上的。
而不幸福的童年最直接的結果就是一顆被扭曲的心靈,畸形的感覺、病態的個性,導致無數的千奇百怪的夢境和對自然、社會、人生的駭世驚俗的看法,這就是李贄的“童心”說和海明威“搖籃”說的本意吧。
如果承認作家對童年經驗的依賴,也就等於承認了作家對故鄉的依賴。
這樣的童年必然地建立了一種與故鄉血肉相連的關係,故鄉的山川河流、動物植物都被童年的感情浸淫過,都帶上了濃厚的感情色彩,許多後來的朋友都忘記了,但故鄉的一切都忘不了。
我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寫作的時候,也經過了非常痛苦的、探索的過程。
剛開始遇到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故事好寫,好像所有的故事都被別人寫了,當看到別人寫了一個知識分子題材的故事,突然走紅以後,我再來寫知識分子的題材,馬上就感覺這個題材已經過時了。
當別人寫一個在長江上放排的故事成功之後,我再來寫又感覺到過時了,所以,當時是千方百計挖空心思去尋找能夠寫到小說的故事。這樣的尋找非常痛苦,結果也是很悽慘幾乎找不到。
真正讓我感覺到有東西可寫了,是在1984年我到了解-放軍藝術學院之後。在這兩年之間我覺得沒有學到多少東西,唯一起到的作用就是每個人找到了自我,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能找到。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自己找到了自己應該走的方向,過去我就感覺到,我們的小說還是寫英雄人物、我們的小說還是要寫這樣的傳奇經驗、我們的小說還是應該寫出驚天動地的事件。
感動人,讓人哭、讓人怒、讓人樂。只有這樣一些巨大的、龐大的題材才有可能寫到小說裡去,透過學習其他人的創作經驗,透過聽了很多作家的現身說法,透過大學文學教授們給我們講述國外的很多成功作家的創作經驗。
我突然意識到,實際上寫作就是應該從身邊的瑣事、小事寫起,過去認為不能夠寫到小說裡的很多細碎的,生活當中司空見慣的事情經過文學的手段把它變成文學作品。
觀念改變之後,就如同打開了一扇窗戶,或者說如同在一道河上打開了幾條久被封閉的閘門。
過去認為不能變成小說的很多個人經驗,突然感覺到變成了非常寶貴的小說素材。
我過去生活了幾十年的村莊,過去認為毫無故事,現在感覺每一個家庭都存在著可以寫到我小說裡去的人物,而每個家庭的人物身上發生的故事都變成了很好的小說情節。
村莊的每一棟房屋、每一條衚衕、村後河邊上的每一棵樹木,河床上每一座小的石橋,包括我們田野的每一塊莊稼地,我們生產隊飼養的每一頭牛、每一頭騾子、每一匹馬都可以變成我小說裡的素材。
我在農村生活的20多年,積累了很多很多的經驗,而且是無意累積的經驗。
一時間都堂而皇之地進入了我的作品。這樣的轉變是一個根本性的轉變,這樣的轉變實際上就是文學觀念的一種革命。
我的成名之作就是《透明的紅蘿蔔》。在座的很多朋友肯定已經看過。這篇小說實際上得力於一個夢境。
有一天早上,在軍營宿舍,似醒非醒的狀態下,看到了一片很廣闊的蘿蔔地,一輪紅日從東邊冉冉升起。
從蘿蔔地的中央突然站出來一個身穿紅衣的、豐滿的農村少女。她手裡拿著一根魚叉,然後從地下叉起一個紅色的蘿蔔,她就高舉著蘿蔔對著太陽走過去。
這個畫面非常輝煌也很壯美。我醒了以後馬上對我的幾個同學說,我剛才做了一個夢,我要把它寫到小說裡去。就對他們講述我剛才說的這個夢境。
他們說這怎麼可能變成小說呢?但是有一個同學說,你先把它寫出來我們看。
我用了很短的時間,大概一個星期的時間寫了《透明的紅蘿蔔》初稿,在寫的時候完全依靠夢境是不夠的,就調動了自己少年時期的一段生活經歷。
因為20多年的農村生活經驗裡面,類似的經驗太多太多了。所以自己開始寫,各種各樣的、五花八門的小說都寫出來了,像《爆炸》、《球狀閃電》、《金髮嬰兒》等一批中短篇小說。
關於想象力,我覺得我的想象力確實還是不錯的,為什麼說不錯呢?因為我的想象力是餓出來的。
人在飢餓的時候,特別容易產生幻覺,當然這些幻覺都和食物有關係。所以統觀我的作品,裡面描寫人對食物的幻想的章節有很多很多。
寫吃、喝的地方很多,寫人身體的感覺、肉體的、感觀的地方很多。也有人說,莫言是一個沒有思想只有感覺的作家。在某種意義上,他們的批評我覺得是讚美。
一部小說就是應該從感覺出發。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要把他所有的感覺都調動起來。
描寫一個事物,我要動用我的視覺、觸覺、味覺、嗅覺、聽覺,我要讓小說充滿了聲音、氣味、畫面、溫度。當然我還是有思想的。
我認為一個作家如果思想太過強大,也就是說他在寫一部小說的時候,想得太過明白,這部小說的藝術價值會大打折扣。
因為作家在理性力量太過強大的時候,感性力量勢必受到影響。小說如果沒有感覺的話,勢必會幹巴巴的。
好的小說應該像一條有人氣的街一樣,充滿了各種聲音和氣味,有各種各樣的溫度,讓人彷彿置身其中。
如果不把身體全部的感官調動起來,小說勢必寫得枯燥無味。我的想象力來自於長期的飢餓。
我在上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就被學校趕出來了。我牽著兩頭牛,一個人在田野裡放牧。家太遠,有時候中午也不回家吃飯,就帶一點乾糧,只有牛跟我在一起。
我經常可以從牛的眼睛裡看見自己的倒影。躺在草地上睡一會兒;躺著看天上的白雲;聽鳥叫、聽青草生長的聲音;聞大地散發出的氣味、各種各樣的花草散發出的氣味……
跟大自然的親密接觸,很長時間孤獨地跟動物在一起的狀態,都讓我想入非非。
當我成為一名作家以後,小時候的苦難生活變成了一種寶貴的創作資源和財富。直到現在,我的大部分小說,動用的還是我20歲之前積累的生活資源。
我二十幾歲以後的生活,還沒有正兒八經地去寫。至於想象力,也有外面的東西。
我們山東高密這個地方,雖然離青島很近,但它在幾十年來,一直是比較封閉、落後的。這個地方離寫《聊齋志異》的偉大作家的故鄉,相隔大概兩三百里。
我當年在鄉村的時候,經常聽老人講很多有關鬼神的故事。我就想究竟是蒲松齡聽了祖先說的那些鬼神的故事,把它寫到書裡去,還是我的祖先裡面有文化的人讀了聊齋再把故事轉述給我呢?
我搞不清楚。我想這兩種狀況可能都有。在這麼一個神話鬼怪比較發達的地方,人因為恐懼也會產生想象力。
我們小時候既怕又喜歡聽這種故事,越聽越上癮,越聽越害怕。經常是聽完了故事,誰也不敢往家走。
我的辦法是一出門就高唱革命樣板戲,大聲吼叫。一進家門,我母親就問:“你喊什麼?”我說:“害怕。”
我想任何一門藝術,包括文學,當它發展到一個極端需要變革的時候,無非是藉助兩種力量:一種是藉助外來的力量;另外一種就是在民間尋找。
中國真正的文學,或者說能夠跟世界對話的文學,超越了狹隘的階級觀念的文學,應該是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的。
我們所接觸的西方小說比香港、臺灣晚了整整20年。後來我到臺灣去跟張大春、朱天心這些作家交流,發現他們在60年代讀過的書,我們直到80年代才讀到。
大量閱讀西方的小說,開闊了這批小說家的眼界。比如我當年讀了馬爾克斯,讀了卡夫卡,才知道小說原來可以這樣寫。
我覺得很遺憾,我們高密鄉的很多神怪故事比拉丁美洲一點不差嘛!
到80年代中期,我覺悟到西方的馬爾克斯、福克納、海明威,他們就像鍊鋼的火爐一樣是灼熱的。如果靠得太近的話,我們就被烤掉了,熔化了,蒸發了。
我們必須遠遠地離開他們,必須要千方百計地寫出一種跟他們不一樣的小說來。
這就需要去民間尋找,在民間故事、口頭傳說、民間文化、民間口語裡面尋找,所以說文學豐富的資源還是隱藏在民間。
當然這個民間,並不是指偏僻、荒涼的農村,城市也是民間,它是廣義的、另類意義的民間。
西方的小說對我們的文學觀念,產生了巨大的衝擊。使我們從1949年到1979年這30年來,形成的文學觀念土崩瓦解,作家的思想真正得到解-放。
圖文源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