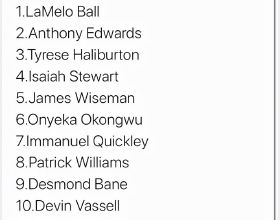渡河東征的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在毛主席親自率領下,分兩路搶渡了天險黃河。十五軍團為右翼,我七十五師二二三團擔任右翼第一梯隊。
我帶著團的渡河先遣支隊來到河邊已經十多天了。早在來到這裡之前,就進行了渡河的技術訓練。渡河的船隻已由地方政府準備停當。現在,我們先遣支隊的主要任務是:繼續詳細的偵察地形,選擇渡河場和登陸點,等候上級命令首先搶渡黃河。
這裡是黃河上游,兩岸都是高山、陡壁,黃澄澄的河水在高山陡壁中間急流直下。時值初春,河兩岸的冰凍已經開始融解,各種形狀、大小不一的冰塊順流而下,河水的吼聲和冰塊的碰擊聲,在兩岸山中迴響。
對岸,閻錫山利用自然地形,從河邊山頭,隘路構築了蜂窩似的地堡群,地堡與地堡之間以交通壕連結,通往縱深的道路都被切斷,並將山崖、地坎都切得壁陡壁陡。閻錫山派了重兵,配置了步重炮,自吹為“攻不破的黃河防線”。
我們到河邊十多天以來,利用河邊自然地形——村莊、溝坎,不分晝夜的隱蔽活動,先遣支隊的每個戰士對兩岸地形都已瞭如指掌,戰士們的勁頭鼓的足足的,每天問我:“參謀長,什麼時候過河呀?”
“團裡怎麼還不下命令呀?”
這四十多個小夥子,是從各營選出來的勇敢、機智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他們的心情我是瞭解的,說實在的,我也同樣著急。究竟什麼時候過河,上級還沒明確指示。
這天黃昏,我們正在渡口研究船隻如何下水的問題,政委的警衛員跑來了,他把我叫到一邊,臉上帶著一種很神秘的表情對我說:“團長、政委請你趕快去!”
我問:“叫我去幹什麼?”
這小鬼嚴肅地說:“我不知道,團長、政委只說請你去。”
我知道這個小鬼的脾氣:一聽說打仗就樂得不知道怎麼好,肚子裡有半句話,不說出來也不舒服。可是有時候也裝得滿正經,不用話套,他不說實話。
於是我故意逗他:“什麼重要問題呀,你看我不是正忙著嗎?明天再說吧。”
這下子,他可著急了:“ 真是重要問題,”
接著又小聲說:“今晚渡河。”
我隨著他來到團指揮所——高村一個窯洞裡。 一進門, 陳錦秀團長和劉震政委就說: “老韋,辛苦了!準備的怎樣?有把握嗎?”
我說:“有把握,大家信心很高,就等著團裡下命令呢。”
接著陳團長說,徐海東軍團長命令,為了保證順利渡河,便於指揮部隊,各級幹部都要到下一級去指揮戰鬥。
我說:“這樣好!我就在一連吧。”
團長說:“要得,我和政委在一營營部。來,對一對錶,現在是七點二十五分,再過一個半小時——九點整開始渡河!”
最後,政委又指示,回去再徹底檢查一下準備工作,一定要注意隱蔽,不要暴露目標,指揮要冷靜。
我回到河邊,天已經黑得對面看不見人了。戰士們把船抬進河汊裡,參謀檢查後報告說: “先遣隊的五隻小船和一連的兩隻大船已經全部下水。”
我站在溝邊向大家傳達了團長、政委的指示後,戰士們在溝裡非常肅靜,除了河水的響聲和風聲,什麼動靜也沒有。先遣隊的戰士,每人衣服後背上釘一塊正方形的白布;一連戰士的左臂上都扎著白手巾,作為聯絡標誌。
天黑,我看不見同志們的臉,知道他們一個個都鼓著勁,只等一聲令下,就會像箭一樣射向對岸。看了看錶,還有一刻鐘才到九點,我又往對岸望望,還和往日一樣,燈火點點,時隱時顯,不時打一陣冷槍。
這十五分鐘,好容易才捱過去。先遣隊的五隻小船順著河汊成一路隊形進入了黃河,一連的兩隻大船隨後跟進。七隻船沿著河岸上游拉了一里多路。
到了預定的渡河點,先遣隊的五隻小船成扇形向對岸劃去。開始還能看到黑乎乎的幾個影子,後來只能看見戰士們背後釘的白布,幾個小白點在河心晃動。兩隻大船開始前進了。這時我才感覺到河裡風很大,浪聲和兩岸山谷的回聲,有如萬馬奔騰。
浪花濺入船中,靠邊坐的戰士的衣服被打溼,漸漸結成冰。對岸仍如渡河前一樣安靜。估計前邊的小船快到河心了,前方一片漆黑,隱隱約約的可以看到幾個小白點。耳邊傳來戰士們划水和低語聲:“加油!”“不要慌!”
忽然,前邊傳來木船碰擊聲,“靠岸了嗎?”
我自己問自己,“不會這樣快吧?”
在黑暗中隱約見到三個小白點在前邊移動。兩個小白點落在後邊。
“糟了!一定是撞在大冰塊上了。”
我正想著,只見敵人陣地上空升起一紅一白的兩顆訊號彈,幾乎與此同時,幾條強烈的電光向河中沙灘上集中照來。緊接著機槍、步槍、炮彈響成一片。
藉助電光和火光,我看到兩隻小船在浪花和炮彈擊起的水柱中間,搖搖晃晃的繼續向對岸划行。我兩手捏得緊緊的,心想,只要一登岸,有了立足點,這些勇士們就有辦法了。
靠左邊的一隻小船加快了速度,趕向前去。突然火光一閃,一聲巨響,那隻小船被擊中,晃了幾下,就被急流沖走了。
正在著急,對岸響起了清脆的槍聲。“是我們的槍響!”
警衛員高興地說,“前邊三隻船上岸了!”
我說:“快劃,趕快靠岸。”
我們的船在敵炮轟擊、機槍掃射中急駛直進。戰士們把準備能舀水的東西都用來划水,甚至用手劃,有的戰士負了傷還堅持劃。船被子彈穿透了,水從彈孔湧進來,戰士們有的用帽子堵,有的乾脆用背靠在洞上。
兩隻大船先後靠了岸。戰士們不等船停穩,就爭先恐後的往冰上爬。這時,先遣隊的戰士有的已經打到山腳下去了;有的還在冰上射擊;有的犧牲在冰上。
戰士們一上岸就撒起歡來,戰士找班長,班長叫戰士。我和參謀、警衛員進入緊靠河岸的第一個地堡,一面指揮登岸部隊作戰,排除地雷;一面組織後面部隊渡河。
這時山腳下不時響著同志們的呼喊聲:“繳槍不殺, 寬待俘虜! “我們是北上抗日的紅軍。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激烈戰鬥,河邊到山腳下的地堡大部解決了。
連續部隊在繼續渡河。我剛要往前轉移,師參謀長畢士弟同志趕來了。
一進地堡,就用他那兩隻大手緊緊地握住我的雙手,說:“祝賀你!我們勝利了。”
警衛員立刻點上蠟燭,擺開地圖。我向參謀長報告:山腳下在我們前面一百多米處,還有一個大地堡和一個小地堡沒有打下,正在圍攻;我們準備打下後繼續往前發展。
參謀長聽了,要我同他出去看看。我倆把地圖一合,吹熄了蠟燭,剛邁出地堡,一股股強烈的火藥味迎面撲來,什麼也看不見。過了一兩分鐘,才開始看清東西。
我們走到前邊一個小地堡跟前,參謀說前邊大地堡裡的敵人還在頑抗,一連戰士已摸近小地堡,正在向敵人喊話,敵人已開始動遙我說:“你趕快找一、二連,叫他們協同迅速拿下大地堡,辦法是:摸到跟前摔手榴彈、喊話同時進行。”
畢參謀長說:“告訴部隊注意利用地形,利用俘虜的敵人軍官喊話。”
參謀走後,我們又走進地堡,點上蠟燭,開啟地圖。前邊手榴彈聲、喊話聲,此起彼伏。過了十幾分鍾,還不見通訊員回來報告情況。畢參謀長等急了,非要出去看看不行。
他剛走出不多久,警衛員氣喘喘地跑回來說:“畢參謀長負傷了。他到那裡的時候,小地堡裡的敵人正在繳槍,還有一個敵人沒出來,順槍眼打了一槍,就把參謀長打傷了。”
我緊隨著警衛員跑到小地堡裡,只見畢參謀長躺在一件繳獲敵人的大衣上,雙手捂著小腹。我問他話,他已無力回答。只是手指敵人方向,示意要我到前邊去。
我派人找來衛生員給他包紮好,並留下人照顧他,待天一亮即護送後方。我交代完畢,用衣袖擦乾淚水,便走出了地堡。
此時,山腳下最後一個大地堡已經攻下。隊伍繼續向敵縱深打上去。敵人防線已被打爛,沿途山坡、路口,盡是我們先頭部隊用各種記號標識的地雷區。穿著各色服裝的狼狽不堪的俘虜,一串串地被戰士們押下來。
天亮後我和團長、政委會合了。他們說:畢參謀長犧牲了。我聽到這個訊息,禁不住的淚水奪眶湧出。我邊走邊回憶著這位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他是朝鮮人,中國共產黨黨員,有豐富的軍事知識,參謀業務很熟練,說著一口流利的中國話,他作戰勇敢,關心同志,工作非常熱情。記得在過黃河前,我每次到師部去,總是看到他在地圖前邊轉來轉去,想了又寫,寫了又想,親自動手為首長們標繪渡河地圖、謀劃部隊渡河準備工作……
如今,我們失去了一位敬愛的上級和親密的戰友,怎能使人不悲痛流淚呢?我默禱著:安息吧!親愛的戰友,你未竟的事業——全世界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由我們來繼續完成!
太陽昇起來了,整個軍團部隊在二十里正面,全部渡過黃河,滿山遍野,英勇的戰士像潮水般湧向敵河防司令部所在地——義牒鎮。
八點多鐘,閻錫山派來幾架飛機為他的河防部隊弔喪。敵機哼哼嗡嗡地在頭頂上轉了一圈,投了幾顆炸彈,又哼哼嗡嗡地飛去了。
我們根本就沒理它,順著大路繼續向義牒鎮前進。下午,我們趕到義牒鎮,守敵已棄鎮向石樓方向逃跑。一部分來不及逃走的敵人,繳槍當了俘虜。
第二天天還未亮,當軍團部發出集合號令時,各部隊從四面八方向義牒鎮西邊的大廣場集中。軍團大旗插在廣場中間,在嘹亮的號聲中隨風飄場,軍團首長精神煥發地站在軍旗前邊。隊伍集合好,部隊便分三路縱隊又浩浩蕩蕩地前進了。
韋傑(1914年3月—1987年2月),廣西省東蘭縣人。壯族。,一九二九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七軍班長、排長、連長,紅三軍團第五師十三團營長,紅十五軍團第七十三師二二三團參謀長、團長、騎兵團團長,第七十四師師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學員隊隊長,八路軍總部特務團團長,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六八八團團長,八路軍一二九師新編第一旅旅長,太行軍區第五軍分割槽司令員。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六縱隊副司令員兼十六旅旅長,華北軍區第十四旅隊司令員,第十八兵團六十一軍軍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第十八兵團軍長兼川北軍區司令員,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三兵團第六十軍軍長併入朝參戰,回國後,先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高階函授系主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