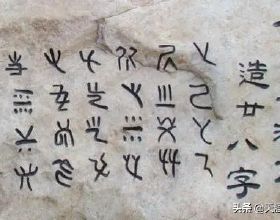縱觀中國翻譯文學發展歷程,不難發現浙江籍翻譯藝術家的貢獻。杭州作為浙江的省會城市,是新文化、新知識和新思想的傳播交流中心,更是湧現了一大批優秀的譯者,如李之藻、夏衍、馮亦代、周其勳和孫用等。他們鍾情翰墨,筆耕不輟,將畢生奉獻於翻譯事業,使浙江翻譯文學不斷取得新成就,為中國翻譯文學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夏衍,原名沈乃熙,字端先,著名文學家、翻譯家、電影家、戲劇作家和社會活動家,中國左翼電影運動的開拓者、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夏衍曾在上海洋場度過一段漫長的歲月,每日與百姓相處,走街串巷,對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頗為熟悉。也正是因為細緻入微的觀察,作為作家,他的創作總能在平凡中造就不同,這也為他日後將“小人物”作為創作中心埋下了伏筆。作為翻譯家,他在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同時,也密切關注世界局勢。翻譯作為一種文化的闡釋和傳播,與時代的政治經濟密不可分。如果說魯迅是棄醫從文,那麼夏衍便是棄工從文。境遇的相似,使得二人惺惺相惜,夏衍翻譯的高爾基著作得到魯迅的高度認可。身處亂世,他們意識到實業救國的渺茫,便另闢蹊徑,試圖先從精神上喚醒祖國同胞。
翻譯也為夏衍轉向文藝事業打開了一扇大門。他的翻譯生涯是從其在日本留學期間開始的,日本小說家和戲劇家菊池寬的戲劇理論專著《戲曲研究》是他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譯著。不同於在上海洋場對百姓生活的觀察,在日留學期間,夏衍憑藉對戲劇的熱愛,頻繁前往劇場,與當地的導演、編劇和演員一同研討學習戲劇的基礎理論知識,先從翻譯戲劇相關譯著入手再到改編劇本,以此奠定了他之後的戲劇發展方向。夏衍希望透過譯介的文藝作品,呼喚人民看到文藝的力量,用人民喜聞樂見的方式展示藝術,從而鼓舞人民,增強革命的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夏衍在翻譯實踐中對婦女問題尤為重視。這在夏衍翻譯出版的德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倍倍爾的理論譯著《婦女與社會主義》一書中可見一斑,此書是最早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婦女問題的經典著作。當時的中國,社會矛盾尖銳複雜,在內憂外患之際,重視婦女問題的文學創作極其少見,夏衍的此部譯著對早期中國婦女運動影響頗深。對女性問題的思考繼而引發了夏衍對兩性關係和婚姻問題的探索,這在當時可謂相當前衛。
夏衍的翻譯道路一波三折,他曾經因翻譯《戀愛之路》而飽受爭議。這是蘇聯女作家柯倫泰的作品,雖在內容上讀者需要辯證看待,但是夏衍的翻譯讓國人看到革命後新國家新政權的進步。面對翻譯中的不足,夏衍總能進行一定的總結和反思,他敢於面對翻譯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卻不妄自菲薄,盲目否定和放棄自己的嘗試。在劇作創作之時,夏衍能充分吸取翻譯中的經驗,將創作的中心集中在社會矛盾,同時,刻畫出個性鮮明的婦女形象,如張曼曼和施小寶等。也許是因為兼具社會活動家的身份,夏衍關注民情、體察民心,在他筆下對“小人物”的刻畫總是入木三分,讓讀者產生共鳴。
夏衍創作的劇本《賽金花》也得益於早前他對於婦女問題的關注,此劇本依舊是以女性為中心。此外,夏衍敢為人先,劇作大膽涉及情感婚姻問題。與觀眾的視角不同,夏衍對自己筆下的人物一視同仁,沒有絲毫的道德綁架,可以說夏衍是一位“公平且公正”的創作者。
當時的中國文壇缺乏介紹近代歐洲文藝思潮的譯著,夏衍在夏丏尊的引薦下翻譯了日文版《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一書。此書篇幅達二三十萬字,較為全面系統地介紹了歐洲各國從文藝復興時期到20世紀初出現的主要文藝思潮和演變、各類文學流派以及各作家及其代表作等。夏衍是一位效率極高且責任感極重的譯者,僅用了三四個月時間,就完成了《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的翻譯。透過夏衍的翻譯,我國讀者慢慢接觸並熟悉了西方文學的梗概,從而獲得了思想啟迪。《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的成功也堅定了夏衍從事翻譯事業的決心。
對不同國別文學的譯介展現了夏衍翻譯文化觀的成長,他對高爾基的《母親》的翻譯堪稱經典。夏衍是首位將《母親》帶入中國的譯者。因為《母親》的譯介,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備受感動,從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今,在國內流行的《母親》譯本依然是夏譯本,足見其翻譯之通俗易懂和廣受歡迎。在抗戰時期,夏衍依然堅持以翻譯作品為革命服務,給予廣大的人民群眾強大的精神支柱,不管是《三兄弟》還是《兩個伊凡的吵架》都讓人們對戰爭有了更深的認識,堅定了戰勝帝國主義的決心。對劇本《三兄弟》的翻譯,體現了夏衍劇作題材創作從歷史到現實的轉向,對現實主義的堅持也延續到了對劇本《兩個伊凡的吵架》的翻譯中。在敵後方,配合“戲劇季”等相關活動,夏衍翻譯並改編了俄國作家托爾斯泰的六幕話劇《復活》。與單純的文學翻譯不同,劇本翻譯往往需要進行大幅度再創作,夏衍保留了原著中人性復活的主線,結合當時國情弱化刪除了其中的空想主義和宗教思想,這也體現了他的翻譯和創作是為時代而生的。新中國成立後,夏衍沒有放棄翻譯工作,而是繼續以自己對美學的感悟不斷為祖國文藝事業添磚加瓦。
除了對文壇和劇場有傑出貢獻外,夏衍對影壇的影響也不容小覷。他學貫中西,孜孜不倦,用譯者的身份叩開了中國影壇的大門。夏衍和鄭伯奇合作譯介了蘇聯電影藝術大師普多夫金的著作《電影導演論》和《電影指令碼論》。夏衍可謂是文藝界的及時雨,不僅譯介《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填補了中國文壇近代歐洲文藝思潮譯著的空缺,還譯介普多夫金的電影理論著作,改變了中國影壇電影劇本和攝製臺本落後的面貌。在夏衍譯介的《電影導演論》和《電影指令碼論》面世之前,中國影壇對外國電影理論的介紹大多片面主觀,客觀性不強,因此缺乏指導的實操性,不利於廣大電影工作者和愛好者學習和借鑑。當此譯著開始在《晨報·每日電影》上連載時,反響空前熱烈。自此,中國電影發展呈現嶄新的面貌,廣大電影工作者在充分吸收國外電影藝術的最佳經驗上,也開始在攝製臺本方面大展拳腳。不僅如此,電影工作者對於“蒙太奇”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和通透,電影批評學也變得有血有肉,中國電影在取其精華和去其糟粕的道路上不斷成長,由此中國影壇便湧現了《馬路天使》等優秀作品。夏衍的譯介加上一代中國電影人的努力,中國影壇從此煥然一新。
回顧夏衍的翻譯歷程,其譯介作品符合讀者的閱讀習慣,高度符合“歸化”翻譯的標準,其中採用一些中國的典故來增加文章的可讀性和欣賞性。也正是因為夏衍始終強調在加強對原著理解的基礎上用易於理解的短語進行翻譯,他的讀者才會如此之多,譯本才會廣為流傳。在翻譯和改編戲劇的過程中,夏衍充分考慮中國觀眾的審美,例如在處理《復活》時,原著為了更顯張力和衝突性,運用了倒敘的手法,但夏衍在處理時採用了順序的敘述手法,按照時間順序安排情節的推動發展,娓娓道來,增強了大家對抗戰勝利的信念。
據統計,夏衍的翻譯作品涉及多個國家,單部作品中包括日本文學譯著14部、蘇聯文學譯著7部、俄國文學譯著2部、德國文學譯著2部。單篇作品和論文包括日本文學16篇、蘇聯文學8篇、俄國文學3篇、德國文學3篇、匈牙利文學1篇和美國文學1篇。
(作者單位:杭州師範大學錢江學院;上海大學外國語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郭聰 嚴程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