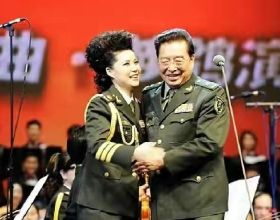繼續鼓勵大家讀漫畫,讀豐子愷漫畫。
今天我們玩手機太多了,不是抖音,就是快手,要麼就是影片號。嘩嘩譁弄點兒小熱鬧,一個跟一個,是有點兒小刺激真快樂。但這種刺激往往缺乏裡子——翻開了,卻發現其實一無所有;翻完了,又感到自己等於什麼也沒看。
翻手機的衝動說明,你還是渴望滿足自己的眼睛,從前那種抱一厚本子長篇小說的閱讀衝動和熱情,還在你血液裡流淌著,只不過,你的耐心已經被抖音帶了節奏。你的探究熱情被快手慣壞了——三分鐘以後,很難保持不換花樣。這時候怎麼辦?我的建議很老套——還是看書。我不是手持教鞭的書塾老先生,沒資格打你手心逼你背《論語》。我也沒有靈丹妙藥,告訴你一套省時省力又高效的三天半拿下一套《紅樓夢》的整本書閱讀妙招。可我這兒有省力輕鬆的好書,願意推薦給你——豐子愷漫畫集。
豐子愷漫畫,其實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藝術作品集。每頁一小方兒,一畫一個情景,用筆簡練,線條敦厚。柔柔細柳,高高古松,青青草,彎彎月,是豐子愷先生取景的經常題材,其中融會著先生溫和的情懷,親切的態度,純中國風的人生詩意。兒童是豐先生筆下的常客,他們頑皮、活潑、好奇心十足,以萬物為朋友,以蝴蝶為玩伴,以天邊云為電影。趣味是豐先生的永恆主題,幾乎每一幅小畫兒都有一種新的發現,無論黑白線條畫,還是淡染彩色介乎於傳統國畫與新式漫畫之間的生活畫面,興味盎然,意趣濃濃,每一張都會給人嘴角帶來一抹情不自禁的微笑。
身為老師,我最愛看豐先生的兒童漫畫和教育漫畫。豐子愷先生青年時代曾在有名的浙江白馬湖春暉中學任教,寫過一本《教師日記》,跟中國現代教育的先驅葉聖陶、匡互生、經亨頤、朱光潛、朱自清等人都是同事。他的漫畫告訴我們,他最喜愛孩子的天性。他永遠將母愛、父愛、兄弟姊妹之間的玩耍和情誼、娃娃們之間的遊戲,甚至是兒童經常表現出來的調皮或者說“頑劣”,當成一個人健康成長最重要的“教材”。他的散文和各種藝術論著告訴我們,向兒童學習,也許不失為一種解決人類當今各種煩難糾結問題和社會病症的良藥。他說:“小孩子真是人生的黃金時代!我們的黃金時代雖然已經過去,但我們可以因瞭解藝術的修養而重新面見這幸福、仁愛而和平的世界。”(豐子愷《美與同情》)“成人的世界,因為受實際生活和時間習慣的限制,所以非常狹小苦悶。孩子們的世界不受這種限制,所以非常廣大自由。”(《談自己的畫》)。讚美兒童天真,並不取代對現實的真實觀察。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我們看到,上世紀七八十年前豐先生看見的很多教育弊端,今天居然還是那麼顯眼。
《某種教育》中,一個做泥娃娃的匠人,正在做出一大堆一模一樣的泥娃娃。這就是“某種教育”嗎?《剪冬青聯想》——有個老師正照著“園丁”剪冬青矮樹牆的方式,將一排個頭不一的孩子按一個標準剪平,很多腦袋就變成半個啦。《教育》這張畫上,一雙大人的手裡捏著一方木頭模具,一個小人兒苦著臉,正從那模具的人形凹槽裡坐起來。教育原來是某些愚魯之人手裡的按一個模式“脫泥坯”娃娃的過程。娃娃的個性呢?潛能呢?個人意志呢?全然不在這個“泥坯匠人”的考慮範圍。因為,有一些教育者,正如《某種教師》裡畫的那樣,他們的頭顱只是一架留聲機,他們的眼前永遠只有一本書,他們的教學只是照本宣科,只是播放同一張唱片。他們目中無人,只有自己偷懶耍滑、麻木無感的那一套兒“教學內容”。如果說今天的某些教育出了問題,恰恰就是這些漫畫揭示的那樣,是教育者看不見眼前個性各異、生動多姿的學生的萬千面貌,不懂得這種因人而異的豐富性,恰恰是亟須教育者百般呵護、精心培植、全力引導而使之各順其流、健康生長的人的潛能,恰恰是這種豐富性才能夠最大限度發展屬於每一個人的天然力量,最後才能形成全社會多姿多彩的創造活力。
如果說今天的教育還有一些東西需要我們警惕,那麼,正是這種因為我們急功近利的、想要取得一時競爭之利而抹殺了學生個性健康發育的狹隘“教學手段”。《母親的夢》裡,一個媽媽太想讓自己的孩子強壯結實,簡單粗蠻地用一支吹管插進他的肚臍眼,往裡吹氣。《我們設身處地,想象我們孩子的生活(其一)》中,一個大人邁開自己的大步伐只管快走,全然不明白那個被他牽著手的孩子,雖然穿了一身大人模樣的長衫,卻因為腿腳尚短,走得滿頭大汗,厚眼鏡片下面的眼睛都翻了白眼。同題其二,成年人的桌面上擺滿了美味佳餚,坐在大人板凳上的孩子,卻因為不具備大人的高大身軀,只能攀在桌沿上伸斷了脖子。《用功》畫面上,一個伏在書桌上做作業的孩子,眼前是厚書本襯著大本子,縮著的頭頂上,是一隻大手蓋著壓著。那隻大手的主人,原來是一條黑衣虯髯、凶神惡煞般的大漢,他胸前的字牌揭示了他的身份——分數。學習本該是一種“分數壓迫”嗎?豐先生請我們思考。
我們該思考。讓我們翻開一冊豐子愷漫畫,去稍稍想一想。 □霍軍
責任編輯:李雪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