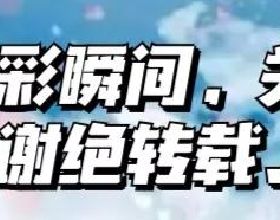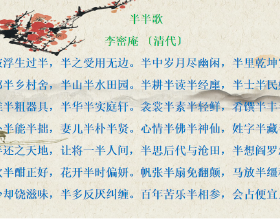最近幾年,我都在紙上重返絲綢之路,並藉助這條路上的唐詩之光創作了詩集《二十四伎樂》。行走考察這條由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的陸上絲綢之路,實際上也是我沿著唐朝宮廷樂器的足跡返鄉,探究唐詩的遼闊邊疆。其間,音樂氣息濃厚的一首首唐詩如同我探訪“一帶一路”多個詩歌通道的通行證,不斷延展著我的眼界,不斷滋養著我的新詩,不斷生髮著我的想象力。對我而言,用詩集《二十四伎樂》回望“一帶一路”,就是詩歌與樂舞的攜手返鄉。
該書獲“第十屆四川文學獎詩歌獎”
俗話說,條條道路通羅馬。“一帶一路”所指的陸上絲綢之路,如果帶上唐詩從長安(今西安)出發,經涼州、酒泉、敦煌進入西域諸國,我以為如此到達的終點羅馬,才是真正彰顯中國文化自信的羅馬。因為這條絲綢之路,連線著來自中國絲綢、瓷器、詩歌的輝煌。尤其是吸納西域樂舞而孵化的《琵琶行》《長恨歌》《霓裳羽衣舞歌》(一作《霓裳羽衣歌》)等膾炙人口的唐詩,將中國的詩與歌合體、壯大,遠播世界各地。事實上,代表中國詩歌巔峰的唐詩,也是世界詩歌的“珠穆朗瑪峰”。
二十四伎樂
¥45.2
購買
我的紙上絲綢之路,主要是考察曾經盛行於唐朝宮廷的琵琶、箜篌、觱篥、羯鼓、銅鈸、貝等西域樂器生存的土壤、遷徙到中國的發展,以及它們催生的唐朝音樂詩篇背景。之所以要以詩歌的名義去尋根樂舞的故鄉,是因為成都永陵博物館石刻浮雕“二十四伎樂”,這24個蜀宮樂伎以及她們手中的樂器正源於這條陸上絲綢之路。她們將唐音託付終身於石頭,至今存在了1100週年,成為全國唯一儲存較為完整的宮廷樂隊石刻浮雕。
某種意義上說,成都在唐朝便是音樂之都、詩歌之城,就因為這些來自西域諸國的樂器,早就讓成都人的骨子裡有了詩的情懷和音樂細胞。吉狄馬加說,成都是詩歌與光明湧現的城池。雷平陽說,成都是用詩句築起的城郭。他們有一個相同的指向:成都,詩意淋漓之城。而成都歷史上的很多名詩,還多跟音樂有關。比如詩聖杜甫在《成都府》《贈花卿》兩首詩中書寫的“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就是成都作為唐朝“音樂之都”的詩意收藏。到了王建於907年在成都建立的前蜀王朝,所奏宮廷樂舞更是盛況空前,可以直追唐玄宗引領的盛唐氣象。時有前蜀詩僧貫休(《壽春節進大蜀皇帝五首》)的“家家錦繡香醪熟,處處笙歌乳燕飛”,宋代也有學者張唐英(《蜀檮杌》)的“屯落閭巷之間,弦管歌誦,合筵社會,晝夜相接”,對蜀地民間音樂的繁盛進行過形象化的描繪。前蜀皇帝王建寵愛的琵琶、箜篌、觱篥等西域樂器,這些閃亮一時的蜀地唐音,經花蕊夫人、韋莊等人之手,還催生了一個承唐啟宋的花間詞派。這些來自絲綢之路的詩意樂器,在王建棺床上,幾乎填滿了我長達兩年的週末生活。“西域遷來的螞蟻睜大了瞳孔/二十四個樂伎全被歡喜凝固”,痴迷於石刻西域樂器多年,我曾腦洞大開冒出這樣的詩句,流連忘返於絲綢之路的某個唐詩通道,有時樂不思蜀,有時也樂在思蜀。
反思唐詩為何就能成為一覽眾山小的“詩歌的珠穆朗瑪峰”,我的手指會攏、捻、抹、挑,彷彿在橫抱琵琶彈琵琶。其實,唐詩尤其是唐朝音樂詩的廣泛流傳,主要在於歌者、舞者、樂伎的身體力行。單就李白、杜甫、王維這三大盛唐詩人而言,他們的詩歌便離不開大唐第一歌手李龜年的反覆吟唱。而我們一提到白居易的名字,腦海裡會立即跳出《琵琶行》《長恨歌》等表現唐朝西域樂器、舞蹈的詩歌名篇,就因唐詩與唐樂、唐舞相互成就。自帶韻律的唐詩、利於放歌的宋詞,至今傳誦不衰,可以說皆是詩與歌的合體發力之功。
現今的詩則和歌分家許久了,一個在彼岸,一個在此岸,難以遙相知音。為追蹤音樂裡的唐詩,探尋詩歌的音樂性,我最近幾年重返絲綢之路創作詩集《二十四伎樂》,試圖給自己的詩注入一些音樂、舞蹈等有跳躍性和節奏感的新鮮元素。“吹的那支法曲離開海螺,/追隨者跟著嗚嗚聲走遠。//絲綢遺忘的路,/衣錦無法還鄉。//內心新生的疑惑,再掏空一次。/我把空出的地方,重新叫作貝。”在追尋“貝”這種西域吹奏樂器經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蹤跡後,我情不自禁創作了《吹貝伎》。儘管我知道這樣的新詩難以譜曲,但是它至少嵌入了我的樂感與詩心。而我考察永陵石刻舞伎和敦煌石刻舞伎的舞姿創作的新詩《舞伎》,比如“她是油燈燃燒時的夢。每一次轉身/都對闖入體內的鼓聲過敏。//英雄奸佞均已到齊,她卻還在/搖擺不定的火焰中,尋找意外……”等詩句,也就是很單純地向白居易致敬,向白居易的音樂詩《霓裳羽衣舞歌》致敬,向楊貴妃引領的盛唐西域風味舞蹈“霓裳羽衣舞”致敬。
如此完成的詩集《二十四伎樂》,僅是我重返絲綢之路的一個縮影。雖然它們並非“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作品,但是透過紙上重返絲綢之路,我至少發現了另一個有禮有節有節奏的我。
(本文系人民日報出版社《二十四伎樂》自序,作者彭志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