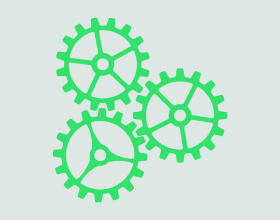那天,我站在新鄭機場的行李傳送帶邊,焦急地等著我的旅行箱。
五分鐘後箱子來了,當我試圖拉開拉桿時才發現它壞了,無論我怎麼搗弄就是拉不開。再用力時,拉桿的把手竟然斷了。上飛機前把手還是好好的,沒想到幾個小時後下來就成了這樣。
箱子有些重,只好拉著箱子上面的輔助帶湊合著往前走,可剛走出大廳,輔助帶也斷了。這下好了,只能提著了。步行了十分鐘,上了機場巴士,大冬天的已是滿頭汗。
這隻旅行箱跟了我十九年,是我的老朋友了。十九年來我從北到南,又從南到北,每一個我所路過的城市,都有她的身影。今天,她盡了最後一份力,鞠躬盡瘁了。
畢竟十九年了,旅行箱的把手塑膠已經老化,輔助帶的縫線也已老化,經不起裝上重物後的折騰。
這個行李箱是我初到佛山打工時花了一百大元買的,在當時可不算便宜。其時自己並沒有錢,錢是尚倫兄借給我的。當時我被一高中同學從東莞騙到中山搞傳銷,在中山一出租屋內住了六天,聽不同的傳銷主任講成功學,洗腦。反正我也沒錢,洗就洗唄,我也想看看他們到底怎麼洗。但直到最後,輪番上陣的傳銷主任們也沒能把我的腦子洗白,更不可能從我的手裡拿到錢,反倒是白吃白住地養了我六天。
離開中山到佛山投奔尚倫兄時手裡只剩下了一塊三毛錢。在尚倫兄的宿舍裡住了二十四天,吃住自然是尚倫兄接濟的。找到工作臨去上班時我向尚倫兄借了兩百塊錢,花了一百塊在汾江南路附近的一個市場裡買了這隻旅行箱。
那時的一百塊對我來說不算一個小數目。之所以買這麼貴的一個箱子,是我看中了它的空間設計和堅固程度。箱子的面料是深綠色的牛津布,內襯塑膠板非常厚實,拉鍊也粗大結實。拉桿較長,抓起來很舒服,不用屈尊彎腰。箱子的空間為三層設計,可以伸縮擴充套件,行李多時可以拉開備用層。整個箱子可以裝下一張薄被、一個洗臉盆、一個枕頭、兩雙皮鞋、幾本書和七八件衣服。我的全部家當放進去都綽綽有餘。
有一次搬家轉廠,我用這隻箱子裝了滿滿的一箱子書,重有八九十斤,上樓梯時雙手緊搬,一層層地往上挪,像扛著一口袋麥子爬坡。運到宿舍,箱子的各個部件完好無損,亦無變形。
過年時回老家,想買到有座票勢比登天,提著行李箱擠火車是難上加難。好不容易擠進了車廂,裡面連下腳的空都沒有,左衝右撞地捱到了過道邊,放下箱子,坐在上面喘氣。衣釦敞開著,頭上不停地冒著熱氣,騰雲駕霧一般。此時的行李箱儼然成了我的坐騎——瑞獸麒麟。
小時候見到村裡一個姑娘拉著一個行李箱從遙遠的外地回家過年,輪子壓過土街,發出唰啦啦的聲響,那聲音就像《卡門》曲一樣撩撥著我的心房。我對拉桿行李箱的情結就是在這時種下的,同時種下的還有對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嚮往。
多年以後每次拉著行李箱回老家,我腦海裡不時會浮現出那位姑娘拉著行李箱的畫面。那個畫面對我來說十分溫暖,充滿了魅力。在這人世間,美好和邪惡同樣讓人難以忘記,只不過人們更願意回憶美好的事情罷了。
這位與我相伴十九年的老朋友所留給我的美好記憶,就是她本身的三層空間也是無法裝下的。比如美好的愛情,比如真摯的友情,再比如那次回家,公交車因為太晚而不往村裡去,我拉著箱子從鄉里步行至村裡。夜很靜,也很黑,路燈眨著醉酒似的眼睛,擠出幾縷迷迷糊糊的光。旅行箱的軲轆滾過柏油路面,轟隆隆的聲音劃過夜空,撞擊著大街兩邊的屋頂。到村口時,一位老大爺騎著單車從後面追上來問我:學生,恁晚了,我送你吧,你把箱子擱我車後頭。
現在,這隻旅行箱正靜靜地呆在房間裡,上面罩著防塵袋。我像收藏古董珍寶一樣收藏著她,收藏著美好的往事。而她也收藏著我,收藏著我的半個人生。
202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