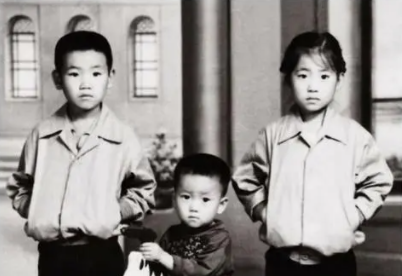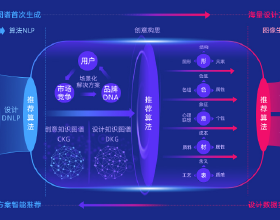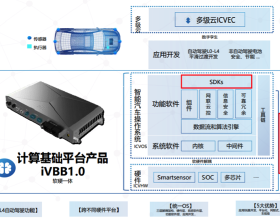口述/魯木匠
撰文/小靨
“如果這輩子能重新來過,我還會做祖傳的木匠、娶我深愛的妻子、生3個孩子。但我絕對不會再望子成龍,把3個子女都培養城大學生……”
大家好,我叫魯建國,53年出生在洛陽城,61年河南大饑荒,父親帶著我們一家人逃難到山西,這一轉眼就是60年。我前半生最驕傲的事:一是承接父業,做了遠近還算聞名的木匠,二是將3個子女都培養成了大學生。
我家算是木工世家,歷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祖上是跟隨魯班學藝的徒弟。小時候我家還保留著一本頁尾都被翻爛的黑牛皮族譜,61年大饑荒逃亡的路上都沒有捨得丟,結果在接下來的幾年特殊時期被破了“四舊”,一把火燒了個乾淨。
族譜雖然丟了,但我們家的木工手藝卻傳承了下來,到父親這一輩,我們家之所以能以河南難民的身份在山西站穩腳跟,也全憑了這份祖傳的手藝。
父親所處的時代,算是傳統木工最後的輝煌時代,那個時候木工還沒有全面被自動化機械頂替,市場行情還是很好的。有市場、能賺錢,就有人願意學,父親門下徒弟最多的時候,足有103個。
“嚴師出高徒”是父親信奉的教條,對眾多徒弟如此,對我這個繼承衣缽的兒子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刻花雕版打深一鏨子、箍得木桶有些許不對稱就要用皮鞭子抽。為了讓我一門心思沉在木工手藝上,在18、9歲結婚都算晚的年代,父親特地給我定製了一條規矩:“不出師,不能結婚!”
父親對我的期許很高,總覺得我還能做得更好。若不是70年之後身子就不大好了,21歲我也不能娶妻生子。
“望子成龍”的家風,也是在這個時候,隨著日益增長的木工技藝,潛移默化地刻入我的骨髓。
75年、78年,我的大女兒嘉堯、大兒子嘉舜和小兒子嘉禹,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相繼出生,彼時的木工市場可以用慘淡來形容,大規模的工廠流水線製作的木質家居流入市場,憑木工手藝吃飯的我,勉強能養活家庭。
木工沒有出路,那就多讀書,上大學。在生活中我始終扮演者“嚴父”的角色,鞭策著兒女讀書。嘉堯、嘉禹勤奮好學,不用我怎麼管教,成績次次名列前茅。
老三嘉禹仗著妻子的疼啊,從小就淘,初二就跟人逃課,被我抓回家就是一頓皮鞭。可他好了傷疤忘了疼,屢教不改。
最後我一怒之下將嘉禹送到了當時很火的軍事化管理寄宿學校,當時看到嘉禹的成績一步並不提升,我還曾竊喜,自己做了多麼正確的決定,殊不知這是犧牲了我和老三的父子感情為代價。
最終,我的三個子女,不負我望的成龍成鳳:
嘉堯考上了廣州大學,畢業後去了深圳,嫁給了同去深圳打拼的江西同鄉,本以為女兒不算遠嫁的我和妻子,三年後卻始料未及收到女兒女婿在深圳買房定居的訊息;
嘉舜大學畢業後留在了上海,定居上海不說,還經常需要出國出差,往往一走就是半年;
老三嘉禹大學考得不怎麼好,只考上了西安的一所大學,畢業後在西安買了房,而後娶妻生子。
兒女成才後,街坊四鄰在我和老伴頭上貼上了“一門三學子,各個有出息”的金色標籤,我們走到哪裡,都能聽到或看到人們包含著讚美、羨慕甚至嫉妒的言語或神情。
說實話,五十多歲的那段歲月,是我人生最愜意的時光。在家,兒女成才定期會給我和老伴打些生活費,我不再為生計而拼命打工賺錢;
最讓我舒服的還是出門後,兒女成材在我臉上貼的金,虛榮心得到了極大地滿足,前半生累得直不起的腰都挺直了三分。
當這些浮華散盡,只落下滿目的伶仃孤苦,當年的驕傲,成了我這輩子最後悔的事情。
18年剛進臘月,我被村裡人請去做婚床,老伴一個人在家。因為臨近婚期,活趕得比較緊,我就留下多忙了一會兒。等我到家,發現老伴蜷縮在床上,身下已是一片殷紅……
等送到醫院,搶救了三個小時後,醫生還是無奈地衝我搖頭致歉,妻子(患有“三高”)突發腦溢血,發現得太晚,腦部出現大量結節阻斷了神經……
那一刻,我心如刀絞強撐著身體給子女打電話,結果一個一直無法接通,一個身在國外,老三紅著眼睛,兩個小時候才趕到。
妻子的彌留之際,竟是無緣再見一眼她疼愛一輩子的兒女。最後一瞬,她努力地衝我眨了眨眼,淚水從眼角滑落,由熱逐漸冰涼。
淚眼朦朧中,我讀懂了她的眼神,那是讓我替她向孩子們道別,她等不到再見他們的那一刻了……
我喚著三個孩子的乳名,告訴妻子他們來了,或許是妻子的腦海中見到了孩子們,閉上眼睛的她,嘴角竟然彎起一個弧度,她笑著離開了。
只不過後來這個笑容,再次出現在我孤獨的夢境中,竟是如此的可憐、可悲、可怕……
三天後,女兒和大兒子陸續趕到,但見到的卻是滿目冰涼,他們哭得很痛,我悔恨地幾度趔趄想要栽倒,如今這個果,不就是我望子成龍的種下的嗎!
七天後,悲傷還未撫平,子女們就紛紛要離開,女兒想我一起去了上海,但住慣了鄉村院落的我,哪裡住的習慣。不到一個月,就回到了住了一輩子的院子裡。
初一十五,我會到老伴那裡和她聊聊天,白天的日子為了不無聊,我拼命地做木工,家裡做的板凳、水桶賣不出去,堆積著,我依然不敢停。
傍晚,我成了村口大樹下的常客,也不說些什麼,就站在那裡看來往的行人,多麼希望這裡面有我那“成材”的子女,也多麼希望他們沒有成材,就生活在我的身邊。
總是等到夜深人靜了,等到我困了,我才敢回家,快速入眠,才不至於被孤獨、惶恐、憂心肆虐席捲!
最難熬的是19年春節,因為疫情,三個本就不常回來的兒女,春節也回不來了。我一個人包了兩碗餃子,一碗放在妻子的遺像前,一碗自己和著淚水吃了。
聽著鄰居家團圓的歡聲笑語,我夢到了妻兒回到了我的身邊,孫子孫女追著喊我爺爺……
兒女並非不孝,只是因為他們都有“出息”,所以忙,我努力習慣著孤獨,但孤獨卻讓我越來越悔恨,如果不是我望子成龍,兒女們沒有那麼優秀,是不是就不會生活在千里之外?
等再過兩年,我快要幹不動的時候,我準備用自己的手藝,給自己打一口棺材。不用多麼名貴的木料,但圖案一定要刻得講究,不寫什麼“壽”字,就刻兩幅“兒孫繞膝”圖,彌補沒想享受天倫之樂的妻子,也彌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