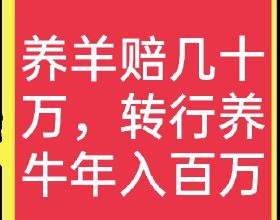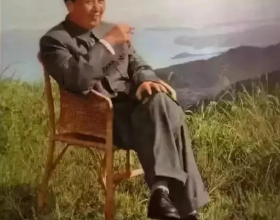巒莊,那個深藏在巍巍秦嶺南麓,綿綿蟒嶺深山縐褶之中的小村莊,是生我養我的家鄉。
穿過秦嶺隧道,繞過商州小城,出丹鳳約裡許,一條進山公路就一頭鑽進深夾溝。沿著蜿蜒山路爬行六十里,昏昏欲睡之際忽聞有人高喊:“上元嶺了,快到家了!”元嶺是丹江與武關河的分水嶺。說是快到家了,其實還有三十里路。是心裡感覺親近了,彷彿車窗外那一道道延綿的山嶺,一彎彎清淺的溪水,還有那留連在山腰的雲霧,點綴在草叢的山花,都是來迎接我們回家的。
翻山越嶺,時見青山前,綠水邊,幾間白牆藍瓦房,便是人家屋場。張、王、李、趙,聚族而居,族內排輩分,族際結姻親。從門前高掛的燈籠上“江南”“安徽”字樣可知當地人祖居江南,明清兩朝逃荒至此,立木為家,落地生根。有歌唱道:
青山綠水邊,草舍三兩間;
山花紅紫開遍,或深或淺;
一笛悠揚繞雲間,
山前人是仙。
巒莊人語言腔調,既不同於西北官話關中秦腔,也有別於東南毗鄰的河南豫劇,反倒與千里之外的黃梅戲的對白神似。蓋房立戶,多為三間廊簷房,裡外石灰搪,中間為堂屋,曰“中堂”,“天地君親師”高供於堂上。祖祖輩輩傳承著敬天厚地忠君愛國孝親尊師的風尚。
順水依山,峰迴路轉,忽見有橋如虹。巒山一莊,已隔河在望。巒莊街坊,一街兩行。像一根彎彎的扁擔,擔著東西兩座寺廟。東頭是關帝廟,供的是紅臉關公。西廟後山有洞,名曰羅漢洞,洞中塑有十八尊羅漢。洞前為佛殿、寺院、戲樓。前庭後院,古樹參天;青磚藍瓦,雕樑畫棟,泥塑木雕,精美絕倫……可惜這佛門聖地,也毀於浩劫。只有廟門前那棵倒掛柳樹任憑風狂雨驟,依然春風又綠,以頑強的生命力,見證著巒莊的冬夏與春秋。
巒莊人愛熱鬧。逢年過節,敲鑼打鼓,搭臺唱戲,耍社火,玩花燈,劃旱船,跑魔女,舞獅騰龍,耍醜逗樂。所到之處,張燈結綵,人山人海。有的看門道,有的看熱鬧,裡三層,外三層,把一條本來就不寬展的街道擠得水洩不通。更有些不長眼色的喜歡在熱鬧處賣母豬,騎個摩托往人堆里加楔子,還把喇叭按個不停。人挨人,人擠人,誰把誰的一隻繡花鞋擠丟了,誰把誰家孩子擠哭了,誰把誰家小媳婦屁股擰疼了……喊聲,哭聲,罵聲,吵吵嚷嚷,笑聲,叫聲,鬧聲,人聲鼎沸。想聽的聽不清,想看的看不見,外邊的擠不進去,裡面的鑽不出來,攪成一鍋粥,亂成一窩蜂。這是巒莊街最熱鬧的時節。
遙想當年巒莊的熱鬧,耳邊又響起家鄉的小調:
“正月裡什麼花沿門高掛?
什麼人扮男裝去上學堂?”
“正月裡燈籠花沿門高掛,
祝英臺扮男裝去上學堂。”
“正月探妹正月正喲嗬,
家家戶戶鬧花燈喲嗬,
看燈是假意喲妹子喲,
看妹是真心喲呀妹喲,
二月探妹龍抬頭喲嗬,
我在南山把書讀喲嗬,
嘴裡念文章喲妹子嗬,
一心掛兩頭喲呀妹喲……
九月探妹是重陽喲嗬,
菊花開在山頭上喲嗬,
伸手摘一朵喲妹子喲,
插在你頭上喲呀妹喲……”
這是民間小調,也是巒莊歌謠。這一問一答,一唱一和,好有情調喲!
快過年了,我終於回到巒莊,回到家鄉,回到了夢縈魂繞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