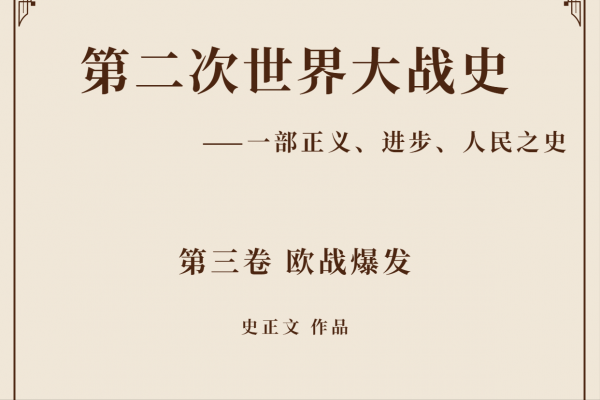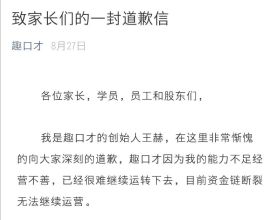第二十三章 英國的反法西斯之路(二)
第一節 英蘇關係
此時,如何處理英蘇關係成了英國反法西斯體系中的又一主題。顯然,相對於和諧如意的英美關係,英蘇關係要差遠了,總有一個東西隔閡在它們之間,難以逾越。丘吉爾,這位高傲的反共人士,面對蘇聯這個新盟友,心情一開始就是五味雜陳的,和這樣一個“邪惡制度”走在一起,那真是莫可名狀,是嫌棄之?蔑視之?不信任之?也許兼而有之。蘇德戰爭爆發後,在他表達與蘇聯合作意向的同時,其反共心性也不能不一時勃發:法西斯入侵蘇聯此乃蘇聯之“報應”,誰讓它當年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而把戰爭之球踢給英法,這“報應”太好了!此時法西斯正在充當“司報應的女神……是大奸大惡的懲罰者”,而蘇聯則是“徹底受騙上當的笨伯”,它大錯特錯,它一錯再錯,它正在遭受最可怕的人間災難!這都是“咎由自取”呀,與吾高貴之大英帝國何干!丘吉爾正以資產階級文明人的身份冷眼旁觀著這場血雨腥風的“野蠻人”戰爭。這場戰爭確乎“野蠻”得驚天動地,它讓溫文爾雅的大英帝國諸臣子們不免心驚肉跳。
當然,丘吉爾沒有陷入過去的“恩怨情仇”中,更不會陷入兩個“邪惡制度”同歸於盡的幻想中。抱怨和攻訐了幾句後,他迅速步入了合作和結盟的正題。對這位新盟友的實力、志氣和價值,丘吉爾是有一個清醒判斷的,他知道這位新盟友是一個怎樣的人物,此乃一位實力不俗,豁得出性命,敢幹敢闖的主兒,儘管“野蠻”了一些。但話又說回來,若沒有這個新盟友的“野蠻”,他的英倫三島是難以獨存的——即使背後有強大的美國。確切一點說,正是有了這個新盟友的“野蠻”作支撐,強大的美國才敢源源不斷投入。我想,誰的作用更具有根本性,西方諸君即使嘴上不說,心裡那還是有譜的。能從容安排一切,不緊不慢地聚集力量,打算1943年後才大規模行動;能“千年等一回”打一仗,能隔數個月才像模像樣發起一場戰役;能千方百計迴避第二戰場開闢,專心致志地謀劃自己的利益;這一切都有一個基本假設暗含其中:新盟友的“野蠻殘酷”能長期把敵人的主力吸引過去。
蘇聯若沒有以其強大的“野蠻”展現於世人面前,我想,是很難博得西方諸君真誠合作和無私幫助的青睞。是的,合作確乎是真誠的,幫助確乎是無私的,若有人敢否定這一真誠,取消這一無私,那是會遭到堅決駁斥的。人民群眾唯有以覺醒、徹底而無比堅強的鬥爭才能贏得歷史的承認和尊重,贏得時代的發展和成果。
在嫌棄和蔑視的心底裡,丘吉爾對蘇聯人民的英勇頑強也不能不感動一二,也不能不給予一些良好的評價:“我們絲毫也不懷疑歷史將要加以肯定的結論:俄國的抵抗粉碎了德軍的力量,並給予日耳曼民族的有生力量以致命的創傷。”“即便蘇聯軍隊退到烏拉爾山,俄國仍然會發揮巨大的力量,而且,如果它堅持作戰的話,會發揮最大的決定性力量。”在蘇聯人民的英勇抵抗中,“我們得到的利益是不可估量的”,“俄國人民已經表現出他們是值得支援的人,所以,我們必須作出犧牲,甘冒危險,以維持他們計程車氣,即使有些困難,而且我也知道這些困難,我們還要這樣做。”
因此,物質上援助蘇聯是必須的,是要毫不猶豫決定下來,這是目前援助蘇聯的唯一方式,如果連這個都做不到,那我們西方諸君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了,這個底線還是要守的。但是,一當開始援助,我們的丘吉爾那是忍痛割愛呀,忍著劇痛去割愛呀。種種困難伴之而來。英國海軍那是冒著千難萬險運輸援助物資,不但要克服北極海域的惡劣條件,還要面對敵人千般阻撓。啊,援助蘇聯是一項風險和犧牲“巨大”的事業!更何況“我們不得不作出最重大的犧牲,並輸出大量的物資”,“我們”是在“勒緊褲腰帶”搞援助,是在“損害”自身利益搞援助,是在“置打亂自己重整軍備的計劃和敵人可能春季入侵的巨大風險於不顧”而“竭盡全力”搞援助。特別是9月間的莫斯科三國會議前後,一些人表現出援助蘇聯的“過度”熱情,我們的丘吉爾不得不採取措施適度遏制這種熱情。於是,丘吉爾在“戰略”上承認蘇德戰場“重大價值”的同時,在“戰術”上不能不適度貶低這一“價值”以免戰爭資源“過度”外流:“在俄國參戰後一年多的時期內,它在我們的心目中,與其說是一種幫助,毋寧說是一種負擔……俄國參戰並沒有立刻對我們有所幫助。德國軍隊是那麼強大,看來,在許多個月中,他們既能保持入侵英國的威脅,同時又能深入俄國。”
但蘇聯新盟友似乎還不領情,不知“感恩戴德”,無視大英帝國的“犧牲”,踐踏大英帝國的“恩惠”,進而提出一系列“貪婪”之要求,“超越”大英帝國高貴之軀的承受力。“咎由自取”之徒竟敢如此,這真真豈有此理!一時間我們的丘吉爾也憤慨不已。不過,他還是及時按捺住了自己的憤慨,及時拿出應有的耐心去忍受蘇聯“野蠻人”的“恫嚇與斥責”,合作的底線始終被牢牢地守著。看來,大英帝國的掌門人不愧為一位上乘的“平衡大師”,一切都精準拿捏:既要援助,更要讓受援者感受到援助的“來之不易”,要“珍惜”援助而不能有“非分之想”。是的,大英帝國對正義事業的每一份投入那都高貴得很,豈非那荼毒生靈的血腥戰場可比!
英國紳士丘吉爾總是覺得與溫文爾雅的羅斯福總統的和諧相處實難移到蘇聯“野蠻人”的身上,總是有一種莫名的東西需要忍受而實難忍受,對一切不得不和克里姆林宮打交道的人來說,“容忍是證明資格的標記”。確乎“辛苦”啊,精打細算的文明人豈能與“不講禮儀法度”的“野蠻人”站在同一條戰線,這世界本是精打細算文明人的,如今“不講禮儀法度”者也登上了“大雅之堂”,正以其前所未有的“野蠻”之勢衝擊著這“大雅之堂”,衝擊著這世界的一切。唉,不能忍也得忍,誰讓您老衰朽了,惜財惜命了,擔驚受怕了。
好了,下面我們還是看一下二戰期間大英帝國(包括加拿大)的援蘇成果,儘管雙方的關係總是磕磕絆絆,矛盾層出,但這一成果還算可觀:
英國和加拿大援蘇武器數量
|
飛機(架) |
7411 |
|
坦克(輛) |
5128 |
|
反坦克武器(門) |
4932 |
|
機槍(挺) |
4005 |
|
魚雷艇(艘) |
9 |
|
潛艇(艘) |
4 |
|
掃雷艇(艘) |
14 |
另外,大英帝國還援助了蘇聯不少軍用物資和戰略原料。
當然這一援助在雙方本國產量中所佔比重很低——即使加上更大規模的美國援助也是如此,而所援助武器裝備效能也不是上乘的,蘇聯自然還是主要靠自己的物質力量打敗敵人的。另外這一援助錦上添花居多,雪中送炭居少,蘇聯最艱難的時候援助往往少,而它不怎麼艱難了援助反而源源不斷,當然這既有上述那“忍痛割愛”的主觀因素,也有一些客觀因素——蘇聯最艱難的時候英美的戰爭經濟產量也不高,而本質上在於雙方的努力程度不平衡。
第二節 第二戰場問題
我們的丘吉爾忍耐也是有極限的,忍不下的那也是堅決不忍,而鬧心的第二戰場問題就是丘吉爾忍耐極限的標識。在我們丘吉爾眼裡,蘇聯新盟友一登場“就大聲疾呼地要求英國不顧危險與犧牲派兵在歐洲登陸,開闢第二戰場”,而他始終秉承“正義之氣”,保持堅定意志,“沒有讓這些相當可悲而可恥的事情來攪亂我們的心思”。看來此時大英帝國掌門人丘吉爾有一個很奇特的思想認識,似乎開闢第二戰場只會有利於蘇聯而絕不有利於英國,難道我們丘吉爾再次幻想著與法西斯和平相處?難道它找到了對盤踞歐洲大陸的法西斯禦敵於國門之外的良方?難道盤踞歐洲大陸的法西斯有一天真的打敗蘇聯後適可而止,不會回師英吉利?大錯特錯!誰說我們的丘吉爾不打算開闢第二戰場,只是現在不行,要等到1943年以後,不過當他擺出“這些相當可悲而可恥的事情”時,我們不免嚇了一大跳,還以為他陷入了幻想或找到了良方。
面對蘇聯“野蠻人”不顧“天時地利人和”,不顧種種“客觀條件”要求開闢第二戰場,精打細算的文明人看來有必要給大家講講什麼是真正的“禮儀法度”,不遵“禮儀法度”會造成怎樣的“血腥後果”。啊,敵人是那麼的強大,“我方”是那麼的弱小,在法國北部登陸,這簡直就是拿英國人民的鮮血和性命開玩笑!沒有空中優勢,沒有海上優勢,沒有大批特製登陸艇,沒有一支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軍隊,沒有……千萬種條件不具備,豈能開闢第二戰場!而敵人已經在“一年多時間的努力不懈”中讓法國海岸遍佈大炮、鐵絲網、碉堡,此乃實難攻克之堡壘也,更何況還有“那樣強大,那樣訓練有素,那樣裝備精良”的四十個師等著屠殺大英帝國那高貴而稀有的軍隊!看來,“我方”是不可能有“一年多時間的努力不懈”,更不會有“那樣強大,那樣訓練有素,那樣裝備精良”的四十個師。看了丘吉爾先生這一番高昂而可怕描述,我們還以為沒個數年準備,這個戰場不可開闢。不過還好,丘吉爾先生給出的承諾還沒有令我們太過失望:1943年以後我們就可以準備好了,但在這以前絕對不行,時間節點不可更改。是的,一個戰場是夜以繼日的戰鬥,一個戰場是年復一年的等待,這都是“秉性”使然,不可“更改”。
唉,蘇聯“野蠻人”就是冥頑不化,不解深意,“荒唐的說法和錯誤的論述仍然像瀑布一般傾瀉出來”。“俄國政府的首腦,既然有許多軍事專家提供意見,竟會有這樣荒唐的想法,這幾乎是令人難以相信的事。”看來,要同不遵“禮儀法度”者爭辯,“是沒有希望會得出什麼結果來的。”而駐蘇大使克里普斯也受到這“野蠻”的影響,竟然提出英國可以做出“一種超人的努力”來開闢第二戰場,這真真是可笑至極,在大英帝國這裡不存在所謂的“超人的努力”,它“沒有這些稟賦”!
蘇聯又提出英國可以考慮在挪威北部登陸,應該說這是丘吉爾當年很中意的一項行動,不過如今時移世易,丘吉爾已經把自己變成一個“兩手空空”者:“我們既沒有軍隊,也沒有可以用來實行這個計劃的船舶”,如何登陸?何況此乃北極極晝期,沒有戰鬥機掩護,明晃晃去登陸,豈不送死。當然如果是北極極夜期,丘吉爾就更直接了當了:“派往摩爾曼斯克的任何部隊都不能在冬季的‘永夜’中行動。”
丘吉爾料到斯大林會提出巴爾幹登陸計劃,特別提醒駐蘇大使克里普斯英軍在希臘和克里特島新敗的“慘痛教訓”,並指出大英帝國的真正“稟賦”:“即使在我們能運用地中海的船舶時,我們也費了七個星期的時間才把兩個師和一個裝甲旅運送到希臘”。更令丘吉爾奇怪的是,“人們竟忘記了當我們從希臘和克里特島撤退時我們的船舶和艦隊所遭受的損失。現在的情況遠較那時為不利,而我們的海軍力量也已經減弱。”看來,人們有點“瘋狂”了,有點“忘乎所以”,不遵大英帝國的“禮儀法度”了。
至於派遣“二十五至三十個師到俄國前線上去作戰”,更是荒唐至極。遙想當年大英帝國“船舶多而敵人的潛艇少的時候”,“還費了八個月的時間才越過海峽在法國境內建成十個師”。而如今它依然“經過了很大的困難”用了六個月時間才把第五十師運往中東。是的,丘吉爾說的都是事實:“我們所有的船舶全都用上了,要想騰出船隻來,只能從我們維持中東供應的那些關係重大的運輸船隊中撥出,或者從運輸援俄物資的船隻中撥出。我們只不過在勉強地維持著生活所需和軍火製造。”
唉,我們要體諒大英帝國的“難處”,作為盟友的蘇聯老大哥也要體諒它的“難處”。地中海生命線要保住,大西洋航運線要苦戰,中東殖民地要管住,亞太殖民地要安住,既要“安內”,還得“攘外”,那一塊能少得了大英帝國的照料。記得美國朋友在大西洋會議上曾建議,英國應該少點十八世紀的殖民主義,多點二十世紀美國的自由開放,如果我們順著這個建議走下去,英國可以膽子更大一點,不但給予殖民地人民自由開放,更給予他們積極性和主動性,讓他們把自己的力量組織和動員起來,我想個把法西斯都不夠打得,更何況開闢個第二戰場。不過,如此“逆天”的建議,可不能讓丘吉爾先生聽見,他會憤慨不已,他會氣大傷身,“他當英國首相的目的,並不是來主持大英帝國解體的”!
有這樣一個問題:在對蘇關係上,難道英國只有一種傾向、一種立場?難道只想著“親美”,而沒有意願“親蘇”?非也,“親美”是主導的,是英國統治階級主打牌,但“親蘇”傾向也在不同程度存在。首先,英國廣大人民群眾眼睛是雪亮,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他們認識到蘇聯人民的英勇戰鬥和巨大貢獻,批評本國軍政當局在戰爭中的某些不作為,要求本國政府“見賢思齊”,更大規模援助蘇聯,更努力地戰鬥起來。其次,英國統治集團內部一些人也有較強烈的“親蘇”傾向,從民族和國家利益出發,主張與蘇聯緊密合作,大力援助蘇聯,更積極努力戰鬥,儘快開闢第二戰場,徹底剷除歐洲法西斯,儘快結束戰爭,還英國和世界人民一個朗朗乾坤。最後,我們要說的是,“親美”和“親蘇”也非完全對立,“美”和“蘇”也非天壤之別,前者也在有意無意提醒英國不要保得過多,得放手時須放手,應把更多的心思放在自身而非別處。
還有一個問題:難道我們的大英帝國真的如此痛恨第二戰場?非也,它只是痛恨別人版本的第二戰場,只是深感別人的版本威脅到自己的第二戰場。丘吉爾和他的將領們早已多次表達了自己的第二戰場觀,而在阿卡迪亞會議前的那個綱領性文獻中,丘吉爾已經明確給出了自己的觀點。不管是小打小鬧逐步消耗,抑或經年準備以待時機,這一觀點的核心是主要靠所謂歐洲人民起義外加幾支裝甲部隊的登陸點綴來推翻納粹政權,而拒絕大規模派遣陸軍強攻歐陸。
這一觀點的底蘊是什麼?難道我們的老大帝國突然改旗易幟,走起“群眾路線”來了?其實啊,大英帝國想依靠在倫敦幹流亡買賣的人物來領導和推動“歐洲人民起義”,這些昔日的統治者大概在本國還有點群眾基礎,能搞點小打小鬧,給法西斯統治製造點小麻煩,而淪陷區的各國共產黨大力發動群眾,大搞抵抗行動絕不會成為大英帝國的“群眾路線”。在老大帝國這裡,一切都是小的,小打小鬧,格局小,眼光小,它幻想著靠這些小東西“折磨”納粹政權,等有一天把它“折磨”得神經衰弱、氣息微微,而後自己派一支小部隊登上大陸,“輕鬆”推翻之,讓這些流亡人物恢復昔日統治,恢復戰前原狀即可。當然,幻想中還有真實成分存在:大英帝國其實並不打算用它的“折磨”動搖法西斯統治根基,只是想削其鋒芒,去其攻擊性,使其不再“危害人間”,對其進行適當的改頭換面,而後恢復戰前的“和睦相處”即可。
啊!驚天動地的東西、滌盪乾坤的東西千萬不要發生在這塊帝國主義制度已立幾十年的大陸,而強大的軍事力量強攻歐陸,進而攻佔這片土地,卻會發生這樣的效果。如果這支強大軍事力量從西邊來,它大約可以保住自己日益下降的地位,但這大陸依然要改天換地,再立乾坤;若這力量從東邊來,它大約連苟延殘喘都輪不到了,那是要毀天滅地,那是要乾坤翻覆,那是要徹底的變色變質。不用說,對東邊的力量,它是要盡力拒止的,而對強大法西斯的戰鬥力量,它是有幾分期許的,這也許可以幫助它實現這一點。而對西邊的力量,它也是在暗暗阻撓。不管是美國參戰前商討中,還是參戰後的謀劃中,英美對如何重返大陸有著明顯的分歧,前者強調戰略轟炸、“人民起義”、外圍打擊、地中海翼側登陸等等,後者似乎一開始就不看好這些小打小鬧,卻在大力倡導“陸軍第一”、“陸戰至上”的理論,把歐戰一開始就看成一場大規模陸戰行動。有些東西早就開始暗暗謀劃了,只待時機成熟付諸實施。美帝要想改天換地,再立乾坤,跟著老大帝國小打小鬧怎麼能行,要幹就得大打大鬧,就得聲勢浩大地重返大陸,擊敗惡敵,樹德立威,成就金身。
當然,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這就要看它們的實力是否支援自己的想法,就要看他們的想法是否順應時代的潮流。想法歸想法,現實歸現實,人們既根據自己的想法行動,也得根據現實情況行動,想法只是表明它有某種行動傾向,當現實阻礙這一傾向時,它也只好退而求其次。某種行動傾向也好,退而求其次也罷,反法西斯這條路它必須走下去,不管是什麼東西,鬧得再兇,也不得不回到這條路上。
第三節 英蘇關係之其他
講了英蘇關係的主要方面,我們還要說說它的次要方面:蘇波關係問題,處理伊朗親德問題,對法西斯僕從國宣戰問題等。在這些方面,雙方照例合作與矛盾並存,對蘇聯的訴求,英國該滿足的還是盡力滿足,該掣肘的也不會放棄掣肘。
關於蘇波關係問題,之前我們已經做了介紹,雙方在蘇德戰爭爆發後經過一段曲折後恢復外交關係,決定擱置爭議,一致對敵,至於所爭議之事只能留待戰爭勝利後解決。在這個過程中,英國一方面也是力促雙方和好,確保反法西斯力量的團結;另一方面不無意圖利用雙方關係中的“瑕疵”行掣肘之實。丘吉爾振振有詞地宣稱要“義不容辭”維護波蘭這位“第一盟友”的利益,“不能承認1939年俄國佔領波蘭領土的合法性”,儘管當年大英帝國是“義不容辭”地袖手旁觀於“第一盟友”的滅亡。同時,他又以帝國主義強盜理由表示無意得罪蘇聯這個新盟友:“我們不能強迫我們受到嚴重威脅的新盟國……去放棄它世世代代認為對於它的國家安全是最重要的那些毗鄰它的邊境的地區。”表面上是左右為難,實則左右逢源,左右掣肘。
事實上,蘇波關係問題只是整個蘇聯西部邊界問題的一部分。蘇德戰爭一爆發,蘇聯不時向西方諸君表明自己的“苦惱”:想讓自己向西擴張幾百公里的西部邊界獲得後者的承認,想讓自己吞併的領土獲得合法性。西方諸君自然輕易地就抓住這個軟肋,一方面擺出各種理由,包括拿《大西洋憲章》說事,表明無法承認蘇聯的領土擴張;另一方面,面對蘇聯巨大的戰爭貢獻,又在不斷鬆口,一再傾向於作出這一承認。看來,蘇聯老大哥不得不被人家牽著鼻子走,儘管這是個不大不小的掣肘,足以讓蘇聯老大哥表現出“英雄氣短”而不得不向西方諸君作出某些讓步。
伊朗親德問題。上一卷我們在介紹中東地區時,曾將其分為北、中、南三塊地區,而北邊的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一線處於法西斯德國的影響下,土耳其雖然在蘇德戰爭爆發後出現親德傾向,總體還保持中立,伊朗和阿富汗就不同了,乘著蘇德戰爭的大潮,親德傾向越來越明顯,而法西斯德國也是加緊向這些地區展開政治、經濟、軍事滲透,這無疑引起了英國和蘇聯的忌憚。
伊朗地處蘇聯和英國中東殖民地之間,北可威脅蘇聯後方,西可威脅英國中東戰區的後方。我們說了,丘吉爾早就想對伊朗動手了,前段時間平定了伊拉克、黎巴嫩、敘利亞等出現的各種隱患,現在騰出手來終於可以解決伊朗問題了。而蘇德戰爭爆發後,英蘇也在這個問題上找到了共同語言。雙方先禮後兵,要求伊朗主動放棄與德國的合作而與英蘇合作,伊朗統治集團還想困獸猶鬥,不過英蘇雙方不給機會,迅速出兵(蘇聯五千人馬,英國數萬人馬),於1941年9月間完成了對伊朗的佔領,平定了這個後方之患。伊朗也滿足了英蘇要求,驅逐德國勢力,完全向英蘇靠攏,而大英帝國再次完成了一項“安內”大業,隨後它迅速掌控了伊朗南部的石油產區,而蘇聯也想在伊朗北部擴大影響力。英蘇解決伊朗問題當然也得到美國的鼎力支援,伊朗曾向美國求援,但美國明確表態,它必須與反法西斯力量合作。伊朗的佔領也為英美援蘇開闢了新的通道,這一通道相對於北極的海上通道安全多了,當然距離也遠多了。英美的物資可以繞道好望角,在運往中東地中海戰區的同時,一部分也可轉運蘇聯。隨後英美開始完善伊朗的交通設施,擴大通行能力,物資由此從南面輸入蘇聯。另外,對阿富汗,英蘇雙方如法炮製(不過未動刀兵),完成了對德國勢力的驅逐。
對法西斯僕從國宣戰問題。英國雖然早就對德宣戰,不過蘇德戰爭爆發後又出現了新形勢,蘇聯向它提出了對其僕從國宣戰問題。丘吉爾雖然很不情願,但不得不滿足蘇聯新盟友的要求。他不情願,是因為還不想割斷與這些國家反動統治集團的關係(以備不時之需),但是相對維持與貢獻巨大的蘇聯新盟友的關係,這些關係該割還是要忍痛割的。丘吉爾提出了一個折中辦法,即準備透過“說服教育”讓這些國家退出戰爭,蘇聯的答覆可以這麼做,但必須有個期限。在這樣的形勢下,“說服教育”只能以失敗告終,於是英國只好滿足蘇聯要求,成為這些僕從國法律上的敵人。
最後還有個問題需要說一下:英國要求蘇聯對日宣戰問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就是否要求蘇聯對日宣戰,英國內部也進行了討論。討論的結果是,還是不要求蘇聯對日宣戰為好,因為讓蘇聯堅守在歐洲戰場就是最大的利益,如果武斷地讓它分心於亞太戰場,反而得不償失。看來,英國的政治家還是能夠做出實事求是決定的,該體諒的時候還是能體諒的,該大公無私的時候還是可以大公無私的,合作嘛,是相互的,不是單方面的,不應只要求而拒絕被要求。
第四節 英聯邦內部
這一時期,英聯邦內部關係既有合,也有分,合的是大敵當前,英聯邦內部繼續能夠保持一致——不管是自願還是被迫保持——的反法西斯目標,大英帝國繼續可以統御英聯邦內的各種資源為反法西斯服務;分的是不管是自治領還是殖民地,與大英帝國“離心離德”傾向越來越明顯。對反法西斯來說是合,對大英帝國來說是分。就自治領而言,終整個二戰,它們的實力都不斷增強著,它們的獨立性也隨之不斷提升,它們有些不太願意待在英聯邦,而更願意與強大的美國走在一起。至於殖民地,更不待言,獨立解放的決心只有更堅定沒有稍減弱,只有永向前沒有稍後退,儘管因反法西斯大局,鬥爭表面上不得不蟄伏起來,但力量正在蓄積著以實現最後的爆發。
這一時期,各自治領繼續處於戰爭動員中。加拿大作為經濟最發達的自治領,自西歐戰役失敗以來就開始了全面動員,並沿著從屬於美國壟斷資本和兩國軍事生產一體化方向發展,事實上這一時期美加關係節節攀升,經濟上一體化和政治上緊密結盟,正在把它們融合為統一戰爭經濟體系。當然加拿大與英國的傳統經濟聯絡繼續保持著,事實上這一時期,英加關係更類似與英美關係,即英國在戰爭資源上主要依賴美國的同時,也很大程度上依賴加拿大。加拿大繼續作為戰略原料基地在英美的戰爭體系中發揮作用,其生鐵產量從1941年155.3萬噸增至1942年200.7萬噸,鋼錠產量從246萬噸增至286萬噸,鋁產量從19萬噸增至30萬噸。加拿大是許多貴重原料(鋁、鎳等)的極其重要的供應者。
加拿大的軍事實力也不容小覷。戰爭動員開始後,加拿大政府用於軍事目的的開支從1940-1941年度的7億多加元增至1941-1942年度的13億多加元,佔比則從60%增至71%,其製造的武器產值從1941年的8.2億加元增至18.6億加元。各種武器裝備,小到槍炮彈藥,大到坦克、飛機、軍艦,乃至雷達等,加拿大均可生產,英國的一些重要飛機型號(蚊式、蘭卡斯特式等),加拿大也可負責生產,它正在成為英國的重要武器庫。整個二戰,加拿大共生產了80萬輛卡車,4萬門火炮、5萬輛坦克、170萬隻槍支和300多艘萬噸以上商船等。在這一生產動員中,加拿大的工業實力急劇增強。另外,千萬人口的加拿大在二戰中也動員起百萬大軍,其軍隊活躍大英帝國下各個戰場。
加拿大是租借物資的重要供應者,它對英國的租借以饋贈的形式進行,1942年4月,加拿大給予英國第一筆饋贈,解決它當時欠加拿大的全部債務,緊接著,加拿大又貸款10億美元,確保英國可以在1942年採購其糧食、原料和武器。另外,加拿大在整個二戰中還向蘇聯提供了11億美元的租借物資。不過,美加雙方的經濟聯絡並不是建立在租借基礎上,因為它們都是戰爭經濟的出超國,完全可以透過正常貿易渠道滿足各自的戰爭經濟需要。看來,不是加拿大有求於英帝而是英帝有求於加拿大。
地處南太平洋上的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雖然趕不上加拿大,但也在戰爭中努力增強自己。很長一段時間裡,這兩國只是英國的原料和糧食的供應者。但隨著太平洋局勢的惡化,他們也加強了自身的動員。澳大利亞在金屬生產方面做了很大努力,生鐵產量從1941年的147.8萬噸增至1942年的155.8萬噸,鋼產量則從164萬噸增至170萬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軍無力顧及太平洋上的諸自治領,澳大利亞便加速建立航空、造船、坦克等軍工部門,並擴大現有軍工部門的規模。紐西蘭也做出了類似的努力。兩個自治領同時也大規模擴軍,增強自衛能力,它們的軍隊依然追隨大英帝國的軍隊,活躍於它的各個戰場上。
這一時期,澳大利亞與母國英國頗有齟齬,根本原因就是太平洋戰爭一爆發,英軍一敗再敗,未能守住自己的太平洋殖民地,而讓澳大利亞暴露在日帝侵略鐵蹄前。1941年9、10月間,澳大利亞就要求英國撤出北非戰場的澳軍部隊,調回本土,應對日益惡化的太平洋局勢,看來從這時起,澳大利亞就對其母國在太平洋的實力和決心不敢抱太大希望。我們丘吉爾是苦口婆心想留住澳大利亞軍隊,而它卻是一去不復返。澳大利亞是全力擁戴美國在太平洋戰場的領導權,視美國為這一戰場的真正救星。
另外,南非作為英帝的自治領之一,其戰爭經濟也在不斷髮展,向英帝提供許多軍需物資和武器裝備。在戰爭需求帶動下,二戰期間南非的加工製造業產值增加了近100%,它的工廠能生產裝甲汽車、大炮、子彈等武器裝備,能生產羊毛製品、制服、鞋靴等作戰物資供英軍使用。而南非軍隊也是北非英軍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為英軍北非作戰也做出了重要貢獻。
這一時期,大英帝國的中東殖民地表面上保持著穩定,從衣索比亞到伊朗已經都處於它控制之下,乘著戰爭之勢,其殖民大權又有擴張呀,當然這只是反法西斯大局支撐下的迴光返照而已。
好了,下面還是說點“安內”的事兒。1941年下半年,鎮壓伊拉克民族獨立力量的“十三日戰爭”結束了,也消除了法西斯滲透黎巴嫩和敘利亞的隱患,儘管黎巴嫩和敘利亞大鬧獨立情緒,不過那是法帝(“自由法國”)的事兒,跟它沒關(確切一點說它還是這一獨立情緒的幕後支持者)。當然,獨立情緒無時無刻不存在著,英帝稍一鬆勁兒,它就會冒泡。這不,靠近戰場的埃及這會兒又發生了一次異動,原因嘛,還是來自戰場。1941年末和1942年初,英軍在北非戰場總算開啟新的戰鬥,但卻又是一個先勝後敗的結局。
恰在此時,戰爭引發的民不聊生也發揮了“作用”,而更有法西斯第五縱隊挑撥離間,統治集團親法西斯勢力異動不斷。乃至“極端主義”學生上街遊行,西里內閣提交辭呈,一時間大英帝國在埃及有些“內憂外患”、“危機四伏”。不過它還是老辦法,果斷行動,撤換不中用的西里內閣,啟用頗孚眾望的華夫脫黨領袖穆斯塔法•納哈斯組閣掌權,最終穩定了局勢,“安定了民心”,此任內閣是戰爭期間最配合大英帝國的內閣,大英帝國的“安內”行動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但是此任內閣再次表達了埃及人民的決心,那就是戰時我們可以配合英帝作戰,但戰後我們是一定要實現獨立的。
這一時期,亞太殖民地出現新的局面。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帝攻城略地,席捲東南亞,前鋒直逼印度東北邊境。英帝的大部分殖民地淪於敵手,殖民地人民開始拿起武器,自願組織起來反抗法西斯統治,同時為將來徹底推翻殖民統治蓄積著力量。而面對法西斯入侵威脅,印度的內部局勢不能不發生震動,民族獨立力量不能不向英帝殖民當局更強有力的呼籲:堅決要求印度獨立。為了穩定印度局勢,英帝決定“先禮後兵”,與國大黨展開談判,明確表態戰爭期間決不放棄印度,至於戰後嘛,我們的英帝有些“模稜兩可”了,開始玩起花樣來了,而實質是萬變不離其宗,它永遠都不會輕易放棄印度。好了,話不投機半句多,談判不成,就要“兵戎相見”了。國大黨發出強有力呼籲,要求英帝退出印度,並積極在印度群眾中籌劃的不服從運動,殖民當局則先下手為強,立即展開鎮壓,立即逮捕了國大黨所有領導人,並全部關押到戰後(甘地因病於1944年3月被釋放),隨後印度廣大群眾展開反擊,暴力鬥爭此起彼伏,獨立的能量繼續聚集著。
當然,英帝還是取得了暫時的勝利,穩住了局面。在反法西斯大局面前,印度民族獨立力量還是未能把握好方向,片面地把獨立鬥爭與反法西斯鬥爭的對立起來,過分反對參加反法西斯戰爭,而要求英帝立刻退出印度在大敵當前也非適宜之舉。而少數人則走向另一個極端,幻想與日帝法西斯合作驅逐英帝勢力。在對付印度民族獨立力量時,英帝還常常使用分而治之的伎倆,利用印度民族和宗教矛盾,偏向和倚重穆斯林聯盟來反對國大黨獨立鬥爭,當然穆斯林聯盟最終也是要求獨立的,英帝只能暫時利用這一矛盾。國大黨少數領導人(尼赫魯等人)和印度共產黨提出了正確的主張,即主張支援英國反法西斯行動,保衛印度免受法西斯侵略,同時要求英國給予印度以獨立地位,但這一聲音未能成為國大黨的主要聲音。印共在1942年被殖民當局宣佈為合法組織,由地下轉入公開,其力量也隨著形勢的發展不斷壯大,但始終未能取得民族獨立運動的領導權。
好了,大英帝國的那些事我們就介紹到這裡,老大帝國是一個龐大的體系,此處介紹的只是它的幾個跟戰爭直接有關的“代表人物”。六大洲、四大洋,何處沒有它的私產,何處沒有它的掌控,若把這個龐大的體系真正發動起來,那是要驚天動地的,不過我們的丘吉爾可要成為一個“主持大英帝國解體”的首相了。
這一時期,大英帝國在中東戰場還做了一件大事,即成立了國務大臣辦公室和中東補給中心,依靠了這兩大機構,全面掌控中東政治經濟一切情況,全面管控協調中東一切事務,統制其經濟,統一其政治,穩固中東大後方,把中東建設成僅次於其本土的第二大作戰基地,也為戰後繼續維持其殖民統治鋪墊新的道路(下面我們還會介紹)。
最後,我們顯然有必要再次展示一下非洲人民對大英帝國戰爭努力的貢獻,對這場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非洲的礦產資源、農副產品和各種作戰物資,非洲豐富的人力物力資源都是大英帝國和後來參戰的美國所不可或缺的。黃金海岸的錳產量在二戰期間增加了近100%而成為盟國錳礦最大供應者,北羅得西亞銅產量1940年比1935年增長近86%,奈及利亞的錫產量1938年至1943年增長41%,賴比瑞亞成為戰爭期間盟國主要橡膠供應國,第一批原子彈就是利用非洲的鈾礦製造出來的……我們不應忘記英美盟國製造出的每一件武器裝備,製造出每一顆炮彈和子彈都有非洲戰略原料的份額。1萬多非洲勞工為塔科拉迪-卡諾-喀土穆美國空運部隊修築基地,1.3萬非洲勞工為運出黃金海岸南部鋁土礦而參加了相關公路和鐵路的鋪設工作,蘇丹為鋪設從博爾至傑拜萊茵的道路平均每月投入5萬個勞動力,埃及動用20萬為英美盟軍修築各種軍事工程……我們不應忘記英美盟國為戰爭需要大批徵用非洲勞動力資源。大戰期間被徵召入伍和自動武裝起來的非洲人約有150萬,在各反法西斯國家軍隊中從事勤務工作的非洲人約有100萬,非洲戰士與英美戰士並肩作戰,其戰鬥足跡同樣遍及歐非亞諸洲,他們同樣為這場戰爭付出了巨大傷亡。
第五節 自由法國
行文的最後,我們再說說自由法國的情況。這段時間,戴高樂率領著自由法國顯然沒有閒著,在敘利亞和黎巴嫩問題上繼續與英帝維持著又鬥爭又合作的局面。現在自由法國也算是有根基了,家大業大,人才多了,人馬多了,影響高了;因此戴高樂覺得有必要成立一個政權性質的機構統領自由法國事業,使自由法國運動更多地帶有政權性質,使名更正、言更順,更能與反動腐朽的維希法國分庭抗禮,在與列強們的交往中更能居於平等地位。1941年9月成立的自由法國“民族委員會”就是這樣一個機構,戴高樂自然是它的最高首腦,它下設多個委員,分管自由法國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事宜。另外到1942年底,自由法國也有七萬人馬了,陸海空三軍樣樣俱全,還有自己的商船隊。自由法國的軍隊積極參與英軍的各項行動,作戰英勇,贏得大家越來越多的認可。戴高樂覺得自己的自由法國有點政府氣象了,雖未得到世人的承認,但正在得到更多人的認可和信賴。
這段時間,自由法國的行動主要對外和對內兩個方面展開。在對外方面,戴高樂力求得到列強們更多的認可和幫助,同時也堅決抵制它們對法帝利益的侵犯,繼續保持其毫不相讓的鬥爭風格。這段時間,英國對自由法國那肯定是繼續保持又欺負又合作的關係,在敘利亞和黎巴嫩問題上,在馬達加斯加問題上以及在其他問題上,不時鬧得戴高樂很不愉快。當然戴高樂不愉快達到極點時,英國馬上會換上一幅合作的面孔,表現出安撫的姿態。可以欺負但絕不能鬧掰,這繼續是英國的底線。而相對於崛起的美蘇,英法兩個帝國主義衰落者是有“同病相憐”之處的,多提攜提攜自由法國在英國的政策中還是佔上風的。物質上援助自由法國、幫助自由法國加入聯合國家、協調自由法國與美國的關係等等,英國能幫助還是會盡力幫助的。
對桀驁不馴的戴高樂及其自由法國,美帝的厭惡之情“由來已久”,對問鼎世界“領導權”的美帝來說,這樣的人物自是不被看好。不想讓它加入聯合國家,這是其一,而未經美帝允許,它就奪佔了加拿大旁邊的兩個法屬島嶼【注1】,更令美帝不高興至極。另外,美帝至今沒有斷絕與維希法國的外交關係。當然也不能說雙方的關係鬧到了不可開交的程度,一方面美國一直不怎麼認可自由法國,一方面也在適度改善對其的關係。首先,大家都是反法西斯中人,抬頭不見低頭見,老僵持著對美帝也沒有好處;其次,戴高樂的威望畢竟是在不斷提升,得到法國人民和法西斯諸國越來越多的認可;最後就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南洋諸地淪陷,而一些法屬島嶼【注2】位於太平洋中心地帶,其重要性上升,美國需要自由法國合作,獲得這些島嶼的駐軍權。總之,美國與自由法國最終依然是鬥爭加合作的關係。【注1:即聖皮埃爾島和密克隆島,位於加拿大紐芬蘭島以南25公里處。】【注2:新喀里多尼亞、馬克薩斯群島、社會群島等。】
自由法國建立對蘇聯的關係基本沒費太大的周折,蘇德戰爭一爆發,維希法國在法西斯德國的逼迫下斷絕對蘇關係,戴高樂則乘勢而上,建立對蘇關係。雙方沒有太多的利益糾葛,但卻有一些共同的東西值得利用:自由法國可以倚重蘇聯來制約一下英美的強勢。而蘇聯也有相同的意圖,明確表示全力以赴支援自由法國事業。另外,自由法國還建立了對中國的關係,還加強了倫敦諸流亡政府的關係。總之,經過兩年來的努力,自由法國在國際舞臺上算是有一席之地了。
再看看對內方面。這段時間,自由法國的對內工作就是如何統領日益壯大的國內抵抗運動。蘇德戰爭爆發了,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歐洲人民的抵抗運動也進入新階段,向更高潮發展。看到國內人民的抵抗運動有起色了,戴高樂也開始把自己更多的關注轉向這裡。戴高樂考慮的是如何把國內抵抗運動統領到自己的麾下,這一考慮有積極的一面:國內抵抗運動雖然發展起來了,但分散性有餘統一性不足,各幹各的買賣,缺乏一個領導中心,而自由法國以其威望正好可以發揮領導中心的作用。戴高樂先後向國內派出自己的代表實現了國內南方(維希統治區)和北方(敵佔區)抵抗運動的分別統一,當然這個統一是分散基礎上的統一,而非絕對的統一,這是符合敵後鬥爭實際的。
當然,戴高樂的考慮自然少不了其消極的一面:決不允許這場人民自己發展起來的運動超過戴高樂規定的界限,威脅到資產階級統治根基。人民自己的運動從來都是“野蠻生長”的,很容易越過雷池,戴高樂統領它就是要把它“皈依正道”。尤其是這個運動中還有一個“重要人物”——共產黨,戴高樂絕不允許它“另立門戶”,脫離戴高樂的掌控而單幹。人民抵抗運動嘛,最終只能起配合作用,光復法國還得靠外邊的力量——靠英美盟軍的拯救,戴高樂就是這樣告訴我們解放法國的思路。
當然,總體來說,這段時間,戴高樂對國內抵抗運動是鼓勵多於限制,而對法國共產黨也更多是合作而非打壓,而國內抵抗運動越發展,自己在對外合作和鬥爭中也底氣更足。與此同時,戴高樂也經常表明自己的自由法國事業是一項革命事業,是一項要改變法國人民命運的事業,是一項革故鼎新的事業——儘管是資產階級範圍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