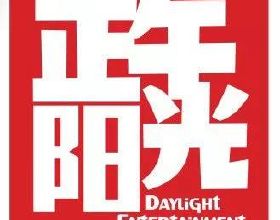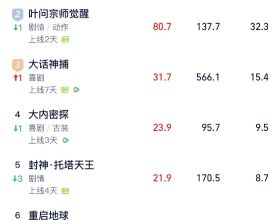為什麼會存在鄉愁呢?哲學家自然有其解釋,但我試圖從經濟學角度進行分析,提供一種新思路、新觀點。
(本文原載《幸福經濟學》一書)
在中國作家筆下,鄉愁(即遊子對故園之情的懷想以及對倫理親情的渴望。這裡所說的“故園”,包括精神上的家園)是永遠寫不完的題目。從《詩經》“懷哉”之思(《揚之水》)、“不歸”之嘆(《東山》)到漢魏古詩的“遠望可以當歸”(《悲歌》),再到“他鄉生白髮,舊國見青山。曉月過殘壘,繁星宿故關”的感嘆(秦觀《望海潮·梅英疏淡》),不絕如縷的鄉愁,成為一種普遍的心聲。
為什麼會存在鄉愁呢?哲學家自然有其解釋,但我試圖從經濟學角度進行分析,提供一種新思路、新觀點。
對於經濟學者而言,要解釋鄉愁,首先需要明白經濟學意義上的人生。
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人生不過是一個不斷滿足慾望(精神的和物質的),或不斷追求幸福(收益或效用)的過程。現代的主流經濟學認為,人人都有慾望,慾望得不到滿足就感到焦慮和痛苦,幸福就是從焦慮和痛苦中獲得一定程度的解脫。在這方面人與動物無異。每個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一個美好社會於是應當“使最大多數的人獲得最大程度的幸福”。
但是,滿足慾望的東西(資源)是有限的,包括我們的時間(如果時間無限,我們什麼想法都可以實現),於是,我們需要做出選擇,將這些有限的資源發揮儘可能大的作用。如何選擇?我們消費或者享受任何一種資源,從中得到的好處,是逐漸減少的,這在經濟學上被稱為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但邊際效用遞減並不說明人生是悲觀的。因為,它迫使我們選擇豐富的生活,換句話說,我們生活的多樣性(包括消費的多樣性),可以帶來最大化的效用或幸福。儘管“單項”消費帶來的幸福是減少的,但是,隨著“項數”的增多,我們得到的幸福感覺會增加。但這並不是“貪得無厭”。比如凡高的《向日葵》,如果同樣的一幅,則任何一個字畫收藏家都會異常興奮,但如果某收藏家再擁有同樣的一幅畫,則興奮的感覺將削弱。如果增加的是其他畫家的畫,他將非常樂意。
對於那些處於漂泊狀態的人而言,當你生存在一個陌生的城市(非出生地),如果融入其中,則你面臨的生活內容的選擇是很多的,包括消費(精神和物質)的種類。那麼你的加總的幸福或效用是持續上升的。如果整天面對的都是那些老面孔,生活老是那麼單調,除了工作、家庭,沒有其他的消遣與休閒,則因為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作用,你可能很快厭倦這種生活方式。而外面的世界是變化的,如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里特所說的,“太陽每天都是新的”。如果你不隨著外界的改變而改變,必然產生“沒有家”的感覺,也就是說,你沒有跟上時代的步伐,從而被這個“時代之家”所拋棄,處於暫時的“無家可歸”狀態。
當然,前面討論的是一般情況下。現實中,在不同的約束條件下,鄉愁的表現或程度是不同的,特別是確定性程度不同的時候。
中國人的鄉愁程度與西方人的就很不相同。西方的一系列宏篇鉅著如荷馬的《奧德修記》、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等,都是以離鄉——漂泊——還鄉(或有較好歸宿,包括肉體和精神兩方面)為基本模式,循著他們的行動、行為在時間中演進的形態,濃墨重彩的講述了主人公奧德修、魯濱遜、哈克貝利等的漂泊歷程及他們的英雄業績和心理活動,展示了人類在對自然進行鬥爭,征服世界以及追求自由過程中表現出的生命的偉大和莊嚴。
相比較而言,中國作家傾向於對內在世界的審視與守護,表現的物件指向內在的心理空間,關注自己的生存,張揚一己的悲歡,用躲避現實來維持心理的平衡。與此相對應,中國作家表意的依託,多半是柳、雁、夕陽、浮雲、猿啼、春草、春水、漂萍、轉蓬等。蘊含這些意象的詩句俯拾即是:“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詩經》);“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韓愈《酬程延秋夜即事見贈》);“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古詩十九首》);“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歐陽修《踏莎行·候館梅殘》);“一聲鄰笛殘陽裡,淚灑空堂淚滿衣”(錢起《哭曹鈞》);“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李白《送友人》)等等。這些意象都是精巧柔弱又悽美無比的。
為什麼中西方人們的鄉愁觀念差別如此之大?我認為,西方的人們由於邊際效用遞減,不安於現有的家園,試圖尋找新的家園;而中國的人們,由於屢屢失去家園,給未來的生活增添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從而留戀和懷念家園。
分析西方文學作品可見,《伊利亞特》的英雄們離鄉背井,苦戰十年終於將特洛伊城毀滅,勝利凱旋。《奧德修紀》中英雄歷經十年漂泊返回家園。史詩結尾,在英雄重整家庭秩序後,神諭暗示奧德修將再度離家,完成新的使命、建立新的功績。在《魯濱遜漂流記》中,魯濱遜的出遊,起因於對平靜的家庭生活的厭倦。於是,他違背父親的願望,私自出海經商。這些都預示了一種開放、流動、進取、征服而非封閉、固守、退縮、安於現狀的價值取向。
但是,中國的情況截然不同。不妨以一首鄉愁詩詞來分析。如宋朝蔣捷的《一剪梅》:
一片春愁待酒澆。江上舟搖,樓上簾招。秋娘渡與泰娘橋,風又飄飄,雨又蕭蕭。
何日歸家洗客袍?銀字籤調,心字香燒。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
這首詞中最值得玩味的是“何日歸家洗客袍?”實際上,“銀字笙調,心字香燒”,只不過是一閃即逝的記憶,這些不過是“夢裡不知身是客”的一時自我陶醉罷了。夢醒時分,還是要面對“流光容易把人拋”的無情現實。
蔣捷這首《一剪梅》,大約作於宋亡之際。當時,可謂無“家”可歸。國都沒有了,那裡還有家?宋亡之後,蔣捷隱居太湖竹山,人稱竹山先生。所以,這首詞可以看作當時民生遭際的一個剪影。與蔣捷同時代,類似意境的詩詞很多。“悠悠遠別離,分此歡會難”(韋應物《寄盧庾》),“此去經年,應是良塵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柳永《雨霖鈴·寒蟬悽切》)……對顛沛流離的苦難有著深刻體驗的作家們對離別看得無比重要,對重逢懷著一種不敢奢望的悲觀,對別後的孤寂悽清又表現出一種避之不得的懼怕。
梳理資料可見,中國古代的文人大多描寫過鄉愁——離別的愁緒。頻繁的離別,是因為頻繁失去家園。而家園的失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古代戰亂遠遠多於和平。根據歷史學家葛劍雄教授的研究:如果以歷史上中國最大的疆域為範圍,統一的時間是八十一年;如果把基本恢復前代的疆域、維持中原地區的和平安定作為標準,統一的時間是九百五十年。這九百五十年中有若干年,嚴格說是不能算統一的,如東漢的中期、明崇禎後期等。
每逢動盪的時局,都會產生鄉愁絕唱。人們流離失所,四處漂泊,鄉愁的感覺就非常深刻了。除了前文分析的宋亡之後蔣捷等文人的作品,東漢末年,社會動盪,《古詩十九首》應運而生。《古詩十九首》的基本情感內容是離情別緒、人生的失意和無常之感。如《涉江採芙蓉》寫遊子想念家鄉的妻子,要採摘花草寄送相思;《明月何皎皎》開創寫月圓的情境表達思鄉情感。
又如,唐朝“安史之亂”之後,鄉愁詩急劇增加,劉長卿、韋應物等詩人均有大量的懷戀家園的詩作。值得一提的是張繼的《楓橋夜泊》:“月落無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這首千古絕唱,是在安史之亂中,張繼逃難到江浙一帶寫的詩。
而今的中國,已經步入太平盛世,古人那種顛沛流離不再。人們感受的是新的鄉愁。由於正在經歷工業化與都市化的過程,絕大多數人的集體經驗就是“離鄉”、“懷鄉”、“他鄉作故鄉”的三部曲。以故鄉為主題的種種懷想,就成了“鄉愁”。不過,不久的將來,全球化之下,人們都生活在“地球村”,可能不僅失去“故鄉”,恐怕連“鄉愁”也將失去。因為更頻繁、更大幅度的流動,將讓更多人不知如何回答“故鄉哪裡”這樣的問題。沒有故鄉,自然也就沒有鄉愁!沒有“懷鄉”問題的一群,或許正是最能適應全球化發展的最佳勞動預備軍,可以毫無羈絆地在全球流動。未來,他們或許放棄“家庭”,更徹底地原子化,以便於流動,以適應全球化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