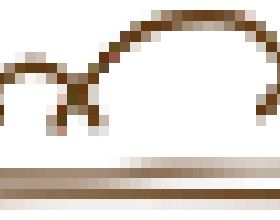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薛力
世界正處在文明競合的時代,而不是文明衝突的時代。這是一個長週期,將構成本世紀國際格局的基本面。當代頗有爭議的美國保守派政治學家、以“文明衝突論”聞名於世的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的錯誤在於:把文明間的衝突當作後冷戰時代的基本面,並從基督教一神論的觀點看世界。
文明競合時代的主要特徵是:
1、西方文明主導世界的歷史已經過去。
沒有一種文明有主觀意願與客觀能力主導世界,“多種文明互相競爭,在競爭中合作、合作中競爭”成為文明間關係的主基調。一部人類歷史,雖然衝突頻仍、戰爭多多,但整體而言依然是合作多於衝突。這是人類社會得以發展的必要條件。歐洲國家制造兩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是,喪失了領導世界的正當性與實力。歐洲國家轉而透過聯合謀求自強,並逐漸轉向“以觀念與規範引導世界”,與美國既協作又競爭。
冷戰時期,兩極對抗格局嚴重弱化了雙方的安全感,迫使雙方都在安全領域投入大量資源,相對弱勢的一方投入的比例更大。兩大集團都難以聚焦經濟與社會發展。兩極對抗消失後,經濟與社會發展自然成為各個文明體的主要追求。宣稱“文明間的衝突是時代特徵”,無疑是放大矛盾,把支流看成了主流。
造成這種認知與判斷的深層原因是基督教的價值觀:它把世界上的人分為教徒與異教徒兩類,認為教徒是上帝的選民,有責任與義務把上帝的福音傳遍全世界,其途徑是透過傳教、征服等手段同化甚至消滅異教徒,並把母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制度移植到這些地方。這是地理大發現以來歐洲人在全世界乾的事,也是冷戰時期美蘇兩國的行為邏輯,更是冷戰後美國外交的邏輯起點。
許多學者常常提到,美國政府與精英偏好製造對手與敵人。但鮮有人指出,其根源也在基督教一神論價值觀。基督教世界的學者都不自覺地從基督教一神論的觀點看問題,薩繆爾·亨廷頓、約翰·米爾斯海默與保羅·肯尼迪是典型,身為猶太人的亨利·基辛格、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瑪德琳·奧爾布萊特等整體上也未脫此窠臼。
冷戰後,和平與發展是世界各國的普遍追求。局部發生的戰爭與文明間的衝突並非世界圖景的基本面,經濟全球化、跨文化交流才是。全球經濟的發展與跨國流動的增加端賴於此。美國製造次貸危機並殃及全球之前,國際格局多極化的說法遠非共識,但經過十來年間的折衝,現在“國際格局多極化”的判斷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國際問題研究者所認同。文明競合是一種新型多極化。
2、“議題同盟”的作用上升,特別是在安全領域。
這一論斷的背景是:世界大戰不大可能發生。核大戰沒有贏家,參與方都將遭受重大損失乃至毀滅,甚至人類文明都可能被毀滅。國際關係學界普遍認為,冷戰期間,核威懾導致的恐怖均衡(balance of terror)有效阻止了美蘇之間的大規模戰爭。冷戰結束後,“歷史終結論”的信念讓美國覺得核武器的作用下降並大規模減少核武庫規模。在文明競合時代,核武器的作用又上升,但“恐怖均衡”依然成立。中美俄法英五個核國家2022年1月3日達成的聯合宣告中強調“核戰爭打不贏也打不得”就是一個證據。
在文明競合時代,文明間的衝突顯然不會消失,但不會發展成主要文明(或其代表國)間的全面戰爭。衝突與戰爭依然會在局部發生:既可能在不同文明之間,也可能在亞文明之間,甚至在同一亞文明內部。較大可能在新教-天主教文明與伊斯蘭教遜尼派文明之間以代理人戰爭的形式出現,也不排除在東正教文明與東儀天主教文明之間發生(編注:東儀天主教是從希臘正教會、俄羅斯正教會和一些較小東方古老教會中分離出來而參加天主教會者。東儀天主教現有信徒約1600萬,佔天主教全體信徒1.5%)。最大的可能性發生在代表新教-天主教文明的美國與某個國家之間。不爭的事實是:美國是二戰後參與或發動戰爭次數最多的國家。它有“文化基因”、能力與意願這麼做。在文明競合時代,美國在這方面會有量的改變(因為能力與意願在下降),但很難有質的改變(因為“基因”難以改變)。
地理大發現以來的歷史表明,信奉基督教一神論的國家多偏好建立軍事同盟以打壓對手、保護自己。在文明競合時代,構建軍事同盟——特別是北約這樣的大規模同盟的難度上升。作為應對,美國一方面傾向於構建小規模的同盟,特別是在與同文同種的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之間。另一方面,就某個議題構建同盟成了便利的選擇,因為比較容易動員相關國家參與其間,也便於美國弱化乃至休眠這樣的“議題同盟”。
3、文明內卷(或“文明還原主義”)成為普遍現象。
冷戰後在伊斯蘭國家再度興起的伊斯蘭復興運動與對政治伊斯蘭的追求無疑是文明內卷的典型案例。新世紀以來,文化內卷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出現。
普京就任俄羅斯總統後大力提高東正教的地位與作用,包括促成俄羅斯境內外兩大東正教會的統一。東正教會也強化自身的政治參與,如反對北約東擴。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上臺後,世俗主義(這是凱末爾確定的土耳其立國六原則之一)不斷被弱化、伊斯蘭教在土耳其政治與文化領域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次貸危機後美國開始全球戰略收縮,並演化出孤立主義色彩濃厚的“特朗普主義”。印度總理莫迪推行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力度遠遠超過了歷屆印度政府,並且在立法中公然歧視穆斯林群體。歐洲國家對接納大規模難民的態度從積極轉向消極,歐盟更為注重“歐洲價值觀”,以便進一步發揮“規範性力量”在全球事務中的作用。1992年開始的突厥語國家首腦會議在2021年演化為突厥國家聯盟。此外,自豪於“單一民族”身份的日本、韓國、丹麥、波蘭等也透過不同措施強化文化身份。
凡此種種,展示出一幅文明內卷(文明還原)的全球畫卷。
4、文明競合的行為體分為不同方陣。
全球文明體依據人口與影響力的大小,大致分為三個方陣:第一方陣為新教-天主教文明(簡稱“新天文明”,約等於西方文明)、中華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蘭教遜尼派文明,人口在10億以上;第二方陣為東正教文明(俄羅斯為代表)、大和文明(神道教-儒家混合文明,日本為代表)、伊斯蘭教什葉派文明(波斯-什葉派混合文明,伊朗為代表)、天主教-非洲(原始宗教)-印第安混合文明(巴西為代表),可能還包括基督教-伊斯蘭教-非洲原始宗教混合文明(奈及利亞為代表),儒家-基督教混合文明(或稱高麗文明)人口在0.8~5億;其他文明構成第三方陣。
遜尼派文明缺乏公認的核心國家,可能進一步分化為一些亞文明:阿拉伯文明(埃及與沙特為代表,4.5億人口)、馬來文明(印尼與馬來西亞為代表,2.9億人口)、孟加拉文明(孟加拉國與印度西孟加拉邦,2.6億人口)、突厥文明(土耳其為代表,6國1.5億人口)、旁遮普文明(巴基斯坦旁遮普語地區、印度旁遮普邦與哈里亞納邦,1.4億人口)等。這些次級文明的人口在1~5億之間,它們以宗教、語言、血緣、歷史記憶等為紐帶,日益抱團,從而成為第二方陣的事實成員。
5、“新西方主義”與“新東方主義”可能構成不對稱競爭,包括在安全領域與非安全領域。
“新西方主義”以新教-天主教國家為主要成員,它們深受基督教價值觀影響,偏好構建同盟。在難以結盟的情況下,轉而搭建不同領域與議題的排他性俱樂部。
安全領域,美國將以小多邊為主構建安全同盟,類似澳庫斯(AUKUS)這樣的安全機制還會出現。美日同盟、美韓同盟、美澳同盟、美菲同盟這樣的雙邊同盟也會繼續強化。多邊領域,北約內的跨大西洋協調依然存在,但有可能分化:英國、波蘭、丹麥、立陶宛、加拿大等構成“緊密層”,土耳其等構成疏遠層,以法國為代表主張發展歐洲獨立防務力量的國家則構成“中間層”。隨著歐盟及其主要成員國陸續推出印太政策檔案,“印太再平衡”正在演化為“印太歐再平衡”,但介入國家數量的增多、各方希望納入的內容增加,機制化程度將下降。美日印澳四方機制很難轉化為正式的軍事同盟。
非安全領域,如經濟、技術、文化方面,美國也傾向於聯合非西方國家構建排他性的俱樂部,以限制對手、強化自身。但是,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美國的盟國與密切夥伴國將採取“區別應對”方略,安全上呼應美國但有上限,經濟上保持自主但有下限。以德國為例,安全上,內心贊成法國發展獨立防務力量的主張,但不會如法國般行事;經濟上不會放棄與中國的經貿往來,但在高科技領域將限制與中國的合作。
“新東方主義”以中國、俄羅斯為主要協調者,還包括不受美西方待見的國家如伊朗、土耳其、匈牙利、委內瑞拉、敘利亞、朝鮮、柬埔寨等。它們不大可能結盟,但會在不同議題上形成比較緊密的夥伴俱樂部,以便衝破新西方俱樂部的各種限制與打壓,為自己的生存與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國應該有什麼樣的外交方略?這需要另文論述。
(感謝肖河、鄧仕超、張榕、薛江等先生對本文初稿的批評意見與修改建議)
“文明競合”是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薛力研究員的專欄。在“各個文明趨向內卷,不同文明又競爭又合作”的時代,本專欄將以此為基調,探討“國際戰略”與“中國外交”兩個方面的不同話題。
責任編輯:朱鄭勇 圖片編輯:蔣立冬
校對:張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