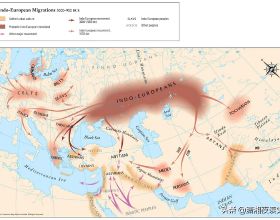佛朗哥1939年成為西班牙元首的前後,由他發起的內戰與迫害運動,致使十餘萬西班牙人失去性命。死者的屍體曾被隨意丟棄,形成多個亂墳場。隨後的近40年,他的獨裁統治將這段歷史塵封。佛朗哥政權1975年倒臺之後,西班牙步入民主社會,但是他的陰魂不散,所犯的罪行一直沒被清算。2007年,否定佛朗哥政權合法性的《歷史記憶法》在西班牙出爐,不過很快便成為一紙空文。《平行母親》中的臺詞“《歷史記憶法》,零歐元”,說出它在西班牙的毫無價值。
圍繞國家是否應該出面組織挖掘受害者的遺骸重新禮葬,西班牙近些年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受害者親屬自然希望親人的亡魂能夠得到告慰,不過右翼保守勢力極力反對,認為國家應該著眼於未來發展,不能不斷地揭舊傷疤。
雅妮絲與安娜是這兩種聲音的代表。雅妮絲出生成長的家鄉,便有包括她的曾外祖父在內的許多歷史受害者,她心心念念要為他們討個說法。安娜的父親是名標準的右翼人士,她受父親影響形成虛無的歷史感,認定回首往事對於當下並無益處。
立場的分歧也由她們的年齡與身份決定。雅妮絲人近中年,是位知名攝影師,她的能力與閱歷,讓她既能用相機拍好時尚風景與時下人物,又會用眼睛凝視歷史的深淵。安娜年紀相對較輕,需要依靠已經離婚的父母生活,但又與他們關係緊張,人生觀與價值觀尚未形成,受著父母以及社會規則的左右——她被幾個男孩強暴懷孕後又被覺得丟臉的父親趕出家門,想要報警又擔心遭到媒體圍攻等,說明西班牙的社會氛圍正在日趨保守,佛朗哥的幽靈彷彿正躲在暗處竊笑。
不過與現實層面自大蠻橫的保守勢力相比,安娜的畏手畏腳不僅屬於小兒科,亦帶有被迫成分。這是阿莫多瓦的有意設定:他無法改變時代的程序,卻能夠在電影裡,讓保守分子看起來像小綿羊或者紙老虎。
獨立又幹練的雅妮絲身上,同樣寄託著阿莫多瓦“改變現實”的理想。
阿莫多瓦過往作品裡的不少女性,比如《崩潰邊緣的女人》中的演員佩帕、《我的秘密之花》中的作家裡奧等,本質上都是法國藝術大師讓·科克託1930年首演的戲劇《人類的聲音》中的女主人公,渴望用一根時斷時續的電話線,挽回決意與她們分手的男人的心。她們儘管事業有成,活著的重心卻是丈夫或情人。他們忽冷忽熱的態度,讓她們的心情在歇斯底里與歡天喜地之間來回搖擺——2020年,在他的電影中多次現身的這部劇作,更被他拍成了同名短片,只不過女人手中的電話,由老式座機換成了新款iPhone。
《人類的聲音》中女人的期待與絕望,某種程度上也是普通個體日常面對大千世界的狀態與心態。按《科克託戲劇選》中文版譯者李玉民的話:一個女人同一部電話的對話,這便是“人聲”,百味的“人生”。阿莫多瓦鏡頭下的大多數人物,性別與情感取向儘管形形色色,身上總有著把電話線當成救命稻草的女人的影子。
《平行母親》中的雅妮絲,完全不需要電話線。開場,阿莫多瓦便告訴觀眾,她是一名掌局者。棚拍現場,她手拿相機給法醫人類學家阿圖羅拍照時,自信又禮貌地指揮他擺造型、做動作。懷上阿圖羅的孩子之後,她更是乾脆地告訴對方,他不用承擔任何責任,她會把孩子生下來獨自撫養。甚至,為了不讓阿圖羅找到自己,她變更了手機號碼。
雅妮絲在政府幾乎不管不問的情況下,悄然整理曾外祖父等死難者的檔案,盼望將來真相大白,也是源於內心足夠強大,具有直面歷史的勇氣與魄力。但是這並不意味她不需要男性。她可以自己養育孩子,可是受孕需要男性的配合。曾外祖父等人的遺骨能被順利挖掘分類整理,也離不開阿圖羅的無私幫助。
當雅妮絲與鄉親們(多數為女性)一起,捧著先輩或丈夫的遺像走向他們的墓地,緘默不語多年的歷史終於開口說話。“歷史永遠不會沉默。不論他們如何詆譭、篡改、偽造,人類的歷史都拒絕保持沉默。”用於片尾字幕,出自拉美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之口的這句話,道出歷史肩負的使命、過去之於當下的意義。以發展的眼光來看,人類需要學會釋懷歷史的不堪與創痛,不過寬恕的前提必須是正視真相、留存記憶,而非將災難從腦海徹底抹除。
“直面歷史”說起來容易做起來艱難。一方面,人類善於遺忘,悲劇總在週而復始。另一方面,我們善與惡並存的體質,會讓個體不經意間成為加害者。雅妮絲早就知道她和安娜抱錯了孩子,想過要讓安娜明曉一切,畢竟兩人在同一屋簷下生活了許久,關係也不只是普通朋友。然而,考慮到自己的親生女兒意外猝死的事實,她選擇了隱瞞真相,對安娜造成極大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