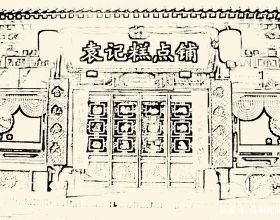村中的老宅
北京有條大石河,流經房山區,進入涿州市後改稱琉璃河。大石河北岸有個五代十國時期的練兵場,當時的幽州節度使劉仁恭屯兵大安山,經常在這裡操練兵馬,此地形成的一個村莊,就起名“常操村”,意思是經常操練。後來有人換了一個同音字,並漸漸約定俗成,於是有了現在的名字“長操村”。而那個寬闊的練兵場,一半演變成了村落,一半成了村邊的莊稼地。現在的長操村隸屬於房山區佛子莊鄉,群山環抱,108國道穿村而過。
通往村南練兵場的衚衕
村舍新舊雜陳
我們沿著一條狹長的衚衕由村北往村南走,去尋找一片開闊的莊稼地,即當年劉仁恭練兵場的南半部。沿途的村舍新舊雜陳,青石板屋頂的老屋大都廢棄,屋前盡是乾枯的荒草和缺胳膊少腿的舊傢俱。在一座門窗殘缺不全的老屋前,一隻髒兮兮的野貓從屋裡躥出來,機警地與我們對峙一陣後,轉身躥上旁邊的牆頭,又從牆頭躥上屋頂。此時,屋頂的另一邊剛好有一隻鴿子在散步。鴿子看到野貓後,停下腳步,腦袋一點一點地伸縮著,彷彿在測算危險係數。而那隻野貓憑藉幾株枯草的掩護,小心翼翼地匍匐於青石板,像是塞倫蓋蒂草原上緊緊盯住獵物的獅子。當野貓試圖靠近鴿子時,鴿子倏地飛走了。
新房的房頂,鐵板取代了青石板,加上刷了塗料的牆壁,看上去有如簡易工棚。在我的潛意識裡,露著磚石的牆壁,石板或茅草的屋頂,意味著安居。也許貧寒,但落地生根。而這種簡易工棚,似乎隨時準備拔寨走人。大石河一帶並非地震高發區,所以這種工棚似的建築物不是用來抗震的。那麼,為何將自家宅院搭建成臨時宿舍模樣呢?也許鐵屋頂結實,也許鐵屋頂搭建速度快,但美感消失了。
在另一條小街上,我看到一座更有趣的院落。這座院落的院牆以大大小小的石塊壘成,大約一米多高,已經破舊,而鑲嵌在院牆中的門樓卻有兩米多高,鮮豔奪目,尤其是那兩扇暗紅色的金屬大門,散發出一種豪華的光澤和富貴氣息。因為院門與院牆的反差太大,我不由得想到一個成語——鶴立雞群。那情形,彷彿守衛院落的任務責無旁貸地落在了高高的門樓上,而低矮的院牆形同虛設,不需要任何武功即可輕而易舉地翻越。
站在院牆邊,院內的一切盡收眼底。幾間坐北朝南的平房,牆面上貼著已經發暗的白瓷磚,掛在門上的棉門簾和門簾兩側的春聯均已褪色。屋前有一片黃土裸露的平地,像是種過莊稼或蔬菜,已經收割過了,但收割得不夠徹底,依然有秸稈殘留,間或有些正在腐爛的枯葉。房屋與平地之間是一截兒高不過膝的磚牆,上面搭著墩布,擺著幾穗幹玉米和幾個爛柿子,牆裡牆外可見鋁盆、鍋蓋、鹹菜缸、塑膠桶、舊衣物、板凳腿、生鏽的鐵棍、油漆斑駁的木板等雜物。
院門的門楣上有五個大字——家和萬事興。“家和”與否我不知道,因為已經人去屋空。至於“萬事興”,我覺得對這座院子的主人來說,或許是一張空頭支票。也許這是一座廢棄的院落,早已無人居住,所以顯得蕪雜。那麼,為何偏有一個氣派的門樓呢?因為門面要緊。如果真是這樣,院落的主人便是一個要面子的人,即使將院子捨棄,院門也要體面地關上。
我們在村子裡遊走時,類似的情形又看到幾處。便想,也許堅固的門樓只是一種象徵,因為這裡留有軍事屬性的烙印。一千多年前,在北邊不遠處的大安山,劉仁恭修築的城堡很堅固,而他在這裡操練兵馬,兵強馬壯又是另一種堅固。
房良聯合縣政府遺址 本版圖片均為嶽強攝影
亂世魔王劉仁恭
作為幽州節度使的劉仁恭,是當時北京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節度使在唐朝初設時,本來是一種武官職位,負責掌管地方軍事,防範和抵禦外敵入侵,並不涉及地方政務。朝廷委任節度使時,賜以旌節,那是當時的一種全權印信,憑此印信可以全權排程兵馬,故稱節度使。但到了五代十國亂世,節度使越俎代庖,集軍政大權於一身,變成了地方軍閥,或者說,簡直成了土皇帝。在如此盛大的權勢之下,如果私德存在瑕疵,必然淪落為驕奢淫逸之徒,譬如劉仁恭。
荒淫無度的劉仁恭在大安山大興土木,宮殿富麗堂皇,後宮美女如雲。與此同時,他尋仙問藥,以求長生不老。據《新五代史》記載:劉仁恭“驕於富貴。築宮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女充其中。又與道士煉丹藥,冀可不死。令燕人用墐土為錢,悉斂銅錢,鑾山而藏之,已而殺其工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處。”因為錢財耗費巨大,劉仁恭強令百姓交出銅錢,將其藏於山中。
劉仁恭放浪形骸,但有一件事從不含糊,那就是操練兵馬。當時正值五代十國亂世,從公元907年到960年,在短短53年的時間裡,先後有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個朝代更迭,每一個短命的王朝均在血泊中來去匆匆,加上地方政權的割據,大大小小的戰事幾乎每天都會發生。有兵就是草頭王,劉仁恭深諳此道,所以長操村這個群山環繞的開闊地帶經常有他的兵馬大規模操練。
對劉仁恭其人,有人說豪爽,有人說奸詐。除此之外,他還善於忽悠。他在幽燕(今河北、北京一帶)徵兵時,很快徵集了20萬人,而且是自備軍糧。那些士兵年齡最小的15歲,最大的70歲。人人都說劉仁恭“精”,這個字眼有褒有貶,說明劉仁恭頭腦靈活,懂得籠絡人心。劉仁恭是怎樣為那些士兵畫餅的,畫了多大的一張餅,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的目的達到了。
劉仁恭不僅善於忽悠,還善於見風使舵。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在太原稱霸時,他依附李克用。李克用賞賜他土地與豪宅,並讓他擔任鎮守壽陽的將軍,待其甚厚,為他日後的崛起奠定了基礎。但劉仁恭不久便與李克用反目成仇,轉而投奔李克用的死敵、汴州節度使朱溫。如此反覆無常,私德著實不堪。
然而,劉仁恭不乏軍事才能,最突出的戰績是以挖地道的方式攻城略地。公元885年,劉仁恭隨軍攻打易州。作為河北門戶的易州城牆堅固,並有重兵把守。在久攻不下、軍心渙散、主帥一籌莫展的情況下,劉仁恭心生妙計,他率領一支隊伍,將地道挖到了易州城內,從而裡應外合,一舉破城。由於擅長地道戰,劉仁恭得了個“劉窟頭”的綽號。有關這個綽號的記載,可見《新五代史·雜傳一·劉守光》:“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能穴地為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
與劉仁恭相比,劣跡斑斑的劉守光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與庶母通姦,囚禁父親,殺害兄長及侄子,惡行遠超其父。而且,一旦得勢,便迅速膨脹,以為佔據兩千裡燕地即可稱帝。對他欲稱帝之舉,屬臣孫鶴極力諫阻,卻被殘忍地殺害。乾化元年(公元911年)八月,劉守光自稱大燕皇帝,改元應天。不料,第二年李存勖就派兵打了過來,劉守光與其父劉仁恭最終被擒。李存勖以劉仁恭之血祭奠先王李克用,然後將劉仁恭斬首,不可一世的劉守光也隨即被斬。
民諺曰,上樑不正下樑歪。就自律和教子而言,劉仁恭無疑是徹底的失敗者。但在軍事上,他還是有才能的。地道戰以外,將大石河畔的那片寬闊地帶開闢為練兵場就很有軍事眼光。那裡背靠巍峨的群山,山下是清澈的河水,場地開闊而平坦,的確是一個操練兵馬的好地方。
房良聯合縣政府遺址紀念館
練兵場成了莊稼地
劉仁恭當年的練兵場在村南山環水繞的一片空地,也就是那條狹長鬍同的盡頭。那片空地最初為橢圓形,面積比現在大得多。後來,有人在北面造屋定居,並不斷有人效法,漸漸形成一片村舍。現在,一條新修的柏油路將村舍與空地隔開,那片空地便成了半圓形。即便如此,面積依然有上百畝。“不能太小,要不然沒法兒跑馬。”一位村民對我說。是的,劉仁恭操練的不僅有步兵,還有騎兵,兵強馬壯是他稱霸一方的底氣。
而今,這裡是一片寂靜的莊稼地,種植玉米和紅薯。收割後的玉米地依然殘存著大片高約一尺的秸稈,被割斷或砍斷處留下鋒利向上的刀口,彷彿根根直立的槍刺。寬闊的莊稼地三面環山,北面是村舍和街道。山下是河,嘩嘩的流水聲老遠即可聽到。“這山叫什麼名字呀?”我問一位正在田間施肥的老人。他一隻手扶著鐵鍁把兒,另一隻手指著不同的方向,鄭重其事地說:“東邊的叫東山,南邊的叫南山,西邊的叫西山。”我又問:“那山下的河呢?”他說:“東邊的叫東河,南邊的叫南河,西邊的叫西河。”好隨意,地圖上或許不會有這樣的名稱。但老人說,我們祖祖輩輩都這麼叫,沒叫過別的名字。至於河水的來源與去向,他說,水是從山上流下來的,最後流進大石河。我在村裡遊走時,又與別的村民說到練兵場旁邊的山與河,他們的說法與這位老人如出一轍。
除了練兵場,長操村還有一個看點。抗戰時期,宋時輪、鄧華支隊曾在這裡建立京西南第一個縣級抗日民主政權——房良聯合縣抗日民主政府。但房良聯合縣政府遺址紀念館落了鎖,房良聯合縣政府遺址的二進院落成了一戶人家居住的庭院。從那家庭院走出來,我想,當年的抗日武裝或許也在村南的那片空地操練過兵馬。
來源 北京晚報
作者 嶽強
流程編輯 吳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