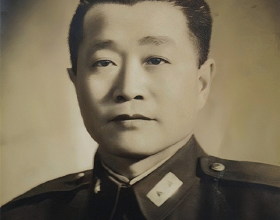文|星袁蒙沂
老家在偏僻山村,冬天,那裡時常下雪。
於我而言,雪似乎是戀家的。雪慣常光顧的地方,就是老家那不大的山村。那裡的冬天,一場大雪過後,藍天之下,清一色的白。就連四周的鳥鳴,都來自曠遠的雪色中,嘰嘰喳喳,嘰嘰喳喳,聲音來處,盡是茫茫。
那天,天陰著,因為沒陽光,溫度降了一點兒。同事拿來一些多肉植物,我把其栽進花盆,移到窗臺邊朝陽的木桌上。氣象預報顯示,夜間有雨夾雪。這些多肉植物若不及時栽上,一旦下雪,地上結了冰,去室外取土就困難了。
栽完多肉植物,我還在想,晚上真會下雪嗎?我將室外那些怕凍怕淋的物品全部移到室內,收拾妥當,逗著孩子看電視。晚上11點鐘,外面開始稀稀拉拉落冰粒,小如唾沫星兒。用手接了十幾秒,只發現一粒落到手心,倏地融化了。
對於雪,我是期待的。而對當天晚上下雪,我卻不抱多大希望。預報有雨夾雪,就算真下雪,估計也不大。說不定有雨水一攪和,地上甚至覓不到雪的蹤影。如果是雨,這個季節來一場,於乾渴的植物而言,自然是好事。對於城鎮街道,尤其是有泥土的地方,雨水和泥土一摻和,到處髒且坑窪,天又寒冷,心中不免會陡增怯意。
大雪則不同。一場大雪覆蓋到地上,厚厚軟軟的。不管在鄉村還是在城市,到處白茫茫一片,視覺上的衝擊和享受,是一場雨所不能比的。雪也會融化成水,水也會和泥土混成一片泥濘,甚至還會迅速凝結成冰。但有雪的存在,那種積壓在各處的白才是主題,那種蓬鬆的白,那種綿軟的白,那種厚實輕巧的白,能夠成就許多故事和感觸。植物因它而多了一層綿軟,腳步因它而變得有形,寒冷因它而有了情調。特別是那些第一次見到雪的孩童,在雪地上一邊聽大人講解著,一邊蹦啊跳啊,多暖心!冬天的風,冬天的冷,冬天的光禿,冬天的暗淡,因為一場雪而煥然一新!一場雪,美麗了整個世界。
次日醒來,雪花依然碎碎地飄著。去單位的路上,到處是水,偶爾能見到一小片略白的路面。老家那邊的山村是什麼情況呢?還沒等我問,村裡的一個哥們兒發來語音,稱老家下了一場大雪,地上的雪已經沒過腳背了。在我的要求下,他接通了影片。老家那邊,大片大片的雪花正在下,院落裡、周邊的山野上,到處被積雪遮蔽。之後,那哥們兒又發來十幾張照片。雪,確實夠大!踩上去咯吱咯吱的聲音,似乎正在耳畔響起。
老家所在的山村與我工作的這個地方同屬一個小鎮,之間的距離只有三十多里。然而,與我一樣,雪似乎也是戀家的。每年冬天,老家那邊的雪都比小鎮上的雪大,下雪的次數也總比小鎮上多些。
老家那邊的雪,看上去也遠比小鎮上白。這種白,絕不是心理上的,而是事實。老家那邊,街巷、道路上行人和車輛少,路是沿著坡嶺修成的,積雪一旦融化成水,順著坡勢流淌,路面上很少見到這兒一汪那兒一汪的泥水。老家那邊的街巷和道路,只是偌大山嶺中的一根根若有若無的細線,就算本色盡顯,也只是白茫茫世界裡的一絲絲點綴,白依然是主旋律。老家那邊的房舍頂,多是斜面構造,院牆也多是石塊壘成,凹凸不平,頂部和側面都能存住雪花。有了積雪覆蓋,從各個方向看過去,都是厚厚的雪,白色佔據了大多數位置。老家那邊的田地、樹木,冬天很少有人去管理,有了積雪,除了一點點融化、厚度一層層變薄之外,很少沾染人類活動的印跡,白得徹底。
雪,似乎是戀著老家那邊的。這些年,經常是同一種呈現。鎮上沒下雪,老家那邊飄了場小雪;鎮上小雪或雨夾雪,老家那邊鋪天蓋地來了場大雪;鎮上好不容易有了場大雪,老家那邊直接就是暴雪封山。
生活在北方的人,大多數年份,冬天多少都能見到一些雪。或許早晨還是豔陽高照,沒丁點兒下雪的意思,中午天色一變,雪就急匆匆地飄起來了。
有些時候,人們也不希望下雪。比如新年臨近,那些亟待回家的人,萬一遇上一場大雪,行程可能就得延誤。但生活在農村的人們,往往又在盼雪。一場大雪,山川明亮,萬物披白,不但可以大飽眼福,還能潤澤萬物。只不過,雪花的來去,總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轉移。它就是這樣,想來的時候來,想去的時候去。
於我而言,小鎮上的樓房和院落是家,那處離此不遠的山村老家更是家。於雪而言,大地是家,那處離此不遠的山腳村落也是家。我戀著山村老家,雪似乎也戀著那裡。當我頻頻回去時,雪也頻頻光顧。那裡,有太多鮮活的、飽滿的、豐富的雪的印跡,似是在一遍遍重複著,其實是在一次次更新著。
總覺得,戀家的除了我,還有那些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