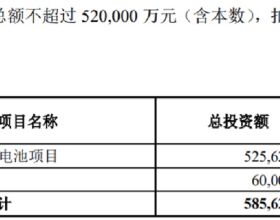辛丑年隆冬的一天,我利用出差閒暇,從北京站乘火車回到闊別三十三年的小米莊。三十五年前,我應徵入伍,來到位於天津薊縣邦均鎮小米莊村的坦克一師二團三營九連,當了一名坦克兵。我們的營房坐落於盤山腳下,只要從屋裡來到屋外,抬頭便可見到巍峨高大、猶如一塊大屏障的高山。從老兵那兒我們瞭解到,盤山是燕山餘脈,有著京東第一山之美譽。老兵還講,盤山頂上座落著一座寺廟,《水滸》裡面的公孫勝曾經在這座廟裡修行過。出於好奇,新兵集訓完畢下連隊後不久,我就和幾個湖北兵一塊登了一次盤山,那次登山的經歷頗為驚險,今天回憶起來,依然心有餘悸,並且夾帶著些許興奮。我們當兵那會兒,文革剛結束,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還在醞釀中,盤山的旅遊開發還沒開始,我們走的都是崎嶇不平、陡峭危險的山路,我這個愣頭青爬得最快,第一個到了山頂,中途跌倒好幾次,所幸,只有十八歲的我,身手矯健,沒摔壞身子。後來究竟又爬了幾趟盤山,我現在已經記不清了,存在我記憶深處的大多是第一次爬盤山時留下的。
四十三年後,我再次來薊州,目的地有兩個,一個是到我們三營的營房,二是盤山。還好,我的目的基本達到,但去的兩個地方卻和我想象得相差很遠。生怕景區關門,我沒有先去找營房舊址,兩點剛過就匆忙趕到盤山。眼前的盤山再也不像四十三年前那樣荒蕪,入口處的山門造得十分氣派,右邊是現代化的賓館,左邊稍遠處是錯落有致的民宿。大概是冬季的緣故,來盤山遊玩的人不多,考慮到時間緊,上山時我花六十塊錢買了張索道票,可以坐六個人的包廂裡就我一個人,短短十分鐘不到的乘車時間,我眼睛不停地透過窗玻璃嚮往張望,尋找著四十多年前的足跡,久遠的時間,哪能輕易辨別得出?此時正值數九寒冬,山體上的植物大部分都枯萎了,只有一兩棵小松樹依然是綠的,給人以幾分生機,再看那形狀各異、大小不一的山頭,雖然灰不溜秋的,可一個個卻都是那麼不卑不亢地躺在那兒,忽然,我的記憶裡跳出四十多年前爬盤山時看到的景象,當時,它們就是這樣躺在那兒,一點變化沒有!畢竟找回一點四十多年前爬盤山時的感覺,我心裡得到些許滿足。下了纜車,我沿著導覽指示牌邊看風景邊向山下走去。說是看風景,其實,北方的山在冬季實在沒什麼好看的,除了一座座寺廟,一個個石塔,一個個石佛,就是如同剛才在攬車上看到的默默躺著的石頭了,偶爾也能看到幾塊碩大無比的巨石,彷彿在為人們展示著大自然造物的神奇功夫。
快要到山門時,我看到一塊豎著的大石頭上刻著中國佛教協會前主席、著名佛教居士赴樸初老先生手書的“東五臺山”四個紅色大字,心頭不由一愣。五臺山是全國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位列北方佛教名山之首,在我國西北的陝西、山西兩省之間,盤山位於京東,其佛教名山的地位竟然可以同五臺山比美,這究竟是本來如此,還是趙樸初老先生老糊塗了,被別人矇蔽,稀裡糊塗寫下“東五臺山”這四個字,我不得而知。帶著這個疑惑,我向入勝處走去,沿途又看到幾塊大石頭上寫著康熙、乾隆到盤山來過多少次以及讚美盤山的語句,最有廣告效果的當數“早知有盤山,何必下江南”這十個字,這二位清朝名帝一生中寫過數不清的詩賦,這句話究竟是不是大清名帝所說又有幾人能搞不清楚?
下山後,我一直在思考,四十多年前,盤山就是一座荒山,除了幾個寺廟幾座古塔之外,別的什麼都沒有,僅僅四十年,薊縣人就用他們的雙手和大腦中的智慧,根據一些歷史傳說將它裝點成一座名山,變為津京兩地人們旅遊觀光以及夏日避暑的絕佳之處,可見,人們的創造力多麼非凡!即便有些東西是想象和虛構的,有些建築是當代人修造的,只要它們能愉悅人,能讓遊人喜歡也未嘗不可,因為,它們沒有傷害到任何人,一切都是讓人生活得更加美好。
出了大門,我透過打車軟體要了輛計程車,準備往城裡趕,看天色還早,我對只有三十多歲年紀的司機說,我要去小米莊看看四十多年未見的老營房。小夥子聽說我以前在這兒當過兵,今天是四十多年後的故地重遊,有些感動,不停地為我介紹薊州這些年的變化。來訪故前,我就聽我們連當時的文書、湖北應城兵陳春平說,坦克一師建制早就不存在了,現在成為朱日和基地的保障部隊,營房幾年前就拆光變成一塊空地。由於有了足夠的思想準備,我知道下面的尋舊將會十分困難,還好,這個司機是當地人,又是跑出租的,對這兒的風土人情比較熟悉,並且,我們坦克一師在薊縣又相當的出名,尋訪進行得挺順利。他首先幫我在小米莊村部附近的一個小超市問了三營營房舊址,女老闆一聽我是老兵尋舊的,熱情地為我們介紹行車路線。司機按照她的指引,開了不到十分鐘就將車子開到一處正在平整土地的建築工地,一箇中年男人正坐在牆頭上,聽說我是尋舊的老兵,連忙說,這兒就是你們的營房,全拆了。我問,是三營的嗎?他回答說是,前一陣子還來了幾個老兵,也像你這樣尋舊來的。我進了院子,看到牆院內是一大塊剛剛平整好的空地,連一塊磚一塊瓦都沒見到,我來不及傷感,竭力尋找周邊能和老營房沾上邊的東西,卻怎麼也找不著,在左前方發現了一個小山包,似乎像又似乎不像我們營房東邊的,這時,耳邊傳來說話聲,好似對我說的:“這是一營,不是三營,三營在那頭,已經蓋成高爾夫俱樂部了。”我忙調過頭去,見到說話的是一位老年男子,大約有七十來歲,瘦挑身材,長臉,長相上看,不像是農民,他推著輛腳踏車,車上放著一些好像用來做買賣的商品。我忙問他,你怎麼知道這些情況的。他說我和三營三個連的連長都熟,並報出我們連長常會林的名字。我聽了甚為激動,隨即和他攀談起來。因時間有限,兩人簡單聊了幾句以後,我又坐上計程車,急忙向原先我們三營老營房,如今的高爾夫俱樂部趕去。按這位老鄉的說法,老營房殘跡還有,可到了以後,我左找右找就是找不到,只覺得那幾座山頭都挺像的,當年我們的坦克庫似乎就建在那兒。一想到坦克庫,腦海中迅速冒出我後半夜站崗時打盹的情形,那會兒我才十八歲,夜裡兩三點正在覺頭上,一個人手持著步槍,夜深人靜,什麼情況都沒有,站在崗亭裡,不知不覺雙眼皮就往一起合,說是睡覺,其實還不能算,只要一有動靜,尤其是查崗的來了,一點點腳步聲都能聽到,這個時候,睏意就會立馬消失。想到這些,看看眼前已經面目全非的老營房,失落感重重地湧上心頭……
回薊州城途中,我和司機談著剛才沒找到老營房痕跡的感受,他一邊開車一邊附和我幾句,對我那句“一生能有幾個四十五年”的話尤其認可。到了賓館,我久久地沉浸在老營房已無蹤跡的惆悵中。直到入睡前,我漸漸想開了。白天的訪舊之路不能說失敗,也說不上成功,人生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過去的就該讓它過去,糾纏某種情感並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抬頭向前看,做讓自己快樂的事才是最正確的選擇,哪怕到了人生的盡頭也都應該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