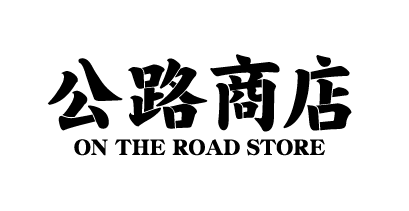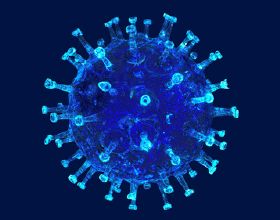轉場有很多種可能的原因,比如你10點得先給學了一個月打碟的朋友捧場,忍受一個小時內的五次跑馬,才好意思去真想去的地兒;
比如這兒的人氣場不對,沒人在跳舞,男男女女不是在左右腳間換重心就是在用舌頭擊劍;再比如你和閨蜜出來,正好遇上你前炮友或者你們的共同炮友。
不過轉場只有一個終極原因:“這兒不好玩”。甚至以上原因都可以歸結成“這兒不好玩”。
從四月起,我在成都生活了半年,感覺每個週五或週六的晚上不換三四個地方,就相當於沒出來玩。畢竟圈子小,就分散在直徑撐死兩米的一個圓裡。
到最後發現,方糖就是科華北路的麥當勞,不一定特好,卻也不會錯。
回北京後的平安夜,我嫌wigwam的音樂就像一首長達一小時的歌點綴各種效果,想去McLab瞅瞅,地圖一查,距離八公里,兩眼一黑。在北京轉場,你需要對追逐“好玩”有極大的決心。
那個平安夜,後來同事們圍著我跳了半小時舞后說要去school,我沒原則地跟著走了。凌晨四點的school只剩下搖滾小逼,看起來混得不太好的樣子;還有個老外,納悶自己18cm怎麼呲不到妞。
十分鐘後打烊了,我一個北方人裹著羽絨服在風裡發抖,而南方同事們還在用不成句子的英語開導老外。我那天決定再也不跟這幫der玩兒了。轉場後是不見得更好玩兒。
但我認為,人始終該有用腳投票的權利。
出於可行性考慮,本文的“轉場”只涉及可供跳舞的電子俱樂部。看live的地方不算,說話不用貼著耳朵的酒吧不算。
我知道有人會提PH,但別鬧了好嗎?因此涉及場所包括:Baby Boom Bar、藥Yao Club、Dada、Aurora、Umu、Zhaodai、Clash撞、Wigwam、Solo以及Mclab。
雖說研究不包括live場所,但還沒走到Yao club就遇到塗鴉人老明和朋友們去看另一個朋友的樂隊演出,我還是跟著折進了school。
剛進去就見到了去年在zhaodai喝多強吻的小哥,段子竟是我自己。我們陷入純為化解尷尬的聊天,我給他講了一晚上串10個club的計劃,他想也沒想就定論:“你轉不完。”
“我算過,每個地方玩半小時,總計五小時,從11點開始,可行。”“你算路上時間了嗎?”之後一整晚,我都被這句話的陰影籠罩。
到了Dada的檢票口,哥們兒看見我腕子上倆手環,說:“喲,有了啊。”我同樣回了句廢話:“可不,去了倆點兒了。” “是都不開心嗎?” “嗨,報銷的。”
答非所問,權當敷衍,畢竟在門口解釋自己的研究課題會顯得我像神經病。但這對話令我意識到自己的快進快出會吸引他人的注意,以致該離開Dada的時候我把藉口都想好了:去地面接個朋友。但檢票哥們兒和bouncer再沒多問,可能他們對於我這種不安分的來客早見怪不怪,也可能純粹是我閃人夠快。
Bong油說北京的街上不留人,“轉場就變成了唯有出發地和目的地,你的行程都被降維成點到點”。的確,成都不一樣,路上也能玩兒:有紋身學徒為了創收賣漢堡,大鐵板上牛肉煎得滋滋響;有大妞騎來電瓶車,擺上幾個馬紮就給你調雞尾酒,瓜子還免費。我反倒覺得,北京的“路上時間”也有它的趣味——你還有什麼機會在半夜端詳北京呢?
這晚1公里之內的路程我都騎共享單車,從Dada騎去Umu的路上,我頭回發現日壇的使館半夜也有人站崗。我想武警一定很悶,又不能玩手機。我衝他們揮手問候,然後意識到,他們是沒法衝我揮手的。到了Umu,我打破了自己設下的“每個地方玩至少半小時”的規矩,但我有理由啊。
一進去裡面在放《說愛你》,我認為這是一種調動聽眾DNA的小聰明,道理類似某位銳舞常客友人談Howie Lee說的:“再亞的人聽見《好漢歌》也得大合唱。”我能理解,但我聽不下去。
從Aurora打車去Zhaodai,計程車師傅問我:“怎麼才這個點兒就不玩兒了?” 我答:“您怎麼知道我不是去接著玩兒?” 師傅說他就知道工體這一帶是玩兒的地兒,“我們年輕時候都在這兒跟人霹舞”,我不確定是不是這個pī字。這並非一個“上一代有多騷”的老套故事。
師傅接著說,他早年更鐘愛的娛樂活動是在馬連店夜市跟人“霹茶”,我仍然不確定是不是這個pī字。所謂霹茶就是品茶後猜出是哪種茶葉、哪年產。我問猜錯了會怎麼樣。“猜錯了?幫人數錢!我那時候正確率基本能達到……”他好像真地計算了一下,“百分之八十八。”
我問那您是不是得嘗過的茶葉多,師傅說不止,還得注意不吃辛辣刺激,保持味覺清明。接著師傅說,想玩兒高檔的,得去民族園。我說那一帶我玩不起。師傅說:“你得先玩兒,就玩兒得起了。” 過會兒他又自己加註解:“你的圈子就不一樣了。”我下車除了慣例叮囑師傅注意安全,一併感謝了他的教誨。
我搬出北京那陣子,北京的club關得沒剩幾個,Zhaodai之於夜生活也相當於麥當勞。但做研究這晚的Zhaodai沒給我熟悉的安全感。今晚的Zhaodai就像我開頭形容的,男女都在兩腳間轉換重心,只是沒人用舌頭擊劍。
我不敢放開了跳舞,生怕我投入的樣子引來了想一起玩的人。我腦裡還盤旋著被強吻的小哥那句“你玩兒不完”的詛咒,今夜我只是招待所的過客,看似埋頭刷Tinder實則只是想避免和人對視,偏偏這晚格納斯大廈地下的訊號格外好。我抓起扔在音響上的羽絨服披上,剛剛好像有抓我手的韓國小兄弟問我要走了嗎。
他用韓語叫我留下來一起玩,我用韓語說不行我在工作,他說什麼工作,我想了下,問:“我說中文行嗎?”上樓梯感覺自己像在逃,儘管後面沒人在追。
一位剛入場的新疆長相的大哥迎面來了句:“走了,大寶貝兒?” 我問他是哪位, 他答:“我是你新認識的朋友。”後來Bong油聽我講這段經歷,說這屬於海選型搭訕選手,我倒不覺得。這種和擦身而過的人蜻蜓點水地接觸,沒有斬不斷、甩不掉,很chill很好。如果沒有他繞過我下樓後那句“你走了我就不開心了”,就更好了。

Zhaodai旁邊日料店的玻璃。好像小時候用數字2畫的鴨子。
黎明越是接近,我越是緊張到胃疼。夾在元旦和過年之間的北京出奇冷清,研究開始前,9點半的鼓樓東大街沒幾個人。
我生怕最後幾個場子提早收檔,轉場變成了朝陽區定向越野。同時,路上的時間比蹦迪更讓我放鬆,當我只和自己在一起,就沉進這城市夜晚的荒涼裡。特別是車開上高架,視野開闊,我感到北京太大了,一個人就像一滴帶顏色的液體被滴進水裡、溶化。有心理學研究表明,人幸福感最強的時候是自我溶解的時候。
到了wigwam和solo,我喘了口氣,終於只剩一站了。然而我沒法溶解在這裡。Wigwam的DJ在放高速Rave,所有人齊刷刷地甩頭。我記得跨年那晚在Zhaodai,大家也很瘋,擠得就像印度火車廂的舞池理當令人生理不適,但我能感覺到大家是自然地開心。
我跳到出汗,旁邊一個姑娘黑長髮飛旋,我踩到她,跟她道歉,她揮舞著手,叫我玩起來玩起來。換歌的檔口,總有人帶頭喊DJ的名字:“Mr.Hoooooooo——”對比起來,眼前甩頭的大夥,似乎開心得很用力,好像帶著給自己的任務來的:必須玩!必須發洩!甚至有些死死攥住狂歡的末尾的意味。
可能是寫稿人的毛病,讓我一定要看出點意義;可能只是音樂我不喜歡;也可能我需要酒精的麻痺,雖然跨年那晚我也沒喝。到了最後一站McLab,這種感覺尤甚。放歌的Hao在猛錘,五點的舞池裡只有五個人,都跳得像要抓住這一夜的末尾。中央的姑娘大露背,袖子和裙襬的黑紗傷感地飄起。
散場打車的時候,她的男伴追著一條野狗喊“高一凡”,我猜那是他們朋友的名字。男孩追狗,姑娘追男孩,黑紗在夜裡飄到我再也看不見。

離開wigwam和solo前要留影,一位捲毛哥們衝入我的鏡頭。
狗。
我很愛玩,愛玩到什麼程度呢?我知道元旦早上家裡要裝修,沒法補覺,不惜在Zhaodai旁開了間錦江之星,也要把這一夜玩好。但做完研究的凌晨六點,我頭一次覺得在家更滿足,與其去那些不屬於我的地方遭遇不屬於我的人,不如在家擼屬於我的貓。
這一晚我不敢和人產生連結。然而潛意識裡我知道,就算我不跳來跳去,在一個點位呆到天亮,也和他們產生不了太多連結。我們會以“一個人來嗎”開場,用“怎麼一個人來呀”“你平常都去哪玩兒”延續。就算進展到“你掃我還是我掃你”,我們始終是兩具空殼,被彼此都不在意的資訊填滿。走出Wigwam那會兒有個明顯喝了點的姐妹兒拉住我,捏著我的丸子頭說我好可愛。
那一瞬我啞了,因為討厭自己張嘴就是套話。最後從McLab打車的當兒,一個高個男孩一樣在等車,他兩步邁到我旁邊,說他本來和哥們兒去了Dada,哥們兒有妞兒了不要他了:“我走的時候倆人兒還跟那兒親呢,我操。”
社恐的我繃緊神經,直到快車來了才解脫。第二天醒來我想到,人家可能沒抱什麼目的,只是也想和陌生人聊上兩句,排遣一夜將近時的枯寂。在這2000萬多人口的城市,我們像一滴有顏色的液體滴進水裡。
有心理學研究表明,自我的溶解是最幸福的。而戒備心、目的性、想比別人更特別……各種東西讓我們保持著自我的形態沒法溶解。
這一晚的打車費總計:29.62+14+25+17+18+23=126.62 不計入從家出發的地鐵票和最後回家的打車錢,也不計入共享單車,因為有騎行卡。
如果想再壓縮成本,可以堅定地等快車,而非像我一樣打了幾回出租。但誰轉場會刻意省那幾塊錢呢?另外,這不能代表你跨年、平安夜這樣的日子轉場的開銷。畢竟你都選擇了湊很有儀式感的熱鬧,該。
本研究重點是轉場需要的交通費而非門票錢,因為你就算在成都、上海轉場,交通費會差不少,門票錢我估計也差不到哪。
但作為參考,這一晚的門票開銷是:60+150+100=310。未計入的場地,有些本身免費入場,有些夜深了也就不要票了。以前看微博上有人問“活著的意義是什麼”。最高讚的回答也是“來都來了”。雖然在北京追逐“好玩”需要極大的主觀能動性,但假如你沒有那麼強的動力轉場,沒必要把自己劈成正反方,讓雙方的辯論耽誤了你享受此地此刻。你大可也默唸一句“來都來了”。
撰文小餅乾 編輯小餅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