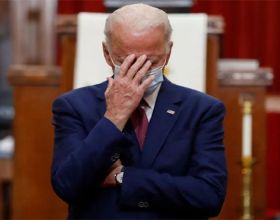我們黨以毛主席為主要代表所進行的這些創造性的理論建設工作,為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理論的基礎。
我們黨建立和展開活動的初期,理論準備是不足的。這是由於:第一,中國資產階級在思想上和理論上很不成熟。
毛主席在《農村調查》的序言中說過:“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可能替我們預備關於社會情況的較完備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歐美日本的資產階級那樣”。
中國資產階級在理論發展上的不足,影響到中國無產階級理論發展的不足。
第二,中國共產黨一誕生,立即投入迅速高漲的實際革命運動,來不及從容地作理論的準備。
當然,決不可以低估建黨前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介紹和研究的巨大成績。
正是由於這種介紹和研究,使中國人民的眼界提高了,中國革命也改變了面貌。但是,這種介紹畢竟是很不充分的,馬恩列的許多重要著作都還沒有翻譯出來,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還缺乏完整的、統一的瞭解。
第三,第一次大革命失敗,黨又立即投入武裝起義,在農村、在偏僻的山溝開闢根據地,進行土地革命戰爭,沒有可能從容地從理論上總結革命經驗和探討革命道路。
但是,革命難道能夠等待理論準備成熟然後才去進行嗎?革命實踐在先。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形勢,迫使我們黨從實踐中開闢了一條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歷史上不曾有過的中國自己的獨特道路——在農村建立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中國革命的理論準備和理論建設,正是要從總結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中,從研究中國革命的條件、特點和規律中,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而求得發展。
當時,正是毛主席從實踐上和理論上代表了這個正確的方向。
然而,一些受教條主義束縛的同志卻不能認識這個正確的方向。
在他們看來,似乎只有在外國,在城市,在書本上,才能有馬克思主義,山溝裡不能有馬克思主義。他們指責所謂“山溝裡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否認理論”的“狹隘經驗論”。
馬克思主義當然不能從山溝裡產生。它是從近代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基礎上批判和改造近代資產階級的理論成果而產生的,是在近代城市中產生的。
從中國來說,它還是在外國產生的。外國傳來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首先也是在城市,在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工人中傳播的。
毛主席同其他許多人一樣,是在城市,在同外國傳來的新思潮相接觸中,瞭解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但是,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形勢,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到農村中、到山溝裡去發展。
因此,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必須同農村中、山溝裡的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在山溝裡研究馬克思主義當然有許多困難。然而,否認農村中、山溝裡的中國革命實踐,拒絕研究中國革命實踐的這些創造性的經驗,只是從書本上和外國決議上去抄襲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和教條,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不能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只能使它遭到挫折。
當毛主席強調實踐、強調調查研究的時候,他所要求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認為理論工作必須遵循這樣的方向,並沒有一般地否認理論、否認書本。
相反,在同實踐相結合的正確方向下,他是重視理論,重視書本的,在山溝裡和戰火中的極端困難條件下,他是盡了可能去學習理論,學習書本,提倡理論的教育和研究的。
在一九二九年的古田會議決議中,毛主席在強調社會調查的同時,強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在這個決議的“黨內教育問題”一節裡,在十項教育材料中,除了列為第七項的“游擊區域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一項外,還有列為第八、九、十項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研究”,“社會經濟科學的研究”,“革命的目前階段和它的前途問題”,以及列為第一、二項的“政治(形勢)分析”,“上級指導的通告的討論”。
在起草古田會議決議的同時,毛主席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說:“惟黨員理論常識太低,須趕急進行教育。除請中央將黨內出版物(布報,《紅旗》,《列寧主義概論》,《俄國革命運動史》等,我們一點都未得到)寄來外,另請購書一批,我們望得書報如飢如渴,務請勿以事小棄置。”他還給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李立三寫了一封信,說:“我知識饑荒到十分,請你時常寄書報給我。”
在反革命“圍剿”中,毛主席想方設法收集馬列著作。《反杜林論》的中譯本就是在一九三二年紅軍打漳州時收集到的。他非常珍惜這些譯本,在長征行軍中都一直帶在身邊,沒有丟失。
關於毛主席在陝北、在延安發憤讀書的情況,有一些很生動感人的記載。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這樣報道過:“毛主席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
斯諾在書裡寫道: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採訪共產黨的歷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於是毛主席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專心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麼都不管了。”斯諾的訪談,是一九三六年十月間的事情。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毛主席給他早年的好友易禮容一封信。信中詢問:“李鶴鳴王會悟夫婦與兄尚有聯絡否?我讀了李之譯著,甚表同情,有便乞為致意。”李鶴鳴就是李達,信中提到的李的譯著現在不能斷定是哪一種。很可能是李達、雷仲堅合譯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
毛主席不僅自己發憤讀書,還組織中央其他同志一起讀書,提倡黨的幹部都來讀書。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一日毛主席、周恩來、博古致電彭(德懷)、劉(曉)、李(富春):“(一)同意富春辦法,組織流動圖書館。(二)明日即開始寄第一次書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轉寄彭劉,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務須按時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後將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毛主席給當時在“外面”從事統一戰線工作的葉劍英、劉鼎去電:“要買一批通俗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哲學書,大約共買十種至十五種左右,要經過選擇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柳湜的《街頭講話》之類),每種買五十部,共價不過一百元至三百無,請劍兄經手選擇,鼎兄經手購買。在十一月初先行選買幾種寄來,作為學校與部隊提高幹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書報。”
毛主席在陝北和延安批閱較多的哲學著作有十幾種,除馬恩列斯的以外,還有蘇聯和中國學者的。
其中李、雷合譯西洛可夫、愛森堡等合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批註文字最多。從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四月,在這本書的第三版上先後用毛筆、黑鉛筆在書眉和空白的地方寫下了近一萬二千字的批註,並從頭至尾作了圈點和勾劃。
其中第三章“辯證法的根本法則”批註文字最多,最長的一條有一千多字。後來,大約在一九四一年,又在這本書的第四版上作了一些批註。批註都用雋秀的行草字型。有對原著的扼要而精闢的概述,簡明的贊同評語,也有對原著觀點的批評、引伸,特別是有許多聯絡中國實際所作的發揮。
李達著的《社會學大綱》,一九三七年五月出版後作者曾寄給毛主席一本,毛主席讀了很高興,認為是一本好書,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教科書,並把它推薦給抗日軍政大學。
他在書上作了很多批註,合計約三千五百字。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毛主席寫“讀書日記”,開頭這樣寫著:“二十年沒有寫過日記了,今天起再來開始,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點學問。看李達的《社會學大綱》,一月十七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辯證法’,從1—385頁。今天開始看第二篇,‘當作科學看的歷史唯物論’,387—416。”以後逐日記了讀書的進度。
三月十六日記:“本書完。”艾思奇著的《思想方法論》(一九三七年一月再版),毛主席也作了批註。一九三七年九月,還寫了十九頁《艾著〈哲學與生活〉摘錄》,總共三千字。
不久後寫信給艾說:“你的《哲學與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書,我讀了得益很多,抄錄了一些,送請一看是否有抄錯的。其中有一個問題略有疑點(不是基本的不同),請你再考慮一下,詳情當面告訴。今日何時有暇,我來看你。”
毛主席充分利用了同江西時期和長征途中比較要好一些的客觀條件,“如飢如渴”地閱讀當時他能得到的理論著作,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
他這種研究的特點,就是聯絡中國革命的實踐,把中國革命曲折發展的歷史經驗教訓提到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線上。
寫作《實踐論》、《矛盾論》,並不是毛主席研究哲學的結束,而是他研究哲學的新的開始。
延安時期是民主革命中我們黨在理論上達到成熟的時期。
如果說,那以前我們黨在理論上準備不足的話,經過延安時期以毛主席為主要代表進行的系統總結中國革命歷史經驗、系統闡明黨的綱領和策略的理論建設工作,經過延安整風,黨為指導中國民主革命達到勝利從容地作好了理論的準備。
延安整風一方面糾正了“中國的主觀主義者在脫離實踐的提倡社會科學理論之重要性”的偏向,一方面也強調了聯絡中國革命實踐學習和研究理論的重要性。
整風學習檔案中關於這方面的許多論述,是大家所熟習的。整風前後,毛主席在延安組織學習哲學,並在新哲學會第一屆年會上指出“中國革命有了許多年,但理論活動仍很落後,這是大缺憾”,強調“如不提高革命理論,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五日,毛主席寫信給當時的中宣部代部長凱豐:“整風完後,中央須設一個大的編譯部,把軍委編譯局併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譯馬恩列斯及蘇聯書籍,如再有力,則翻譯英法德古典書籍。我想亮平在翻譯方面曾有功績,最好還是他主持編譯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願幹否?為全黨著想,與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譯工作,學個唐二藏及魯迅,實是功德無量的。”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毛主席在西北局高幹會上講布林什維克化十二條時提出:我們要注重理論,高階幹部要準備讀書,從《共產黨宣言》起到《季米特洛夫文選》止,選三、四十本。我們有這樣豐富的經驗,有這樣長的鬥爭歷史,要能讀一、二十本到三、四十本馬恩列斯的書,就把我們的黨大大的武裝起來了。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又寫信給凱豐:“惟譯、著方面(譯是馬列,著是歷史),須集幾個人來幹,期於有些成績。”
總之,那種認為《實踐論》代表著“否認理論”的“狹隘經驗論”傾向的觀點是不合乎實際的。《實踐論》從哲學上深刻地闡明瞭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必須同中國革命相結合的原則,指導和代表著我們黨的理論建設工作的正確方向。毛主席重視學習,重視理論,我們要牢記,堅持讀書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