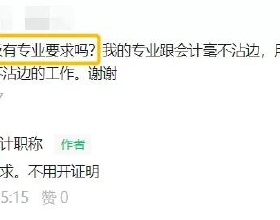去年春節,就地過年,沒能回鄉。
今年一進臘月,就計劃著有錢沒錢,回家過年,然而,疫情之下,回家過年依然要三思而後行。
昨天,兒時好友回去探親,發來圍桌團圓的熱鬧影片,勾起了一些羨慕。以前鄰居們,雖樣貌染了歲月的變化,但有熟悉的鄉音做背景聲,看豐盛的飯菜在畫面裡搖晃,觥籌交錯,推杯換盞。
不由得感慨一聲,這才是年啊。
還挺想回農村過年的,雖然也不知道回去做什麼,雖然村裡大抵也沒有年味,但就是有一種莫名的想念,伴隨著春節的臨近在發酵。
是真的上了年紀了麼,再往前倒幾年,我都是不喜歡過年的團聚的。每次都想回避那種盛裝打扮的熱鬧,討厭沒完沒了的聚會,招架不住毫無意義的寒暄,全身心抗拒這一場已經有些失去的儀式感。
過年的回鄉,每個人都想準備一次盛大的衣錦還鄉,把最多的財富和最得意的樣子展示給故土。但是精心地打扮,回去才發現只是一村子的寂靜。
當我們反覆談論城市的孤獨時,卻少有關注鄉村正在塌陷的寂寞。
一切當然是從失去熟悉開始的。許多鄰里鄉親只是過年才見一次面,恍然覺得他怎麼變成這幅模樣了,然而卻並不清楚他們都在忙什麼。
娛樂開始變得孤獨。小孩子回家沒有手機就會百爪撓心,打牌成了大人的唯一消遣。從小賭怡情上升到大賭傷身,一年的奮鬥抑制不住家鄉牌桌上一擲千金的衝動。
宴席變得孤獨。有外地務工的人,舟車勞頓回鄉幾天,一場宴請成為了最大的事情。正月裡似乎每天都在吃席,所有人都想趁著人最多的春節,風風光光大宴鄉里。
記憶中的鄉村不是這樣的,它應該是舒展的、公共的、熱鬧的,是和孤獨遠離的。
農忙時大家吆喝著去上工,隔著田地大聲交談,不是山歌卻也自有腔調。農閒和年節時小孩子都鬧渣渣的,大人們也享受在難得的悠閒中。
記憶中從前的鄉村,誰家有事全村子的人都一起出動,連宴席用的桌椅板凳和鍋碗瓢盆都是從各家湊來的。村裡還會自發形成有組織的分工,誰搭灶、誰宰殺牲畜、誰切菜、誰掌勺、誰洗碗……條理清晰、各司其職。
記憶中的鄉村還沒有隱私。住在小鎮或村落裡的記憶,大家串門子串來串去,不會像現在這樣拜訪朋友還要先打個電話問:“我方不方便到你家?”
人們喜歡在離你家很遠的時候就開始喊,大聲說笑著要你去接。於是整個村子都知道你家裡來了客,好不熱鬧。平日裡張家長李家短,飯點時聞著味兒就知道你家煮了什麼菜。
資訊的遲緩在時代的通路上拉慢了鄉村的發展,同時也圈定了一個保護層,留存了某種純真。從前的鄉村當然是閉塞的,書本和電視獲取也不夠豐富,小孩子和大人們卻總能找到自己的玩樂。
跳皮筋、跳房子、踢毽子、過家家、轉陀螺、滾鐵圈、翻花繩、翻紙殼、撿石子、彈彈珠……上山採花、下河捉魚,一整片原野都是童年的遊樂園。
不過,這些場景已慢慢遠去了。
當鄉村已經失去了記憶中的模樣,為什麼我們還是執著於一年一次隆重的迴歸呢。
大年三十回到老家時,發現大半個村子都還是關門閉戶。可十二點鐘聲敲響,邁入初一,整個村子卻突然鞭炮喧天,此起彼伏的煙花照亮了田野鄉間。
新年第一天,眼睛還沒睜開,就聽到對門的鄰居大聲叫爸爸去打牌。整個村子一下子就熱鬧了起來,全國各地的鄰居似乎在一夜之間回到了這熟悉的鄉土。
小夥子新娶了媳婦,過年總要帶回家,給鄰里相親介紹一番。好叫老人們知道,這個娃娃已然長大成人,可以擔負家庭。
小姑娘交了男朋友,帶回老家是女方家庭對姑爺最莊重的認可。
好幾個鄰居,幾年前就已經舉家搬離舊居在外省的城市置業安家,春節依然拖家帶口回鄉過年。人群中多了幾個嫩嘟嘟的小娃娃,水汪汪的眼睛裡滿是好奇。
新年第一天,見到的每一個人都把快遺忘的稱呼叫上一遍。
你祝福一句“新年快樂”,他回一句“回來了哇”。問一問一年的近況,嘮一嘮沒多少實質意義的家常。夾雜著鄉音的問候,簡單的寒暄,完整了我們過年回鄉的整個儀式。
今日的鄉村,不再如往日那般充斥了個體的所有世界。回鄉過年,也慢慢變成一種儀式,一種情懷。
記憶的烙印比血緣還深刻,會牽連著你的腳步,讓你無論身處何地,心中總有一個故土鄉村,等著你回去,即使它早已不是當年模樣。
希望,今年能回村過一個記憶中的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