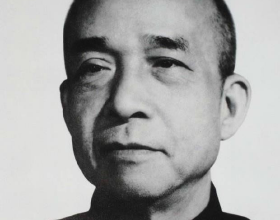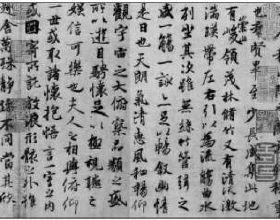老婆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減肥,這一次來勢洶洶,內服加外穿,節食加運動。我早已麻木了:減肥一定會成功,體重一定會反彈!這種時刻,千萬不要做出事不關己的樣子,要積極鼓勵,多表揚多參與。過日子嘛,多動腦子少吃虧。
常年在山裡奔波的人都不會胖,我爺爺輩裡,印象中沒見過一個胖人,到我父輩之後,一部分棄農經商或務工的,體型開始有了明顯變化。我父親六十多了,清瘦,過春節回家一時興起,和父親一起爬山走一遍之前打獵走過的老林子,順便找一找冬菇,結果是父親一邊走一邊等,我跟在後邊氣喘吁吁。
對父親爬山功夫見識最深的那幾年,到現在想起來都腿痠。每天天不亮就上山,在深山老林翻山越嶺,每天路程少說四五十里,更可怕的是,有一少半都是在懸崖峭壁上攀援,渴了喝山泉,餓了,硬扛!
爬上懸崖,是為了活捉一種神奇的動物---飛鼠,學名紅白鼯鼠。
說它神奇一點不誇張,山裡老人很多活了一輩子,知道有這玩意存在,但從沒見過。以前只有最厲害的採藥人,揹著成捆的篾繩爬上高高的懸崖頂上,從懸崖上“放繩”落到懸崖中間的臺階上收集飛鼠的糞便做藥材,藥名“五靈脂”,在採藥時偶爾能見過它的真容,並由此衍生出很多的傳說,比如,飛鼠的“翅膀”有刀刃,會割繩子;白天聽見飛鼠叫了會死人等等。
飛鼠頭像貓,眼睛超大,四肢之間有皮膜,說是會飛,其實是滑翔,像極了現在流行的極限運動“翼裝飛行”。這玩意晝伏夜出,天不黑不出窩。它的窩都是在懸崖峭壁上,一個很簡陋的石縫或樹洞就是它的家。
那一年,飛鼠突然氾濫,我家十來畝板栗被禍害殆盡。每到天一黑透,先是聽見對山懸崖上“嗚嗚”的呼朋引伴,接著,板栗園中傳來飛鼠落在樹枝上的嘩啦嘩啦聲,到第二天,地上全是被飛鼠折斷的樹枝和吃剩的板栗刺殼。那時候我正好打槍算是“出師”了,吃完晚飯,背上槍帶上手電,就到板栗園中蹲守。
嘩啦一聲,一隻飛鼠竟落在了我頭頂的板栗老樹樹冠上,我不慌不忙的先裝上底火,這才打開手電開始搜尋。陰坡山上的板栗樹都很高,三十來米的樣子,樹冠濃厚,飛鼠藏在裡邊是很難找的。不過那時候的飛鼠膽大的很,一點不怕人,我在樹下找,它竟然蹲在樹上開吃了,順著板栗殼掉落的方向,用手電照過去,只看見一對紅色的電燈泡一樣的大眼,紅白相間的身軀隱約可見。我一點不忙亂,林子裡今天來的飛鼠少說十幾只,慢慢來。舉起槍,抵肩,扳槍機,調整呼吸,瞄準,緩緩的摳動扳機,“砰”的一聲巨響,十幾顆大號鐵砂呼嘯而出,飛鼠掉落地上發出一聲悶響,緊接著又一躍而起向一棵櫟樹跳去,但明顯它受傷很重,行動遲緩了許多。我抄起一根乾柴追過去,一棍子掄下去之後,這傢伙終於不再動了。
我拎著飛鼠又長又粗毛茸茸的尾巴,將它扔到了路邊,掏出火藥壺,豎著槍管,先灌火藥,用通條墩一墩,壓一撮頭髮掩住,再灌一小把大號鐵砂,最後依然是一撮頭髮掩住槍管。忙完後,稍歇一口氣,繼續開始循著聲音尋找下一隻。那一晚,我開了十一槍,撿住了九隻,加起來四五十斤,要不是我爸聽見槍響個不停過來看熱鬧,我差點背不回去。
那時候沒人買飛鼠吃,但是皮子可以賣錢。我爸花了一上午的時間殺完剝皮。看著紅赤赤的一大堆肉,我只好嘗試著燉了一隻,這玩意比老牛肉還耐煮,肉柴,腥味倒不大。燉了六七個小時才能啃的動,可能是我的廚藝不好,味道很一般。剩下的只好便宜我家那兩隻大肥貓了,每天撐得那兩隻貓肚子圓滾滾的躺在太陽下不想動。
由於打這玩意沒啥挑戰性,我的興趣也就下降了,隔三差五的去打一兩隻回來喂貓,只到板栗季節過了,那玩意就消失了,就像從沒來過一樣。
到了第二年秋天,縣城裡來了兩夥人,一夥四川人一夥廣東人,開始收購活的飛鼠,一百三一隻。四川人不僅收購,還上山抓,帶了幾個本地人做幫工也當徒弟。這時候大家才知道,飛鼠是可以白天去抓的。靠山吃山,周圍好幾個老獵手也加入了。我爸當時還說,啥玩意要滅亡了,一定會先氾濫一陣。
秋末是農閒時節,家裡本來也窮,一天能掙個百十塊也算不低的收入。我父親在瞭解到大致方法之後,便要求我跟他一起上山。
一根細長的竹竿,竿稍綁一個鐵絲圈,這就是全部的工具了。主要難點在於怎麼找到飛鼠的洞穴,這玩意白天都是藏在懸崖峭壁上,而且它會飛,只能悄悄的接近。
我跟著我父親,真的見識到了什麼叫飛簷走壁。腳下就是萬丈深淵,石頭滾落下去十幾秒不能落地的懸崖陡坎,我爸赤手空拳就能攀來躍去,我跟在後邊腿都是軟的,一手抓住樹根石縫,一手拖著竹竿,渾身打顫。
飛鼠白天不活躍,一般不會出洞,它的洞都是很淺很簡陋的,勉強能容下它的身體。當週圍的聲音驚動它時,它會探出頭來觀察,這時候便可以將綁著鐵絲圈的竹竿慢慢伸過去,將它的頭輕輕套住,然後猛的一拽,將它從洞裡拽出來。這玩意性子烈,超兇猛,而且它的爪子是我見過最長的野物,簡直可以跟樹懶相比。抓它時必須特別小心,一爪撓住就不是幾個血印子那麼簡單了。
那一年跟著我父親,一冬天抓了上百隻飛鼠,一路驚險不斷,至今印象最深的一次,或者說至今仍是我夢魘的一次,是經過一處絕壁。
那是一處陌生的山崖,海拔已經到了將近兩千米,山頂已是樹少草多。我和父親在山上已經兜兜轉轉了大半天,找到一處絕壁中間的臺階,順著這一級臺階往前走了幾百米,一路寬的地方能有一米多,一看便知是人極少來的地方,一堆堆的明鬃羊羊糞,獐子麂子屎,還有乾燥之處的大堆的五靈脂,多的地方一處就能有幾十斤。路窄的地方,石頭明晃晃的光可鑑人,我父親說那是獸徑,千百年來野獸走多了就變成這樣了。
天色已漸漸變暗,山腳下的薄霧漸漸漫了上來,腳下的懸崖在霧中更顯得深不見底,路也越來越窄。走著走著,父親在前停了下來,猶豫了一下,再看看來時的路,然後說:你看著我怎麼過去的,不要慌,慢慢來。然後,他兩手扶著石頭,臉貼著崖壁,三兩步就跳過去了。等我走到跟前一看,“臺階”已經斷了,只剩幾塊略微凸起的石頭,三五釐米大小,光滑的像是已經盤包漿了的玉器。更要命的是上方的石壁也是凸起的,人經過時必須略仰著身體踩住那幾塊凸起的小石塊才可以透過。
我站著比劃了好久,越看越害怕。父親也不好催我,只是安慰,實在不行他就再過來帶著我原路返回,那樣的話走夜路是不可避免了。我蹲在那躊躇了好久,手心出汗變得黏糊糊的。沒辦法,硬著頭皮過吧。說真的那幾步是怎麼跨過來的我腦子裡一片空白,只記得跨過去後坐在石頭上擦冷汗。
去年過春節跟我爸聊起那幾年打獵的往事,說到過那幾步懸崖,我說:“現在做噩夢還經常夢見”。
我爸說:“我知道那次嚇壞你了,當時你跨過去之後蹲那就吐了”。
我竟然完全不記得當時吐過,一整天沒吃沒喝,估計吐也只能吐苦水吧。
一陣沉默,為了打破氣氛,我說:那時候整天拖一根長竹竿在林子裡鑽來鑽去累死了,你看現在的魚竿用來抓飛鼠多好,又長又輕還不佔地方“。
“那時候,要知道你一兩千塊錢買根魚竿,腿都給你打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