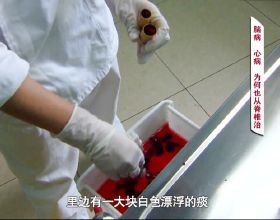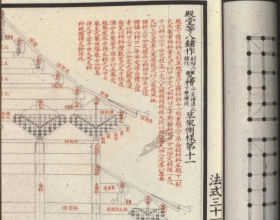作者簡介
鹿欽海,字玉山,1965年出生,山東高密人,1988年畢業於曲阜師範大學,自由職業者。作品在《中國旅遊報》《齊魯晚報》《山東水利報》等發表,出版過散文集《故鄉、爺孃和我》,作品收錄到《山東景區導遊詞選編》等。
童年美餐
至今不知童年的判定該從多大到多大,只是感覺那個時候肯定還小,甚至還沒有上學吧。
我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出生的,我們那個時候的童年,正好趕上了文革。在那個火紅的年代,我們除了跟著迎風招展的紅旗奔跑,對吃的理解,也根深蒂固。
那個時候全世界範圍內,經濟還很落後,所以我童年時候對吃的印象,還停留在傳統的“工藝”。因為平常都是地瓜面窩窩頭、煮生地瓜乾子、煮地瓜,亦或還有改善生活的玉米麵餅子等等,至於就菜,無論是醃白菜幫子、蘿蔔頭子、辣菜疙瘩,亦或偶爾一頓的大白菜、粉條燉豆腐,都顯得平常簡單,根本談不上是美食。
那時候爺爺還長年累月地吃一種叫“散糕”的東西,讓我想起來就眼淚汪汪。那還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吧,爺爺因為牙不好,咬不動地瓜面窩窩頭,奶奶就把地瓜面用水合起來、再稀稀拉拉地灑在高粱秸做的箅子上蒸熟了,用一條已經發汙的包袱包起來,送到生產隊送飯的挑擔裡。在坡裡幹活的爺爺,接到這個叫“散糕”的地瓜面飯後,總是小心翼翼地端到避風處,就著一碗白開水,慢慢地吞嚥下去。
爺爺上過四年私塾,當年還婉拒了去柴溝供銷社公幹,青年時候還逼著父親“休學”、選擇了省吃儉用地攢錢置地,也終於在1949年前置下了十幾畝薄田,結果就是他老人家這個“三十畝地一頭牛”的樸素妄想,讓現實摔的粉碎不說,還搭上了孩子們的前程。不知爺爺扛著犁耙、吃著散糕,艱難地耕作在生產隊的時候,他老人家有沒有對當年那個選擇後悔?
童年時候,從沒記著爺爺跟我交流過、也不記著爺爺抱過我,至今印象最深的,是我小時候調皮,讓爺爺捶了一拳。但我佩服爺爺的人格,至今仰視。也正是因為爺爺那些年的散糕,讓我至今對吃,顯得尤其知足,所以小時候那些美食,就終生難忘。
豬肉是那個時候最美的食品,雖然做起來五花八門,但口感只有一個:香!所以蒸著的叫“蒸肉”、炸著的叫“炸肉”、燉著的叫“紅燒”,而且從沒有脫脂之說,買肉也是選擇“肥”的下手,不跟現在這樣,總是挑著瘦肉買。
但那個時候豬肉憑票供應,一是不能隨便買、二是也沒錢買,所以蒸肉、炸肉這些吃法,只有在過年或者辦大宴的時候才可以見到。但那個時候過年的那點肉,得等著“大客”來的時候才上席、大宴的時候也得有資格上“大席”的人才有資格品嚐。
但不論怎麼樣,爺孃還是想方設法,怎麼也得讓孩子們,在春節的時候,吃上一頓“肉飯”、解解饞。我雖然不是一個標準的“吃貨”,但爺孃在準備這些的時候,我總是認真觀摩、用心記下了這些過程。蒸肉的做法,是先擀一張大餅,攤在小麥秸做的箅子上,撒上細面後,把切好的肥肉放到大餅上,再用細面輕輕地攪拌一下、把肥肉裹起來,蒸熟了就好。至今記著這肉放到嘴裡,那滑滑的、彷彿一咬就碎的嫩軟,香香的,挺美。但再美再香,一般人也就吃幾塊的“本事”。吃多了,就膩的“難受”、享用不了。我們家,只有爺和我,有開懷吃下一碗的“胃口”。炸肉是在鍋裡燒著油,把肥肉沾在生面攪拌的粘糊糊裡逛一下、再撈出來,放在油鍋裡炸。剛炸出來的時候,填到嘴裡,香脆滑口、膩到心軟。也是,一般人也吃不了幾塊。
這倆種都是農村大菜,卻也是一般人享受不了的肥膩美食,只有那種“瘦肉丸”,還得加上蔥蒜薑末之類,才是一般人都可以吃上一些的美味。只是我不怎麼喜歡這些蔥姜味道,小時候總是說這是“驢屎蛋子”,為此還惹得表兄很不待見。
我們老家昌濰大平原,雖然離著青島很近、雖然村邊就是綿延幾十裡的五龍河,卻因為政治環境所限,很少可以吃到水裡的東西。偶爾吃到的,無非就是常見的青鯽子鹹魚、蝦醬。饞“魚”了怎麼辦?一種流行於當時農村的“美食”,就應運而生了,叫“魚醬子”。寫出這個名字之後,很多人肯定浮想聯翩,甚至都可能產生出“魚之精華”的幻覺。其實差矣,這雖然跟魚逃不脫關係,卻羞的說出口來。因為這是用洗過鹹魚的水,再攪和上些面,或者再放上些菜吧,燉熟了,吃起來“鹹鹹”的,有點“魚味”而已。
買一次鹹魚,可以挖空心思地吃到這個程度,當時的經濟,可以用“崩潰的邊緣”去形容麼?
寫到這裡,就想起初二的時候,有天早上起晚了,沒來得及吃飯就匆匆上學去了。爺那天就買了油條,帶著來到教室裡、遞給我。下課後,狼吞虎嚥下去,咂摸一下嘴唇,才忽然感覺,這油條的味道,真好!
只是到了初中的年紀,還是童年麼?
如果說初中還是童年,有次我跟一個同學去了土莊蘋果園,爬上果樹之後,挨個摘著吃的感覺,或許只有孫大聖有過吧?只是那個時候的國光蘋果挺酸的,至今都記著吃到了倒牙,好幾天吃飯都不得勁。所以,雖然很少可以吃到蘋果,但那個時候的蘋果,確實不算美味。
寫到這裡,就想起小學時候的“一頓飯”來,那是個夏天,我負責給生產隊割的三十斤青草完成上繳任務之後,回到家裡,爺孃也從常家疃割草回來不久,家裡連一頁煮熟地瓜幹都沒有。這個時候爺正在餷豬食,揭開鍋來,爺放進去的粗地瓜面、乾地瓜葉子已經熟了,立馬舀上一碗,連醃白菜幫子都不用就,稍微涼到可以上嘴,就狼吞虎嚥地吃起來。已經忘記吃了幾碗了,但當那空蕩蕩的肚子填飽、那餓得頭暈目眩的感覺過去之後,其實豬食,也是最好的美餐之一。
童年的快樂與困惑,雖然轉瞬即過,但童年養成的習慣如果挑肥揀瘦,恐怕會造成很多營養上的偏差,還好,我這連豬食都可以狼吞虎嚥的食慾,不但很好地繼承了爺孃勤儉持家的美德,還吃飯潑辣、不奢魚肉,所以也一直覺得吃飯只是為了填飽肚子,去他媽的舌尖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