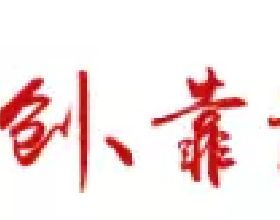文藝家李漁“生平有兩絕技,一則辨省音樂,一則製造園亭”。
他的園林建築才能,在《閒情偶寄》和芥子園遺蹤中也有吉光片羽。
居室乃安身之所,也是用心之地。
李漁居室設計中的安身安心觀念,體現出他無奈獨善其身的生涯中,隱約閃現的濟世安邦的渴望和儒家美學觀念。
李漁是當時有名的居室設計專家。他家也有類似樣板間的功能。他自我評價其居室設計佈置因地制宜,不拘成見,別出心裁。
“使經其地入其室者,如讀笠翁之書,雖乏高才,頗饒別緻,豈非聖明之世,文物之邦,一點綴太平之具哉?”
李漁的居室設計突出了文人風格,即使放在今天的家裝市場,依然是中式風格的主流風尚。
“夫房舍與人,欲其相稱”
李漁是個外浪內儒的藝術大家,藝術和美是他的最高追求,而社會生活是他的關注焦點。
在他看來,置宅安身首先是一種基本需要,“人之不能無屋,猶體之不能無衣。
衣貴夏涼冬煥(音同“欲”,yu),房舍亦然。”房舍應適於人居,以人為尺度,太大太小均不舒適,令人不快。“夫房舍與人,欲其相稱。”
廣廈高堂顯得人矮小,可鋪陳擺設以“略小其堂,寬大其身”;而低簷窄廬倍覺窘迫,則要注重收納打掃,“淨則卑者高而隘者廣矣。”
李漁認為,“土木之事,最忌奢靡,匪特庶民之家,當崇簡樸,即王公大人,亦當以此為尚。
蓋居室之制,貴精不貴麗,貴新奇大雅,不貴纖巧爛漫。”
他一心要倡導“雅素而新奇”的居室風格,而且立定平民甚至貧民根基,“凡予所言,皆屬價廉工省之事。”
李漁注重創新,認為凡立戶、開窗、安廊、置閣事事皆仿名園,纖毫不謬,是抄襲陋風。
他把其藝術創新精神,移植到製造園亭之事業中,力求別開生面,別出心裁,形成自家風貌。
藝術以無法為至法,園林藝術也如是,“山之小者易工,大者難好”,可以以土代石,土石相伴,草木滋生,則渾然一體,生機盎然。
“雖由人作,宛自天開”(計成《園冶》),這正是為文造園的至高境界。
文如其人,庭院也是主人寫照,疊山壘石名手,往往俱非能詩善繪之人。
“主人雅而取工,則工且雅者至矣;主人俗而容拙,則拙而俗者來矣。有費累萬金錢,而使山不成山,石不成石者,亦是造物鬼神作崇,為之摹神寫像,以肖其為人也。”
建築園林美學中的知人論世的藝術批評,欣賞決定創造的接受美學,均可在這裡窺見淵源。
以藏書養心
有一間自己的書房,佈置一個心儀的精神空間,是許多文人的追求,書齋聯匾、桌椅爐瓶、文房四寶、琴棋書畫、古玩信箋等,曾是文人雅興所鍾情的審美焦點。
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科舉時代,居室裝潢的文人情趣是時尚領軍者,富貴俗麗則在其次。
而李漁的居室美學,實用之外,尤重書香意趣。
他的頂格用糊紙做成“手卷冊頁”形狀,“簡而文,新而妥”;他的地磚“能自運機”,“使小者間大,方者合圓,別成文理,或作冰裂,或肖龜紋”,他的借景扇窗梅窗巧絕,而亂石壘成的牆頗具禪意,“泥牆土壁,極有蕭疏雅淡之致”,花鳥魚蟲力求如置自然場景中,兩相愉悅。
“書房之壁,最宜瀟灑。壁間書畫自不可少,然貼上太繁,不留餘地,亦是文人俗態。”
聯區設計當然是書房點睛之筆,他又特別為文人設計了有收納廢稿殘牘等雜物的抽屜書桌,多容善納的書櫥,兩房借光的壁燈,甚至有書房內用竹筒引流的便廁,真是貼心設計,細緻入微。
今天的室內設計師怕是難得為業主這般用心考慮的。
看來自己的房子,還得由自己規劃,對於精神品位精細固執的文人,更是如此。
書房生活無非讀書著書,書房的主角自然是書。
書比古董珍玩這些器物層次的東西,更能體現文人的活精神、真性情。
“物之最古者莫過於書,以其合古人之心思面貌而傳之乎?其書出自三代,讀之如見三代之人;其書本乎黃虞,對之如生黃虞之世,舍此則皆物矣。物不能代古人言,況能揭出心思而現其面貌乎?”
這顯然是一個典型的真文人的價值觀,是這個以讀書為最大樂事,以著書為療疾秘方,以藏書養心,以售書為業的文人最真實的心思。
“人慾活潑其心,先宜活潑其眼”
李漁是個高產文人,卻不是個只顧埋頭幹活的苦工,在精神生產的同時,把自己的文人生涯,打造成後人仰慕的審美生存,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不為其“窮”,而為其“酸”。
“吾貧賤一生,播遷流離,不一其處,雖債而食、賃而居,總未嘗稍汙其座。性嗜花竹,而購之無資,則必令妻摯忍飢數日,或耐寒一冬,省口體之奉,以娛耳目,人則笑之,而我怡然自得也。”
李漁的儒家風範,在居室美學中也展示出來。
如他談到牆的時候,“居室器物之有公道者,唯牆壁一種,其餘一切,皆為我之學也。家之宜堅者牆壁,牆壁堅而家始堅。其實為人即是為己,人能以治牆壁之一念治其身心,則無往而不利矣。”
如今城市樓房建築牆壁,更是眾人公器,但裝修時首先拆牆打壁,而影響整體建築安全,顯然有違公德,此時倒可重溫李漁一說,比理學名賢之說更顯親切。
李漁把治身心之說,引入日常生活,於行中求知,於知中踐行,並未流俗為工匠,也不高蹈作聖人,不過是生活常態中彰顯智慧情趣,更符合現代人的性情行止。
佈置器玩與書法中的結構、繪畫中的經營位置、音樂中的主旋律、文學中的敘事線索也是同理,得全域性在胸,死物活用,才能血脈貫通,活潑生動。
“安器置物者,務在縱橫得當,使人入其戶登其堂,見物物皆非苟設,事事具有深情。”李漁的藝術感覺,使其佈置器玩也迭出妙招,忌排偶,忌八字、並列、四方、梅花等刻板對稱,宜品、心、火形等活格局,“但宜疏密斷連,不得均勻配合,是謂參差。”這個“參差”,與張愛玲的“粉紅配蔥綠”是一個道理。
而李漁給這個“參差”灌注的,是生機和情感的溫度,關鍵在“貴活變”、“尚新奇”。“幽齋陳設,妙在日新月異。
居家所需之物,惟房舍不可動移,此外皆當活變。何也?
眼界關乎心境,人慾活潑其心,先宜活潑其眼。
或卑者使高,或遠者使近,或一物別之既久,而使一旦相親,或數物混處多時,而使忽然隔絕,是無情之物變為有情,若有悲歡離合於其間者。
如此一來,家庭裝飾便也成了藝術創作,今天的專業設計師與家庭主婦均可體會其趣、運用其妙,這正是生活美學的迷人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