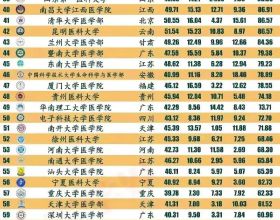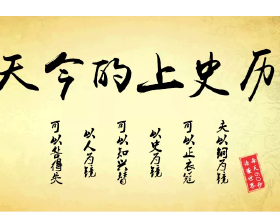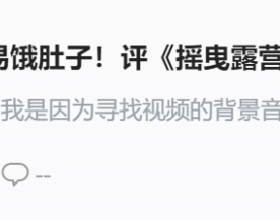陶行知在1919年7月一次關於“新教育”的演講中,提到了新教育對新教員的要求,第一條就是“要有信仰心”,他認為,對教育的“信仰心”,不僅來自教育本身的意義,“是永久有益於世的”,而且還來自教育所帶來的快樂。
陶行知的原話是這樣說的:“這裡頭還有一種快樂——照我們自己想想,小學校裡學生小,房子小,薪水少,功課多,辛苦得很,哪有快樂?其實,看小學生天天生長大來,從沒有知識,變為有知識,如同一顆種子由萌芽而生枝葉,而看他開花,看他成熟,這裡有極大的快樂。……那不信仰這事的,可以不必在這兒做小學教員。一國之中,並非個個人要做這事的,有的做兵,有的做工,有的做官……各人依了他的信仰,去做他的事。一定要看教育是大事業,有大快樂,那無論做小學教員,做中學教員,或做大學教員,都是一樣的。”(《陶行知教育文集》)
從這裡可以知道,當時也有教師抱怨“房子小,薪水少,功課多,辛苦得很”,絲毫看不到教育職業有什麼快樂可言。這和今天不少教師的心態不是一樣的嗎?
教育的快樂源於何處?陶行知認為,教育的快樂首先源於對教育本身的信仰,“那不信仰這事的,可以不必在這兒做小學教員。一國之中,並非個個人要做這事的,有的做兵,有的做工,有的做官……各人依了他的信仰,去做他的事”。
說到“依了他的信仰,去做他的事”,我想到有一年我去參觀青海塔爾寺的時候看到酥油花的情景。寺廟的一個僧人告訴我,酥油花塑造工藝複雜,要進行大量的選料、配製、做模等前期工作。由於酥油易融化,藝僧們徒手捏塑酥油花時只能在零下十幾攝氏度的陰冷房間裡封閉工作。在製作過程中,藝僧手指被凍得疼痛難忍,失去觸覺,但他們依然將酥油做成一朵朵精美的花。這些酥油花只能“存活”幾個月,因為天氣轉暖便要融化,於是每年都要重做酥油花。因此,最後藝僧們的手指都會潰爛,且終身殘疾。這些藝僧都是自願做酥油花的,沒有誰強迫他們,哪怕手指潰爛,他們也無怨無悔。這些美麗的酥油花都不是為市場而製作,唯一的用途就是放在寺廟裡供奉神靈。沒有半點兒功利色彩,而完全是出於心靈深處的信仰,而自覺自願地奉獻出自己的智慧和健康。在世俗的人看來,他們很苦,但他們自己卻覺得很幸福——這就是信仰的力量!
回頭說教育。並不是每一個教育者都會把教育當信仰,但要看到,陶行知、蘇霍姆林斯基、魏書生、崔其升等人的確是對教育有一種類似於宗教一般的信仰,他們不但為中國教育作出了貢獻,也因此而獲得內心的自由、寧靜與幸福。我們也許不應苛求每一個教師都把教育當信仰,但如果教育者有了一份陶行知所說的對教育的“信仰心”,一定會享受到更多的教育幸福。
陶行知還認為,教育的幸福源於看著孩子成長:“看小學生天天生長大來,從沒有知識,變為有知識,如同一顆種子由萌芽而生枝葉,而看他開花,看他成熟,這裡有極大的快樂。”讀到這裡,我想到了我從教幾十年來所教過的一批又一批學生。我帶班常常是“大迴圈”——從初一到高三,一教六年;當然,也有隻帶初中三年或高中三年的“小迴圈”。但無論“大迴圈”還是“小迴圈”,幾年中,看著孩子的成長,真的是一件很美妙的事。他們剛進校時,還是剛畢業的小學生,十一二歲,十二三歲,活潑調皮的小男孩,天真爛漫的小姑娘;當他們高三畢業離開我的時候,已經是英俊健壯的小夥子,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了。然後我又回頭帶初一,又迎接一批可愛的小不點兒,然後又陪著他們一天天長大成人……多年後,他們回來看我,有的是企業家,有的是作曲家,有的是醫學專家,有的是科研專家,有的是飛行員,有的是足球教練,有的是搖滾歌手,有的是大學教授,有的是鄉村教師……無論他們從事什麼,只要他們善良、正直、勤勞,就是我最優秀的學生,也是我幸福的源泉。
有一個叫王紅川的孩子,是我大學畢業所教的第一個班的學生,當初的他,瘦瘦的,小小的,戴個小眼鏡,特別機靈可愛,因為體質較弱,我特別呵護他,有一次還幫他揍高年級欺負他的學生,為此我還捱了學校的處分。我每天早晨騎腳踏車上班要經過他家附近,有一段時間他每天早晨都在街邊等我,我到了以後,他便跳上我的腳踏車後座,我載著他上學去。多年後,他成了一位著名的西醫骨科專家。還有一個女生叫“周惠”,高一新生報名的當天晚上,她就病了,肚子疼得厲害。我用腳踏車送她到醫院急診室,結果醫生說必須住院,於是,我又揹著她到了山上的住院部。在山路上,為了安慰趴在我背上輕輕呻吟的周惠,我一邊喘息一邊給她開玩笑:“騎在人民頭上的,人民把他摔垮!”多年後,在德國大學教書的周惠,帶著女兒回來看我。回憶當年我揹她上醫院的事,她說當時她疼得說不出話,但在心裡默唸著:“給人民做牛馬的,人民永遠記住他!”
2018年8月,應學生的要求,我為他們上了一堂退休前的“最後一課”,不同年級的學生都來了。從幾年前教畢業的“關門弟子”,到已經年過半百的第一批學生……180個座位的階梯教室,擠滿了400餘人。王紅川帶著妻子和女兒來了,周惠專程從德國趕回來了,還有當年的“差生”如今的省足球教練張凌,還有當年的學霸如今的飛行員、機長吳鏑……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已經不再年輕,但看到他們,浮現我眼前的,依然是他們當年稚氣可愛的面容。當我講課時,他們一雙雙痴迷的眼睛凝視著我,已經二三十歲、四五十歲的眼睛裡依然閃爍著當年十二三歲的光芒。那一刻,我感到我面對著屬於我的一片星辰大海!
我想到了加拿大學者馬克斯·範梅南的話:“教育學就是迷戀他人成長的學問。”(《教學機智——教育智慧的意蘊》)不過,我要補充一句:“迷戀他人成長的人也必將被他人迷戀!”
我想到了蘇霍姆林斯基曾經說:“我生活中最主要的東西是什麼?我毫不猶豫地回答:對孩子的愛。”(《育人三部曲》)我根據自己切身的感受,也想補上一句:“以及孩子對我的愛!”
我想到了陶行知的話:“看他開花,看他成熟,這裡有極大的快樂。”我還想補充一句:“不只是看孩子開花與成熟,在陪伴孩子成長的同時,我也開花,也成熟,同樣有極大的快樂。”
(作者系新教育研究院院長)
《中國教育報》2021年11月17日第9版
作者:李鎮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