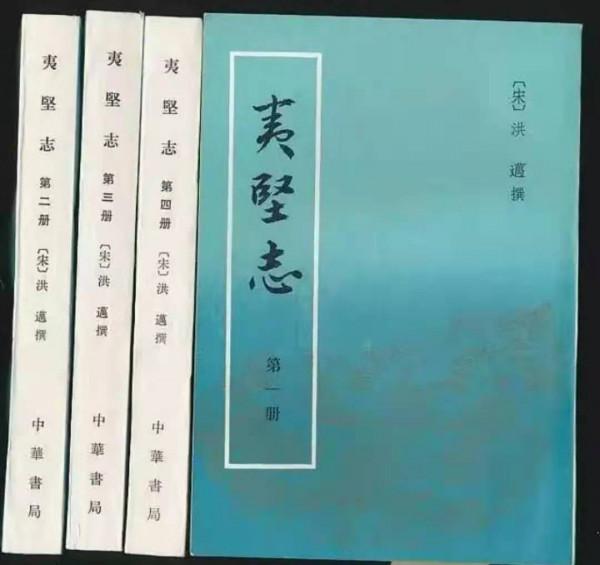宋朝在歷史上以經濟繁榮,科技先進,文化發達著稱,被歌頌為中國古代文明的巔峰。在人們的印象中,宋朝社會平安富庶,政治氣氛寬鬆自由,統治者寬厚仁慈,一派繁花似錦的盛世景象,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然而有幾個問題卻無法迴避,一個如此優秀的朝代,為什麼會發生歷史上最多的農民起義?為什麼其疆域在歷代大一統王朝中是最小的?為什麼要向鄰國稱弟、稱侄、稱臣?為什麼每年要花大量“歲幣”朝貢外國買平安?為什麼會釀成華夏曆史上空前絕後的靖康之恥?
更重要的是,在發生瞭如此多的不堪事件後,這個朝代為什麼仍然能以華美的形象垂諸清史呢?原因在於,這種美好存在於文人的筆下,而歷史,正是由文人秉筆書寫的。
對於文人和士大夫來說,宋朝確實是個鑽石般璀璨的夢幻時代,這個時代充滿了文人的榮耀,也給後世文人留下了最美好的記憶。
宋朝文官的俸祿是歷朝最豐厚的。宋朝官俸是以“貫”來計算的,1貫就是1兩銀子或者1000文錢,其中一文錢大致相當於現在的8毛,所以一貫錢就相當於800元。宋朝的高階的官員,每個月可以拿到的俸祿是四百貫錢,也就是相當於32萬人民幣,而這還不是全部,其他各種補貼甚至比俸祿還多, 比如餐飲補貼、燃料補貼、保姆補貼等等。像參知政事或樞密使一級的官員,月收入都是超百萬人民幣的,其生活之優裕可想而知。
由於不殺大臣是宋朝開國就立下的國策,所以官員的言行比其他朝代要自由得多,在烏臺詩案中,蘇軾以詩文訕謗朝廷,宋神宗雖然非常痛恨他,卻仍讓他逃得性命。
如果說大臣可以不因言喪命是一種進步,那麼對那些犯下反人類罪行的官員也予輕釋,就是無底線的放縱了。
南宋嘉定戊寅年冬天,欽州知州林千之殘害孩童一案事發。他為了治病,竟然聽通道士之言,“以童男女肉強人筋骨”,為此他派人在欽州和鄰近的橫州大肆劫掠孩童。大量孩子失蹤引起了百姓的恐慌,直到他派出的爪牙被橫州官衙抓獲,人們才知道林千之身為一方父母官,竟然是個吞噬兒童的惡魔。如此十惡不赦的暴行令當時還比較野蠻的廣西土司官員都驚駭不已。然而林千之是朝廷命官,他們無法處理,就將案情上報,廣西安撫司也感到棘手,就奏報了朝廷。
按理,林千之罪大惡極、天理不容,按律應處死,但朝廷卻不願意破壞不殺大臣的政治規矩,於是重罪輕判,只是將林千之追毀除籍,發配吉陽。林千之被流放後過了幾年就遇大赦被釋放了,直到南宋滅亡後,他都活得好好的。他在亡國之後每天舞文弄墨,自娛自樂,過得逍遙快活,據宋代筆記《鬼董》的記載,林千之“秩滿歸裡,宋亡,以翰墨自娛。”這種對官員的寵溺和放縱,對百姓們來說是何等殘忍,然而在宋朝,那些失去孩子的百姓是無處說理的,絕不會有官員來為他們討回公道。
文武結合,相輔相成,是歷來的治國之道,兩者不可偏廢,可是在宋朝,文武官員的地位嚴重扭曲,文官的地位至高無上,而武將則如文官的奴僕一般。慶曆八年到皇祐五年,名將狄青任定州總管時,韓琦任定州知州兼安撫使。有一次,狄青的下屬焦用因為犯錯被韓琦抓了,狄青趕去求情,他站在臺階下不敢上前,只是懇請堂上的韓琦:“焦用作戰勇猛,是個有軍功的好男兒。”可是韓琦聽後卻譏笑道:“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名者才是好男兒!”然後當著狄青的面誅殺了焦用,狄青驚懼萬分,渾身戰慄,卻不敢離開,直到有人提醒韓琦狄青還站在堂下,他這才讓狄青回去。
王銍所著的《默記》是這樣記載這件事的:“……青舊部焦用押兵過定州,青留用飲酒,而卒徒因訴請給不整,魏公命擒用,欲誅之。青聞而趨就客次救之。魏公不召,青出立於階下,懇魏公曰:‘焦用有軍功好兒。’魏公曰:‘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者乃好兒,此豈得為好兒耶?’立青而面誅之。青甚戰灼。久之,或曰:‘總管立久。’青乃敢退。”
狄青對此也很不忿,經常對人說:“韓樞密功業官職與我一般,我少一進士及第耳。”然而,在宋朝的大環境下,他毫無辦法,如此貶抑武將,宋朝的軍隊又怎能抵禦外辱?
宋朝為什麼要如此重文抑武呢?因為趙宋的天下是篡周得來的,因而得國不正,而且欺負孤兒寡母的吃相尤其難看,所以特別害怕讀書人書寫春秋的那支筆。秦始皇因為得罪讀書人,被謾罵千年的教訓,趙氏當然清楚,所以他們對文人採取贖買政策,換取他們在清史上的稱頌。趙匡胤以武人篡權上位,他自然深知武將擁有實權後,可能對政權形成的威脅,所以對武人的防範特別嚴密,並因此設定了“內外相制”、“強幹弱枝”的兵制,竭力分散兵權,打壓武將的地位。
宋朝遠比唐朝弱小,可是官員數量卻遠多於唐朝,唐朝鼎盛的玄宗時期,官員有18000人左右,而宋仁宗時官員數量達到48337人,是唐玄宗時代的三倍有餘。
宋朝官員不僅數量龐大,還要享受駭人聽聞的高薪,開封府尹的年收入高達3.5萬貫錢左右,另外冬春兩季可分到13匹質量上好的絲絹,夏季可以分到1匹紗,秋季可以分到30匹絲綿。這個收入,與宋朝一個州的財政收入相當,真可謂是以萬民之膏腴奉一人之身。
按史料記載的資料換算,唐太宗年間,一品官員的年收入約為170萬元左右,而這只是宋朝相同品級官員一個月的俸祿。唐朝那些開創了萬國來朝雄風的赳赳幹臣們,要是知道後來那些見了番邦就下跪的猥瑣同行竟然拿這麼高的俸祿,不知會作何感想。
在供養這麼臃腫的官僚文人集團的同時,宋朝每年還要用大量“歲幣”去朝貢遼、金、西夏,以獲得苟安,因此財政支出極大。可是數量龐大的文人階層不事生產,不納稅賦,而且宋朝開國以來就鼓勵士大夫“擇便好田宅”,廣置田產,又奉行“田制不立”和“不抑兼併”的土地政策,導致了嚴重的土地兼併,結果這種財政壓力最終都落在本已貧苦的百姓身上。朝廷則透過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和濫發紙幣(交子)來搜刮財富,地方官吏還要額外索求,中飽私囊,普通百姓的負擔之沉重無以復加,他們哀嘆“終歲勤動,妻子凍餒,求一日飽食不可得。”當他們實在無以為生時,便頻頻起來造反,規模比較大的就有王小波,方臘,楊么等起義,規模小的更是不計其數,其中就包括人們熟知的宋江起義。
方臘起義時,宋代文人方勺親歷了這一劫難。事後,他寫下《青溪寇軌》一書,對這次事件做了詳細記載,並分析了禍亂產生的原因。
據方勺的記敘,宋徽宗年間,北宋政治腐敗,社會黑暗,朝政被蔡京童貫一夥人把持,他們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不斷蠱惑諂媚宋徽宗。童貫在蘇州和杭州開辦了造作局,專門為宋徽宗置辦精美豪奢的御用物品。與蔡京、童貫並稱“六賊”的朱勔為了刻意奉迎痴迷藝術的皇帝,在江南蒐羅各種奇花異石進獻,稱為“花石綱”,宋徽宗在他們的誘惑下,變得越來越奢靡腐化,對民間索求無度。
為了運送“花石綱”,需要動用大量人力物力,於是造辦局的人就在運河上攔截運往各州道的糧餉,隨意徵用民間商船,押運的胥吏們如狼似虎,趁機勒索沿途州縣,連那些撐船的船工也狐假虎威,橫行霸道,人們都敢怒不敢言。
有些特別巨大的沉重石頭無法在運河裡運輸,只能走海路,如果遇上風浪,則船沉人亡,許多伕役因此喪生。
宋徽宗鍾愛的那些奇石,不是在深山溝壑裡,就是在浩淼江湖中,採運異常艱難,但皇帝千方百計要搞到,而且限時限刻,一旦不能如願,經辦者就要受重罰。當時的百姓家中,要是被造作局的人發現有皇帝可能喜歡賞玩的假山石木,馬上就派人上門,用一塊黃帕蓋上,指明這是御用物,任何人不得觸動,卻又不馬上來取走,只是命令這戶人家仔細看護,稍有不慎就要獲罪。等到啟運時,為了把這些花石搬出去,必然要拆牆扒屋,毀壞人家的宅院,以致江南百姓家中都不敢放置石木古玩,生怕招來災禍。
為了運“花石綱”,朝廷徵發大量百姓去服徭役,許多人死在途中。為了支付“花石綱”的巨大開支,官府對民眾橫徵暴斂,百姓們被迫變賣田宅甚至是兒女應付捐稅,直至傾家蕩產,在這種殘酷掠奪下,民間怨聲載道,動亂便逐漸醞成了。
在方勺筆下,“天下監司牧守,無非時宰私人,所在貪墨,民不聊生。”一派百姓生活痛苦,官吏既貪且酷的黑暗景象。在朝廷的殘暴壓榨下,當時舉旗造反的遠不止方臘一家,《青溪寇軌》中就提到了宋江、仇道人、呂師囊、沉十四公、朱信、吳邦等多股響馬。要不是實在活不下去,或者有了深仇大恨,誰願意鋌而走險嘯聚山林?
宋朝給人留下了雖然軟弱但也寬容溫和的印象,可事實上,宋朝對文人確實是溫軟的,但對底層百姓的統治卻很嚴酷,絲毫不見仁慈,鎮壓造反時,經常一殺就是幾萬人,還築起京觀恐嚇百姓,場面血腥恐怖。宋軍對外作戰極其拉誇,可是鎮壓農民起義卻極其兇猛。據《青溪寇軌》記述,方臘起兵時,事發非常突然,而且很快呈遼源之勢。由於那時宋朝已經與金約好聯合攻遼,軍隊都調到了北方。在接到方臘造反的警報後,卻並沒有措手不及,而是迅速揮兵南下,動作兇猛,幾乎以摧枯拉朽之勢,不到兩年就撲滅了起義,官軍最終殺人達百萬之巨,方臘哪有這麼多士卒,死者多數是無辜百姓。為什麼宋朝在攘外和安內兩種場景下的表現大相徑庭?只能解釋為,文人們認定,外敵只是要錢要土地,無關根本,而農民起義會要他們的命,所以對外投降,對內鎮壓是宋朝的國策,誰敢反對這一國策,不要說是普通百姓,就是文人士大夫,也是可以殺的。
當金人兵臨汴梁城下時,有一名太學生叫陳東,他投筆從戎,以身報國,組織大家請願參戰,很有感召力,得到了廣泛支援,陳東也因此聲名鵲起,烜赫一時。然而,這卻讓本是驚弓之鳥的宋高宗感到了不安,生怕威脅了他的統治。南渡後,迫於陳東的聲望,趙構只得封了他一個官位,可陳東卻連續三次上書,積極主戰,請罷奸臣。這就大大地犯了趙構的忌,連大將岳飛都因此而死,遑論一介書生?結果被找了個藉口殺害了。後世史家評論:“東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死。”
宋朝的刑法也極其殘酷,像凌遲這種酷刑,雖然宋朝以前早已出現,但都屬於法外之刑,或者存在於遼國這樣的遊牧政權刑法中,在中原的漢族王朝中,第一個將凌遲納入刑法的,是宋朝,而且是在以仁慈著稱的宋仁宗當政年間,如果說一開始這種酷刑還只是用於罪大惡極之徒,後來就被濫用了。據《通考·刑制考》:“凌遲之法,昭陵以前,雖兇強殺人之盜,亦未嘗輕用,熙豐間詔獄繁興,口語狂悖者,皆遭此刑。”意思是,宋仁宗以前,凌遲之刑的使用還比較謹慎,但後來,連說話不小心,太過狂妄,也會遭凌遲。可見宋朝對百姓刑罰之殘酷。
由於占人口少數的文人集團鯨吞了鉅額社會財富,宋朝廣大百姓的生活資源極其短缺,以至於為了爭奪生存權而陷入嚴重內卷,甚至經常發生人相食的慘劇。南宋大臣洪邁所著的《夷堅志》中記載了這樣一件可怕的事:“宣和初,有官人參選,將詣吏部陳狀,而起時太早,道上行人尚希,省門未開,姑往茶邸少憩。
邸之中則浴堂也,廝役兩三人,見其來失期,度其必村野官員乍遊京華者。時方冬月,此客著褐裘,容體肥腯,遂設計圖之。密擲皮條套其項,曳之入簾裡,頓於地,氣息垂絕,群惡誇指曰:“休論衣服,只這身肉,直幾文錢。”以去曉尚遙,未即殺。
少定,客以皮縛稍緩頓蘇,欲竄,恐致迷路,遲疑間,忽聞大尹傳呼,乃急趨而出,連稱殺人。群惡出不意,殊荒窘,然猶矯情自若,曰:“官人害心風耶!”俄而大尹至,訴於馬前,立遣賊曹收執,且悉發浴室之板驗視,得三尸,猶未冷,蓋昨夕所戕者。於是盡捕一家置於法,其膾人之肉,皆惡少年買去雲。”
這段文言文翻譯成白話文是這樣的:北宋徽宗宣和初年,外地有個官員來京城來參加晉職選拔,他按規矩去吏部遞交材料。但那天他起的太早了,天沒亮就出門,路上還沒有什麼行人,吏部也還沒有開門辦公,他就找了一個茶館歇息等待。
這間茶館裡面還有個澡堂。澡堂子裡只有兩三個小廝,他們一看這官員對京城人的作息時間都不瞭解,料定他是一個鄉野村官,第一次來京城,在這裡人生地不熟。 當時正是寒冬臘月,他們看那官員,身穿昂貴的褐色皮裘, 體態肥胖,便心生歹意,準備加害於他。他們偷偷拿出皮條做的套子,突然從官員身後擲出,套在他脖子上,使勁勒住,一邊勒一邊把他往布簾子裡拽。 他們把官員拖進裡間,扔在地上,看樣子已經氣絕身亡了。這幾個惡徒高興地說:“先不說這裘皮大衣,就他這身肥肉,也能賣幾個錢。”但此時距天亮還早,他們沒馬上宰割這個人。
過了一會兒,官員脖子上的皮套子有點鬆了,這官員也緩了過來。他琢磨著想跑,但又怕跑出去迷路。就在此時,他忽然聽到大街上有大員出行的鳴鑼開道聲,顯然是送這個大員上朝的儀仗隊伍過來了。這官員忽然一下子竄出去了,一邊衝到大街,一邊大喊:“殺人了!殺人了!”那幾個歹人猝不及防,一時非常慌張,但還強作鎮靜,跟出來說:“這個官員精神病發作了!”
很快那大員已經到了,官員跑到大員馬前訴說了自己剛才的遭遇。大員馬上命令捕快把這些賊人全部抓起來,並搜查澡堂,把地板全部撬開,發現裡面還有三具屍體,身體還沒僵硬,這都是昨天晚上殺的。於是把這一家子全都逮捕,繩之以法。
這些惡性案件,在宋朝並不是個案,史料中,還記載了其他同類慘案,《夷堅志》中就不止記載了上述一例。
在人們的印象中,宋朝的文明教化冠絕當時的世界,而且經濟繁榮社會富裕。可是頻發的反人類暴行揭示,宋朝存在著嚴重的社會問題,繁華背後,掩蓋著另一個讓人毛骨悚然的黑暗世界,連天子腳下的京城首善之區都會發生這種慘絕人寰的案件,其他地區普通百姓的生存狀態也可想而知了。在這個號稱富庶的朝代,百姓生活物質上竟然如此匱乏,以至於一件值錢的大衣,一個肥胖的身體就能讓歹徒起意殺人,雖然這些都是惡人的暴行,可要不是窮瘋了,誰會去幹這種悖逆人倫的勾當。
對於文人來說,宋朝是從未有過的美好時代,稱之為天堂也不為過,他們因而揮動如緣大筆極力謳歌,可是對於生活在那個時代的百姓來說,則不啻是黑暗的地獄,對於中華文明來說,漢唐以來創造的驕傲和榮耀被這個朝代斷送,此後幾百年裡每況愈下,不斷淪落,直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才扭轉了頹勢。
圖片來自網路公開渠道,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立即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