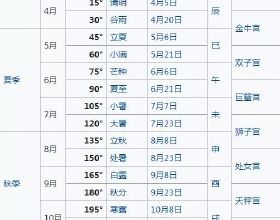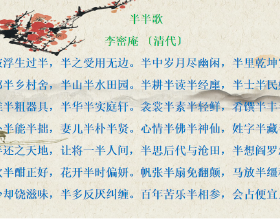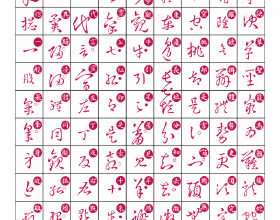雅加達街頭,斑馬線僅僅出現在新城區或老城最繁華地帶。圖源:視覺中國
在印尼雨季還沒消停時,我準備前往爪哇。印尼是一個非常成熟的旅遊國家,但看完許多關於瘧疾、痢疾、登革熱的介紹,我突然理解了史書裡中原民族對南方“瘴癘之地”的莫名恐懼。
當然,這份粗淺無知的恐慌,隨著我深入爪哇而慢慢消弭了。在十餘天的時間裡,我穿越了這座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島嶼,磕磕絆絆地完成了自己旅行生涯的“成人禮”。
“萬島之島”的心臟
飛機降落在雅加達郊外的蘇加諾—哈達國際機場,這座機場以印尼的開國總統蘇加諾和副總統穆罕默德·哈達命名。
印尼是由超過1.7萬個島嶼組成的龐雜群島,有超過300個民族使用著超過700種語言。1945年,蘇加諾宣佈這個群島脫離日本的統治,並在昔日荷蘭殖民地範圍的基礎上,重建為一個新國家。因此,即便蘇加諾最後政壇失意,這座首都機場仍以他的名字命名。
我跟隨抵達的人流,來到聲名狼藉的入境處——在早年的旅行者論壇上,印尼無處不在的腐敗就像它極致的文化多樣性一樣著名。入境處的官員以狡黠的目光掃視了我的護照,簡單地詢問了我的行程,就讓我通過了。這突如其來的順利令我感到了一陣短暫的欣喜,但我很快就迷失在雅加達的狂亂與喧囂之中。
殖民者建立的老城被稱為“巴達維亞”。1619年,荷屬東印度公司開始經營爪哇島西北沿海這塊地方,奠立了雅加達今天的政治地位。如今,這裡的幾處重要景點,包括國家銀行博物館、哇揚戲博物館都被打造成國家統一的象徵。其實,哪怕就在幾十年前,雅加達的政令也往往對那些偏遠島嶼鞭長莫及,而哇揚戲(即本土的皮影戲)則更像是爪哇及巴釐的傳統,而並非上萬座島嶼共同的文化記憶。
“多元而統一”是印尼國徽上的箴言。蘇加諾、蘇哈托向全國各地遷徙爪哇移民,並派駐了大量爪哇官員,與此同時,印尼各地的人也移民爪哇,尋求更好的教育與發展機會。在幾代人經營下,雅加達成為了一座典型的“亞洲首都”。
當荷蘭人離開時,巴達維亞只有區區60萬人口,但如今,這裡生活著超過3000萬人,是世界上僅次於東京的第二大都會區。雅加達可沒有東京那密如蛛網的軌道交通體系,除了狂躁的摩托大軍以外,每天的早晚高峰期,進出主城的高速公路和幾條僅有的市郊鐵路,都令人望而生畏。
對當時還罕有海外旅行經驗的我來說,雅加達真是一座令人心驚膽戰的城市。斑馬線僅僅出現在新城區或老城最繁華地帶,當地人泰然自若穿行其間,而我每要過馬路,只能忐忑地在路邊等候隨時可能竄出的本地人,瞅準時機緊隨其後。我甚至向朋友感嘆,在雅加達過馬路,是印尼最激動人心的旅行體驗之一。
而這份混沌中存在的秩序感,其實是印尼最迷人的部分之一。
世界的十字路口
爪哇島擁有印尼最完善的基礎設施:平整的公路、密集的機場,以及國內為數不多的鐵路。我在雅加達南郊的Cawang車站等候去往茂物的列車,站臺上熙熙攘攘,有許多雅加達人趕在週末去茂物省親或度短假。
小城茂物位於雅加達以南約80公里,曾是巽他王國都城,屬於印度教的勢力範圍。如今,茂物最著名的景點,是市中心那處由殖民者建立的茂物植物園。但我來茂物植物園,只是意在尋找萊佛士夫人紀念亭。在昔日荷屬東印度的腹地,有這樣一座英式建築,著實耐人尋味。
扼守巽他海峽與馬六甲海峽東口的爪哇島,歷史上就是全球海洋貿易重要的十字路口。就連伊斯蘭教在島上的傳播,都與這裡濃厚的商貿氛圍有關。擁有同樣的宗教信仰的人,在一起參加禮拜禱告,最便於陌生的貿易商之間開啟共同話題。
18世紀的最後一天,盛極一時的荷屬東印度公司轟然倒下,法國人、英國人相繼試圖把爪哇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拿破崙曾試圖以爪哇為根據地,切斷英國與東亞之間的海上貿易。英國人萊佛士正是在此背景下大顯身手,擊敗了島上的荷蘭與法國軍隊,為日不落帝國維繫了海上命脈。
1811年,萊佛士成為爪哇的代理總督。與舊有的殖民者不太一樣,萊佛士夫婦試圖在爪哇推行一定程度的區域自治,併力圖推行種種社會改革,恢復歷史古蹟。幾年之後,他的夫人死於瘧疾,最終被埋葬在巴達維亞附近。當局在興建茂物植物園時,就在最醒目的正門入口處,修建了她的紀念亭。
這座紀念亭,標記了萊佛士這段不太為人熟知的歷史:早在1819年新加坡開埠前,萊佛士已經在東南亞以學者和政治家的身份活躍了十多年,其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撰寫了《爪哇史》。也正是在他的主持下,被火山灰埋葬了數百年之久的婆羅浮屠終於重見天日,併為世人熟知。
萊佛士試圖喚醒爪哇的偉大,這份偉大是由不同文化共同寫就的。爪哇一直是四方勢力彼此競逐的舞臺。著名的“萬隆會議”給當地留下了一處重要的會址,而中國高鐵走出國門的第一個專案,正是連線雅加達與東南面的萬隆的雅萬高鐵;在萬隆東北面的井裡汶,Kesepuhan王宮裡來自巽他、爪哇、印度、伊斯蘭和中國的文化元素錯落有致,而北郊規模宏大的皇家墓地內,埋葬著井裡汶最受尊敬的國王Sunan Gunungjati(萬丹國的創立者)和傳說中來自中國的皇后。
中國與印度兩大古文明的角力,也從印支半島一直延續到爪哇。不可否認,爪哇的大部分史蹟中都有更鮮明的南亞元素,但位於爪哇中北部的三寶壟是一個例外。鄭和的船隊曾抵達這裡,城市之名就來源於鄭和的“三寶太監”之名。
在三寶壟,我走出殖民地風格的荷蘭式街區,意外闖入了一片由“下南洋”的中國移民興建的唐人街。眾多精美的閩南、潮汕、廣府的宗祠建築,讓人恍如置身中國南方。
探訪印尼的“中原”
從三寶壟出發去南部的班車,會在凌晨抵達日惹。我不得不先找一家通宵營業的麥當勞過夜。等到天空微亮,我便踏上了前往婆羅浮屠的道路。
每一個來爪哇的人,都不會錯過日惹。如果說爪哇是印尼的“中原”,那麼日惹是當之無愧的“洛陽”或“長安”。這座城市的周邊,分佈著印尼最重要的兩處古蹟,夏連特拉王朝的婆羅浮屠是一處重要的佛教遺蹟,而馬塔蘭王朝的普蘭巴南則是一處規模龐大的印度教寺院遺址。兩處古蹟相去不遠,始建年代也頗為相近。
婆羅浮屠與普蘭巴南寺院的龐大與精美,哪怕一本專著也無法盡數羅列,但這兩處古蹟其實和荷蘭人的巴達維亞、英國人的植物園或中國人的三寶壟一樣,仍然是外來文化的產物。大概在公元4世紀,印度教、佛教隨著印度海員的到來而先後傳入爪哇,並在此後約千年內都是爪哇島上的主流宗教。
但這並不意味著爪哇一直是文明發展中的被動傳入者。爪哇歷史的續篇,正是在日惹東北面的梭羅拉開序幕:1930年代,德國古生物學家孔尼華在梭羅河流域,發現了距今55萬年至10萬年前的古人類化石,從而填補了東南亞人類進化史上的研究空白。
從梭羅嘈雜的車站出來,我鼓起勇氣要去梭羅的古人類遺址看一看。當地的摩的司機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因為連他們也無法在茂密的叢林中,找到那幾處冷僻的遺址。
旅行指南警告我,梭羅向來以民風彪悍著稱,但我的感受卻截然相反。我正巧趕上了一個當地學校的春遊團,孩子們互相慫恿著推選出一位英文良好的溝通代表,幫助我在雨林裡找到了一處處罕有遊人的博物館和發掘現場。博物館的保安自告奮勇充當了我的免費司機,這讓我的訪古行程如虎添翼。在抵達最後一處博物館後,當我還在思忖著留下多少錢作為感謝費用比較合適,保安大叔就騎著他的摩托一溜煙消失在雨林中了。
雨林上方陰雲密佈,一輛路過的小車見到我在大雨即將降臨的土路上行走,執意要免費把我帶回梭羅市區。車上的音響,流淌出熟悉的旋律,與蔡琴的《心戀》幾乎一模一樣。我驚訝地詢問,才知道這首《Indonesia Pusaka》其實是《心戀》的原版,堪稱印尼的第二國歌。
大雨終於降臨,車上是兩國語言的歌聲。
作者 | 樓學
編輯 | 姜雯
南風窗旗下國際新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