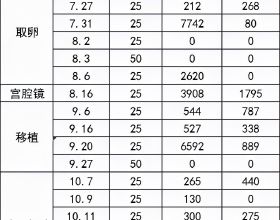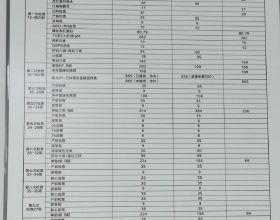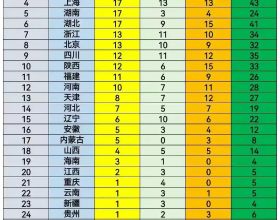《易》之作,乃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聖人探賾幽深而知宇宙萬物變化之奧妙,而欲以此理告知世人,然又不為常人所理解,故聖人以打比方的方式類比,即以“象”的方式告知世人高深的道理,以引導世人,適變而行,深入淺出地講解自然社會變化執行之規律,幽明、死生、鬼神俱已說清,深恐時人及後人難以理解,反覆說道,務必使言以盡意,此即聖人用心之良苦。後世之人反以為難懂,卻是為何?
王充在《論衡.自紀》中說:“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遠離,此名曰語異。”也就是說,今人讀不懂易經,只是因為時移世易,語言發生了變遷,其實聖人的本意是要把道理講明,從而教化天下人的,又怎麼會故意設定閱讀障礙,使之晦澀難解呢?那麼面對古今語言的變異,我們如何去讀懂易經呢?這就要從聖人作易的本意談起,再輔之以文字解讀,則讀懂《易經》並不難。
一切皆流,一切皆變,這個世界,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如何在變化的世界中把握“幾”,而至於“道”呢?聖人以“一陰一陽之謂道”來給“道”定義,此處之“一”即“無”之意也。無陰而陰以之生,無陽而陽以之長,即道為無陰無陽,太極之意也。道之生物,無心無跡,生養萬物而出於無心,育成萬物而無跡,萬物雖殊形,而其歸一也,一即道也,亦即無也。如之何及於道,之於無呢?只有適變。如何適變呢?只有識“幾”。如何識“幾”呢?,“幾”即動微之會,亦即動與不動之間,事已露端芽,將萌未萌之時,當提前預為之變,適變故無憂也。而世人常待變之極時,方才應變,此變之窮也,被動而變,亦為變之一種也。窮則見理,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然則何以窮理?以之數也。數何從知?以之蓍龜也。蓍者以求數,求數以得卦,得卦以觀象,“象以知往,逆數知來”,從而佔其吉凶悔吝,而知小大,所以趨吉避凶是也。
聖人即以此趨吉避凶之法,以象辭、繫辭、爻辭的方式曉喻世人,適變、窮變、通變,故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以至於道,“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聖人觀天文之象,知日月之執行,日月之執行與寒暑之變之關係;觀地理之象,知山川之走勢,水火之執行與災患之變之關係;觀人文之象,知社會人情之變革與平戰之變之關係。變,化之漸也;化,變之成也,變之漸為量變,變之成為質變,宇宙間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日之變,南行而冬漸至,北行而夏漸至,寒暑亦隨之變,植物榮枯見矣,動物換毛見矣,人之衣裘與葛見矣。月之變,望則圓,晦朔則隱,月圓則夜行無礙矣,隱則夜行掌燈矣,是以天變關乎人之變也。聖人觀象設卦,系卦爻辭以明變,明變以教人適變。六十四卦,聖人於社會之建模也,處六十四種形勢下,居爻之進退得失、消長盈虧,以知利弊吉凶,提示君子將做何種應對也。故易經之象有君子當如何行動之詞,是為君子謀也。於六十四種形勢下,處不同地位,當有不同之作為,此爻辭所繫也,處下者不可為之上,處上者亦不可為之下也,各當其所當,為其所為,則兇不至、悔無也;若不當位,則悔也,處此時,當觀與他位之聯絡,或敵應、或比附、或自作,吉凶悔吝為之變也。
故八卦五行皆聖人所設之象,即具象也,其目的在於說明抽象之理,即“道”也。此即一般與特殊,具象與抽象之關係耳。故王弼有言,“得象忘言,得意望象”,即直觀表象上升為抽象理論,則具象可忘也。客觀世界的萬事萬物,即永珍是普遍聯絡著的,又是普遍運動著的,生生不息,這種運動是有規律的,週而復始,對於這種運動規律的認識,是從觀察中得來的,而有些變化是長期漸變以至於質變的,難以滿足人類的求知慾望的速度,故創設條件,以促其劇烈快速地變化,以此得出自然條件下長期變化之結果,此即科學實驗,於反覆實驗後,驗證其可重複性,則理得矣。理即規律之一種也,公理者,推論而出定理,定理復推出定理,要之歸於公理也。即如《易》之象,萬事萬物,無窮盡也,要之歸於一也,即歸於無也,歸於《易》也,歸於太極也,“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也。
此《易經》之所以為萬經之首,亦即中國古代聖賢認識改造主觀與客觀世界之觀察與思維之模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