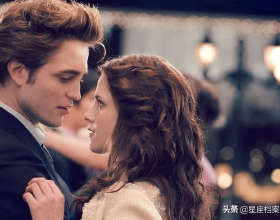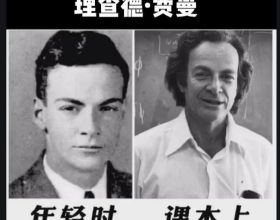原創:陳巽之
軍用卡車拉著我們五個新兵沿著汾河岸邊的公路疾馳,由於沒有和大部隊同行,我們都有落單的感覺,一路上都很少說話。大約一個小時後,我們就到了老連隊所在地——古東車站。顧名思義,這個車站在古交縣城的東面。我們到老連隊的時候已經中午,老兵們穿著黃不拉嘰的棉工裝,有的扛著十字鎬、有的扛著鐵叉子,有的挑著筐子,鬆鬆散散地從工地下班回來。我一看,這哪裡是解放軍,簡直就是種地做工的農民。這個時候我才知道鐵道兵是做什麼的,我想象中的解放軍是身穿整潔的軍裝,手握鋼槍在城市的大街上值勤,在邊防哨所站崗,在戰場上殺敵立功,保家衛國。我怎麼也想不到我所在的部隊是一支施工部隊,一想到今後我也像眼前的老兵們一樣,穿著土不拉嘰的黃色工裝在工地幹體力活。我心裡大感失望,好生後悔。但是,後悔已經晚了,就是後悔也不能讓人看出來。否則,老兵會認為我是一個思想有問題的落後分子,就不待見我,那樣的話,以後的日子就難過了。
剛從工地收工回來的“老兵”們,見到我們這些新同志,顯得十分高興和熱情。這些所謂的“老兵”,其實不老,大多數剛二十出頭,就比我們大兩三歲,按部隊的規矩,即使只比我們多當一天兵也是老兵,看見來了新戰友,他們都很高興,一個個笑呵呵的同我們打招呼:“來了,歡迎你們。”連隊有三個排,一排、三排跟隨大部隊轉場到新的建設工地去了,只留下二排在這裡。排長馮永宇點著名,把我們分到班裡。熊海金分到五班,我分到六班,白萬虎分到七班,陳祖波分到八班,孫成華分到炊事班。排長分配完,六班長趕忙安排老兵拿上我的行李,把我領到班裡,為我鋪好床鋪。
下午,老兵們去工地幹活,班長李振忠對我說:“小陳,你下午就不去工地了,寫寫家信,洗洗衣服,先熟悉一下班排周圍的環境。”我問清楚通訊地址和郵政編碼,從行李包裡找出紙和筆,爬在床上給父母親寫信。離開家裡幾個月,我長大了,知道該給父母寫些什麼,不該寫什麼。我在信中說我已分到老連隊,身體很好,長高了,長結實了。部隊的條件很好,餓不著也凍不著,首長和戰友們都關心我們,請二老放心。寫著寫著,思鄉之情油然而生,真想爸爸媽媽,想弟弟妹妹,也想我們家的大花狗了,在家時我從地裡幹活回來,聽到我的說聲,它老遠就跑過來,親親我的手,嗅嗅我的腳,搖著尾巴跟上我回家……距離產生美,遠離了家鄉,才覺得水還是家鄉的甜,人還是家鄉的親。
寫好家信後,我和熊海金、白萬虎等約好一起到河對岸的河口鎮郵政所去發信,我們沿小路下到河岸上,走過一座只有一米寬的木橋,河對岸是一片開闊的麥地,麥苗即將返青,農民們正忙著給麥苗澆水,泥土裡己經能聞到春的氣息。一條水渠把麥田劃分成兩片,一邊的田埂上長著挺拔的白楊樹,一邊成了人行小道,我們沿著水渠邊的小道走過麥田,六七個女孩子正在水渠邊的菜地裡勞動,紅的衣服、紅的頭巾,點綴在碧綠的麥田裡,就像幾株早放的桃花,鮮豔奪目,給人一種“萬綠叢中數點紅”的溫暖。這時節,我的家鄉該做什麼了,哦,該翻耕水田,育苗插秧了。
“嘻嘻——”“哈哈——”。一陣鬨笑聲把我的思緒拉回來。原來是地裡幹活的那幾個女孩子,幹活幹累了,想找點什麼事來取樂,她們看到田埂上走過來幾個小兵,不知是誰出了餿主意,決定拿我們這幾個小兵來取樂。她們這個喊“齊步走”,那個喊“一二一”,另一個又喊“向左轉”,邊喊邊笑,邊起鬨。把我們搞了個大紅臉,站不是、走不是,惱也不是,只好飛快地跑遠了。
從郵政所回到宿舍,我推開門一看。噫,不對啊。我的被子哪兒去了?我走出宿舍,看到同班的老兵朱桂紅正在水池那裡洗衣服。我走過去很不好意思地說:“老朱,我的被子放在床上好好的,我去郵電所寄了封家信,回來一看不知道哪兒去了?”他笑呵呵地說:“你的被子嘛,在那兒,你去看看。”我順著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涼衣繩上曬著幾件床單、被罩和棉絮。他說:“我洗衣服,順便幫你把被子洗了,關心愛護新同志是我們部隊的傳統,沒有什麼奇怪的。”我心裡非常感激,又感到不好意思。我是新同志,沒有想到幫老同志做事,反倒讓老同志幫我洗被子,只好一個勁地道謝。朱桂紅說:“這是舉手之勞,有什麼好謝的,在我們部隊這種互相幫助的事多著呢。”這是我下老連隊第一天,老同志用行動為我上的生動的一課:同志之間,要互相幫助。
⊹
陳巽之,原名陳家順,原鐵二師小戰士,現中鐵十二局集團老員工。大半生執筆弄文,結緣文字,曾寫公文、新聞以養家餬口、安身立命,案牘勞形之餘,不免偶抒性情,詩詞、散文和小說等時常留諸筆端,多次在全國詩歌、散文大賽中獲獎,己出版詩詞集《鴻爪雪泥集》、散文集《苔花米小牡丹開》、長篇小說《幾度秋涼》。
☆
來源:老兵原創之家
責任編輯:夢醒
編髮:鐵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