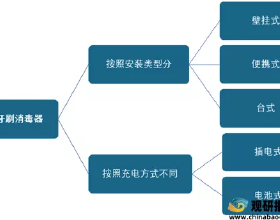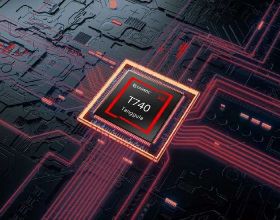■ 趙海波
家住小鎮西面,與海邊直線距離五六百米。早晨,我還在睡夢中,海水湧動的濤聲已經彙集到陽臺上,被厚實的木門阻隔著,有些急不可待了。我起床的第一件事,是睜著惺忪的睡眼,赤著腳去開啟房門,嘩嘩嘩的聲音和晨光一起破門而入。在小鎮的日子,新的一天差不多都是被這樣的濤聲拍醒的。
每年冬天,我都會回小鎮住上一段時間,沒有必須要做的事,整個假期悠閒自在。平日,我喜歡換上休閒服,穿上運動鞋,去海邊散步。從家裡步行到海邊,只需十分鐘。行走在瓊西路上,我遇見許多人,老老少少。他們在茶館門前的椰子樹下喝茶,高談闊論,小城剛剛發生的事情,一下子就傳開了。這種和時間一起打盹的生活方式,讓我心生羨慕。來到海邊,沿海岸漫步。海水漫卷夕照,落進水裡的夕陽一片血紅,蔚為壯觀。我在海邊走來走去,一邊感動於海水的姿色,一邊感慨於自己從這裡出發上路,幾十年後,成了故鄉的一個遊子。有時候,夜深人靜了,我心血來潮,也會去海邊溜達,在溫潤的夜空下,看岸邊的燈火、看泛著微光的海面,然後回家睡覺。
海邊有幾個公園。港灣公園建園時間最早、規模最大,曾經紅極一時。從大門進去是一條水泥路,綠化帶裡除了椰子樹,還有其他熱帶雨林植物,它們迎風搖曳,婀娜多姿。岸邊有座引橋,彎彎曲曲伸向大海,一家多功能娛樂廳彷彿漂浮在海上。夜晚,年輕人從四面八方匯聚過來,吃的喝的、唱的跳的,公園一下子熱鬧起來。二樓露天歌舞廳人滿為患,有些人找不到座位,只好站在護欄邊上。港灣公園的白天也是遊人如織。年輕人將這裡視為戀愛之角,許多人的婚姻之旅就是從這裡出發的。我第一次帶妻子回故鄉探望父母,遊玩的第一個景點便是港灣公園。那天的情景記憶猶新,雖然是深冬時節,但陽光明媚,暖意融融,樹葉清新得像被水洗過一樣。公園深處,曲徑通幽,穿樹林、過長廊、登亭臺,眼前是遼闊海面,風在雕琢著一層一層的波浪。那時剛領取結婚證,不知道將來的生活怎麼展開。但我深信,一切都會十分美好,就像此刻映入眼簾的風景,綠意蔥蘢,碧波盪漾。如今,公園已經不是原來的樣子,但我每次來海邊,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往港灣走去,有時走進公園深處,有時只是站在門外往裡看,然後轉身離去。
近些年建設的沙灘公園,被相關部門評為國家2A級旅遊景區,是小鎮景區建設史上的大突破。公園連著沙灘,隨處可見青草、不知名的花兒、龍血樹、三角梅、龍船花、蔓花生等,奼紫嫣紅,相映成趣。北方大雪紛飛的冬日,小鎮仍是溫暖如春,從北方來的“候鳥”和當地居民都穿著夏天的服飾,有的在海水裡暢遊、嬉鬧,有的在亭子裡吹拉彈唱,載歌載舞,一派歡樂祥和的熱鬧景象。
鐵路博物館是我不可或缺的打卡地。我時常在兩個龐然大物之間流連忘返:一個是曾經在西線鐵路上呼嘯馳騁的蒸汽機車。它龐大的身軀趴在鐵軌上,安靜從容,像一位老者用獨特的方式述說著屬於它過去的榮光。另一個是披著綠皮外殼的車廂。這節車廂原產於日本,曾經承載過一些驚心動魄的故事……流年似水,物換星移,如今它靜靜地躺在這裡,曾經輝煌的往事已經煙消雲散。
魚鱗洲南側的海灘上,佇立著一排風力發電機,遠遠看過去,只有手指大小,走近一看,卻是龐然大物。粗大的管狀塔架,高達六十米,三個轉子葉片,每個長約二十米,酷似飛機機翼。碧海、藍天和風力發電機,構成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夜幕降臨,海灘外圍的水泥路邊,擺開幾家燒烤小攤,攤主或男或女,或老或少,大多是鎮上的居民。年輕人從各個角落來此消夜,幾聲吆喝,眾聲喧譁。經過其中一家,一股煎炸的海鮮味牽住鼻子。檔主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婦女,她用夾生的普通話和我打招呼,我以家鄉話作答。她看我的眼神有些異樣,嘴角掠過些許的尷尬笑意。在島外生活多年,我的相貌已然沒有家鄉人獨有的特質,但一根海島舌頭依然堅硬如初。縱使習慣了都市西餐廳的燭光,回到老家,總是要去街頭攤檔尋找童年的味道。檔主走動時一瘸一拐,一支假肢藏在她黑色的褲筒裡,她必定有過一段痛楚的經歷,但對生活仍然充滿希望,並投入極大的熱忱。我將竹籃裡剩餘的十幾塊蝦餅都買了,她連聲向我道謝。走了百餘米,我回過頭,燈光微弱,幾乎沒入了夜色。有些人雖然卑微,卻很倔強,他們以頑強的毅力與命運抗爭,砥礪前行,努力讓自己的生命發出應有的光芒。我不緊不慢地走著,很快走過了這段水泥路。小鎮兩千多年曆史,就藏在一朝一夕安之若素的煙火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