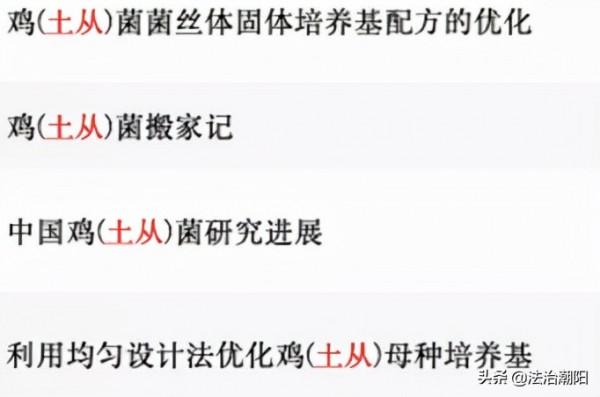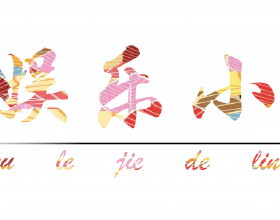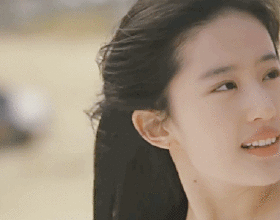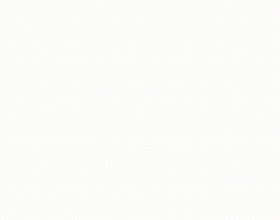蛋撻、荸薺、餛飩、芫荽……
若把這些湊成一桌子菜,鐵定能瞬間激發人們心中的多巴胺,為食客帶來滿滿的快樂,可是,你們能準確說出它們的名字嗎?
但塔?勃齊?混沌?元妥?
世上還真就有這樣“博大精深”的“食物語言學”,想讀對它們的名兒,可就是不容易。比如,不知多少人,讀錯了“蛋撻”。不信?慢慢往下看。
不認識,所以讀不對
要說被“食物語言學”搞得頭疼,也不全是我們自己的責任。
誰叫這烏泱泱的食材大軍裡偏偏藏著這麼多生僻字?
深諳此道的,荸薺能算一個。這倆字的讀音是 bí qí,燉鍋裡頭的荸薺早就被雞湯煨得軟爛香糯,只等被端上桌兒了。
荸薺,也叫馬蹄、地梨,果肉呈白色,是一種水生的草本植物,口感爽脆清甜,雖然頂著這個晦澀難認的名字,可它也許就藏在餃子餡兒裡、裝在水果籃裡或者乾脆躺在街上擺著的竹籮筐裡。
荸薺。攝影/大鵬DP,來源/圖蟲創意
自然,這能讓吃了啞巴虧的餮客們憋一肚子火——馬蹄這個名字又好聽又上口,為什麼非要拿“荸薺”倆字給人添堵?
“荸薺”這個名字背後,確實有由頭。
千百年前的古代,人們並不知道荸薺是啥,更沒有地梨、馬蹄之類的說法。《本草綱目》記錄了這種清甜果實的“離奇”身世——“烏芋,其根如芋,而色烏也,鳧喜食之,故《爾雅》名鳧茈。”
鳧,是指水裡的野鴨;茈,也就是茈草,放在一起,就得了這麼個簡單直白的名字。後來,可能是誤讀,也可能是讀音變化,總之,鳧茈成了鳧茨。古語裡頭,荸和鳧音相近,經過幾次音變,鳧茨也就成了今天的荸薺。聽著玄乎,可許多研究都佐證了這種猜測,比方說清代段玉裁就直言:“今人謂之葧臍,即鳧茈之轉語。”語言學家鄭張尚芳還指出,從“鳧”到“荸”的音變,可能受到了江淮官話的影響。
不過,也有研究發現,荸薺的成長還有另一套版本。從方言來看,“荸薺”的前世或許叫“脖薺”,也就是肚臍的意思。本來這種圓乎乎胖墩墩的果實,和肚臍有些形似,古音裡面,脖和荸正好是同音字,方言裡頭,“薺”的讀音千差萬別,可都和“臍”的發音沾點關係。所以,真相也可能是,大家拿“脖薺”這個名字稱呼植物實在太過順口,這倆字的字形和意義乾脆直接發生變化,肉月旁成了草字頭,荸薺就成了植物的專用名字。
總之,不管荸薺倆字再怎麼難讀,也是名正言順的。相比起來,“馬蹄”反而成了大家隨口叫叫的暱稱。
如果“荸薺”是生僻字在食材裡的小試牛刀,那藏在各大奶茶店配料表裡的“蒟蒻”(jǔ ruò)絕對算是大招。
對奶茶愛好者來說,想要在絲滑的奶茶裡添上這個配料,首先得攻破讀音這一關。
魔芋果凍。攝影/blueplanetz,來源/圖蟲創意
畢竟,比起果凍、布丁或者仙草這樣形狀口感都頗為相似的甜點,蒟蒻多少顯得冷漠而不近人情。
但是,要拿布丁之類的名字“概而論之”,無異於把耄耋老人生生退化成稚嫩孩童。蒟蒻這個名字,幾百年前就被蓋章認定了。宋代唐慎微的《證類本草》有言:“蒻音弱。口味辛,寒,有毒。”鄭樵在《通志》裡頭說得更明白:“蒟,其實曰蒟蒻,生於葉下,輿天南星班杖相似。其根生時可為糊黏,熟之可食。”《本草綱目》點出了蒟蒻的別名,鬼芋,吳其濬的《植物名實圖考》更是一語道破天機,將其稱為磨芋、由跋。
照這條線索一捋,好幾百年時間過去,蒟蒻也成了我們日常最熟悉不過的魔芋(磨芋)。不同的是,古時的蒟蒻扮演著藥材角色,發揮著消腫、解毒的功效,到了現代,因為生蒟蒻的塊莖帶有毒性,人們繼而沿襲了先人們琢磨出的好法子——碾碎成粉再成膠,蒟蒻搖身一變成了Q彈滑嫩、征服一眾甜口愛好者的甜品食材。
如果,生僻字為名的食材恰好碰上生動通俗的小名,殺傷力成倍增加——食材的真實學名早就不知被食客們丟到哪個犄角旮旯了。
這種苦,芫荽(yán sui)絕對能懂。
彆著急說壓根不知道這種食材,紅燒牛肉、紅油雞片、涮火鍋,哪道大菜裡不得擱上一點?因為芫荽有個小名,叫香菜。
芫荽——任勞任怨的香味點綴。攝影/陳家二少,來源/圖蟲創意
從芫荽到香菜,它到底經歷了什麼,可能還得靠李時珍為我們揭曉答案——
荽,許氏《說文》作葰,雲姜屬,可以香口也。……張騫使西域始得種歸,故名胡荽。今俗呼為蒝荽,蒝乃莖葉佈散之貌。俗作芫花之芫,非矣。
也就是說,芫荽是標準的外來戶,原名胡荽,民間也叫蒝荽,是為了貼合它“莖柔葉細而根多須”的外貌神態,後來被民間誤讀成芫荽。至於香菜,這個小名也有由頭,便是避諱——“石勒諱胡,故並、汾人呼胡荽為香荽”。到了現代,許是“荽”字過於拗口,就著“香荽”的臺階,也就簡化成了通俗易懂的“香菜”。
戲劇的是,在滿街都是香菜拌牛肉、香菜肉圓的現代,四川等地區還保留著“鹽須”一類的叫法,勉勉強強挽留了點香菜學名的味道。
不知芫荽心裡,能否好過些許?
認識,還是沒讀準
生僻字,不認識也就不認識了。更難受的是,把那些看起來認識的字讀錯,也是真的尷尬。
比如,“餛飩”怎麼讀?hún dun?滿大街好像都是這麼叫。
照正規的路子,餛飩,分別為hún tún,連讀時“飩”字變調為輕聲,便是hún tun。這種讀音,同樣也能追到吃食的出身上去。
餛飩的得名說法挺多。最離奇的一種得屬《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卷之四》中記載的民間傳說。相傳漢朝時,北方匈奴部落有兩個殺人如麻的首領,“渾氏屯氏”。這倆人無惡不作,百姓深惡痛絕,被惹急了,乾脆想出個法子,用肉餡包成一種吃食,煮熟了,就當“食惡人之肉”,這種吃食的名稱,也就成了影射“渾(hún)氏屯(tún)氏”的“餛飩”。但由於太過離奇取巧,這種說法飽受質疑。
《唐語林校證卷八》給出另一種說法,餛飩源於混沌,一位上古天神。混沌之名大氣、上臺面,可就是多借幾個膽子,敬奉鬼神的先人們也不敢說自己食用的是天上的神仙,如此,混沌的偏旁才發生了改變,成了大家碗裡的“餛飩”。據考證,“沌”讀作“混沌”時為“徒損切,音囤”,而與之形似的“飩”,徒渾切,音屯,“魂”韻,這麼推理下來,hún tún倆字的讀音都算是鐵板釘釘。
好吃但不好讀的餛飩。攝影/鯨尾視覺,來源/圖蟲創意
那滿街上的hún dun又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呢?學者得出結論,算是慣性思維搗亂。據推測,飩對各位好吃嘴們來說確實有些陌生,但與它形似的“沌、燉、鈍”都拿d當聲母,“舉一反三”下來,把餛飩讀成hún dun,自然合乎“邏輯”了。難怪兩廣地區的老餮們別出心裁地想出“雲吞”這個雅稱,這下總不會讀錯。
“餛飩”的字形也算少見,但即便是一碗香濃軟稠的“芝麻糊”,也要鉚足了勁給我們使絆子。就算是習慣了棒子糊糊(hú)的北方朋友,捧著這碗黑黝黝的小吃,也很難想到它的真實讀音,卻是芝麻糊(hù)。
在《康熙字典》裡頭,還暫時找不到“芝麻糊”的用法,可在《新華字典》裡頭,芝麻糊就有了“真名分”。糊(hù),專指像粥一樣的食物,麵糊、辣椒糊也都是這個路子。
黑芝麻糊。攝影/大鵬DP,來源/圖蟲創意
讓人委屈的是,闖過了本土食物的關,從西方“遠道而來”的吃食們,也要在讀音上橫插一腳。
香甜可口的蛋撻就偷偷地給大家挖了“坑”,無奈讀蛋撻(tǎ)的朋友實在太多,以至於不少媒體還專門發文糾正它的讀音。
媒體發文糾正讀音。來源/中國新聞網
確實不冤。字典裡的撻(tà)就一個讀音。再結合它的出身來看,蛋撻(tà)只能讀四聲。
蛋撻,英語名稱為“egg tart”。柯林斯大詞典中,tart實際指甜心的餡兒餅。諸多蛋撻中的佼佼者,葡式蛋撻的誕生,離不開一位英國人——安德魯·史鬥。他早年在葡萄牙品嚐到了傳統的蛋撻後,陶醉於美食的同時也開動腦筋,採用英國式糕點做法,改用英式奶黃餡兒,減少了糖的用量,創制出葡氏蛋撻。這種甜點,表皮精緻圓潤,一口下去,內餡柔和軟嫩,甜而不膩。蛋撻的讀音,實際上也就是tart的音譯。
港式蛋撻。攝影/Missraine,來源/圖蟲創意
邁過了點心埋的坑,往各大景區、飯店裡走走,絕對能再次收穫一堆關卡。
到了北方面館,想要來碗鮮香爽辣的筋道麵條,得先認識這倆字——餄餎(hé le)。餄餎面多為蕎麥製成,所謂“北方山後,諸郡多種、治去皮殼,磨而為面……或作湯餅,謂之河漏。”河漏,說得是個形象,得有專門的壓制器具,滾湯百沸時,麵糰被塞進器具中的圓洞、木芯置於洞口。雙臂用力一壓,細長筋道的麵條一點點落下,便是河漏面,也就是現在的餄餎面。
蕎麵餄餎。攝影/圖瑞,來源/圖蟲創意
走進南方小店,想來一份清爽開胃的涼拌豇豆,也得過了讀音這一關。“豇”和“缸”長得像是雙胞胎,估計讀音也差不離?可翻開康熙字典看看,“古雙切,音江。豆名。”這才是人家的真名——豇(jiāng)豆。
要是再碰到一家日料店,就輪到了牛丼飯的表演時間。
牛丼飯。攝影/sasazawa,來源/圖蟲創意
按照《新華字典》,得讀作(niú jǐng fàn),但要按日語譯過來,又得念成dòng。
再加上海鮮市場裡的文蛤(wén gé)、飯桌上的清炒莧(xiàn)菜、鍋裡頭的白水茼蒿(tóng hāo)……
茼蒿。攝影/金牛山人,來源/圖蟲創意
彆著急灰心,畢竟,挑戰還沒結束。
菜我愛吃,字我放棄
上面的情況雖然讓人頭疼,倒也算是有跡可循。可還有些食物,看著和藹樸實,一出手,真是絕招。
頭一種絕招,便是讀音兩可,橫豎都有理,只叫人傻傻分不清。
這一招,牛軋糖算是用到了極致。牛軋糖甜蜜香軟,美味可口,可就是這種惹人喜愛的吃食,愣是沒擠進《漢語大詞典》《現代漢語詞典》和《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的任何詞條,所以,牛軋糖究竟怎麼讀,在源頭上就多了重迷霧。
當然,牛軋糖也不是石頭縫裡蹦出來的。錢乃榮先生曾在“上海方言中的外來詞”中,揭露牛軋糖的身世。錢先生認為,牛軋糖是典型的外來詞彙,真身是一種西方叫做nougat的奶糖,音譯過來,在糖紙上,除了牛軋,還有鳥結、紐結三種寫法。如此,讀成牛軋(gá)糖也算是順理成章。
也有人站出來唱反調。有人專門拿媒體語料庫來推敲,發現在包括《新聞聯播》在內的媒體中,牛軋(zhá)糖的讀法反而更佔優勢,幾乎都把這種奶香馥郁的糖果稱作牛軋(zhá)糖。況且,軋有著“壓”的意思,正好符合牛軋糖的製作過程,讀(zhá),還是說得過去。
牛軋糖:“我很苦惱,我的名字到底咋讀?”攝影/dream79,來源/圖蟲創意
這還算客氣的,至少軋字(zhá)(gá)的讀音,在字典裡好歹露了個面。
可有些食物狠起來,連字典都束手無策。
2013年,咬文嚼字編輯部曾拿“字”說事兒,劍指《漢字聽寫大會》欄目的失誤。被推上風口浪尖的是一種味美肉肥的食用菌,在這檔欄目和不少人的認知裡,它叫雞樅菌,經常被讀作雞樅(cōng)。
經考證,咬文嚼字編輯部揭露了這樁“張冠李戴”的誤會——
雞樅,無論讀zōng還是cōng,都和食用菌沒有半分關聯。故事的正主,是個連輸入法都顯示不出來的“狠角色”——
這種食用菌蓋圓錐形,中央凸起,老熟時微黃,味道鮮美,因為味美如雞,長在土中,所以在古代典籍中寫為(土從),真正的讀音,實為cōng。雖然爭議不斷,字形也是頗為怪異,可絲毫不影響此菌闖蕩江湖。開啟瀏覽器,隨手一搜,各種可見的(土從)表達,既成了人們和輸入法搏鬥的招式,更默默地見證著這種食物的真實威力。
部分雞(土從)菌的表述。來源/中國知網截圖
然而,雞(土從)菌的“兇猛”放在另一種吃食麵前,瞬間成了輕描淡寫。逃離輸入法算什麼,真有能耐,不如從音到形,從字典到古籍甚至傳說,都無跡可循。
這一點,biangbiang面還真做到了。
與這種馳騁陝西、油鮮面香的賣相相對的,是它傳奇般的名字。
傳說,古時咸陽有位書生,腹中飢餓可是囊中羞澀。為了填飽肚子,他想出一個主意,到麵館先點上一碗熱騰騰的面,狼吞虎嚥吃完,叫來了老闆。書生問老闆,這面叫做啥?這可難住了老闆,只能反問書生,你說叫啥?還承諾書生,只要能說出面的名字,兩碗熱面,就送給書生。
書生也不客氣,拿來筆墨紙硯,一通龍飛鳳舞——
一點撂上天,黃河兩頭彎,八字大張口,士字向進走,你一么,我一么,中間夾個言字口,你一言我一言,中間夾個馬大王。心做底,月做旁,留個掛鉤掛麻糖,坐個車車逛咸陽。
停筆後,紙上多了一個大字,卻是沒一人見過。大夥連連稱奇,老闆也軟下口氣虛心請教,書生告訴老闆,這字念biang。此後,熱騰騰的寬面得了個名,biangbiang面。
biang字寫法
戲說之外,也有正兒八經的考證論辯。學者張志春曾根據考古和方言學推斷,biangbiang面實為餅餅面的音變。傅功振教授更是直接把baingbiang面的出世歸於秦地這方水土。照這種推論,biang實際上是秦人用水和麵,將麵糰放到石頭或案板上捶打時發出的聲響,也正是這個biang,在眾多擬聲中尤為響亮雄厚,活脫脫是秦人運用強音的寫照。
biang的字形更像是縮小版的百科全書,秦地的地理環境、居住形式、飲食習慣等統統濃縮在小小的字形中。比方說,“穴”代表古秦人以穴居為主的特點,言,實為鹽,這背後,便是生活在黃河流域的秦地先民早早地用鹽、製鹽的深厚歷史。
直白點說,biang不僅是民間生造出的字,更是名副其實的文化字。這背後,淌過的不止米麵醇香,還有獨屬於秦地的澎湃往昔和悠悠年歲。
biangbiang面。攝影/Shing547,來源/圖蟲創意
如同張光直的慨嘆:“到一個文化核心的最佳途徑之一,就是透過它的肚子。”
也如歷史學家孫隆基的概括,“吃”正是中國文化一種最堅固的深層結構。
或許,我們對食材“咬文嚼字”,守著的,就是這一條內涵吧。
參考文獻:
《趣味導遊知識》編輯部主編,趣味導遊美食知識,旅遊教育出版社,2015.
任繼愈總主編;吳徵鎰主編;呂春朝,徐增來副主編.中華大典生物學典植物分典 4[M].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17.
葉世蓀,葉佳寧著,上海話外來語二百例,上海大學出版社,2015.
(明)吳祿輯;曹宜,食品集本草 48,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6.
楊曉紅譯,看圖學百科叢書 科學的奧秘 3,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7.
宿育海,程鵬,陝人陝菜,西北大學出版社,2018.
朱鴻本冊主編;李西建叢書主編.木鐸之音[M].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2013年十大語文差錯[J].語文世界(中學生之窗),2014(05):19.
張銳.“餛飩”的誤讀[J].環球人文地理,2014(14):184-185.
嶽秀文.也談“餛飩”的“飩”的讀音[J].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2007(04):118.
郭伏良,高彭瑋.“牛軋糖”讀音探討[J].漢字文化.
作者:念緩
來源:廣東共青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