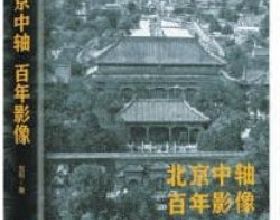導讀:為什麼科學革命沒有發生在火藥的發源地中國?歷史上各國各族都打仗,為什麼偏偏是歐洲人發明了“數理化”? 對於著名的“李約瑟之謎”,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管學院特聘教授文一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他的最新著作《科學革命的密碼——槍炮戰爭和西方崛起之謎》剖析西方近代史,揭示了西方戰爭資本主義和軍事重商主義的產生,在“國家競爭體系”這個框架內解釋了科學革命的爆發。 以下為採訪全文。
【採訪/觀察者網 劉惠】
觀察者網:文一教授,您之前研究的是宏觀經濟學,為什麼會轉向科學史特別是科學革命的研究?您最新的研究理論和成果是什麼?
文一:我一直在高校和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從事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和教學,轉向對科學史和“科學革命”這個李約瑟之謎的研究是緣於一個困惑。
大家知道李約瑟之謎有兩個方面:一是為什麼“工業革命”發生在18到19世紀的西方而不是東方;二是為什麼“科學革命”發生在17到18世紀的西方而不是東方。
我的《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一書只是探討了“工業革命”這一面,但是沒有回答“科學革命”這個方面的李約瑟之謎。
這個方面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為科學革命是“西方中心論”和新制度經濟學的最後堡壘;它是如此硬核,以至於迄今為止反對“西方中心論”最得力的西方歷史學家和最卓越的“東方主義”學者[包括詹姆斯•布勞特(J.M. Blaut)、唐納德•拉赫(Donald Lach)、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W. Said)、馬丁·貝爾納(Martin Bernal)、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約翰•霍布森(John Hobson)、阿布·盧格霍德(Janet Abu-Lughod)、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王國斌(R.Bin Wong)、傑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丹尼斯•弗萊恩(Dennis Flynn)、馬立博(Robert Marks)、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傑克•古迪(Jack Goody)、彼得·弗蘭科潘(Peter Frankopan)、歐陽泰(Tonio Andrade)]等都盡力迴避它。
在我看來李約瑟之問的這個方面必須回答,它的謎底必須揭曉。如果其答案的確是因為西方文明的古老制度基因和文化基因才自然導致了科學革命在歐洲文藝復興以後的爆發,那麼非西方文明就不能只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虛情假意、搞半拉子工程;而是必須全面擁抱孕育了近代科學的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的核心要素,才能完成思想啟蒙和現代化,才能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成為無愧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成員。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問題就大了。
透過多年的研究,我形成了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和答案,也就是我在《科學革命的密碼——槍炮、戰爭和西方崛起之謎》這本書所要闡述的。這本書中所引用的浩瀚史料雖然主要是二手資料,其錯誤在所難免,但是我對我的基本判斷和基於這些史料而形成的歷史觀是有信心的,因此希望能夠拋磚引玉,激勵更多的學者投入到這個研究方向來。
目前學術界對於科學革命為什麼爆發在西方而非東方的解釋,有好幾種相互關聯的流行“理論”。而我書中的結論與這些流行觀點背道而馳。
比如一種流行理論認為是古希臘公理體系與中世紀歐洲一神教經院哲學刨根問底的理性思維相結合,產生了17世紀的牛頓力學革命。按照這個理論,中國因為自古就沒有產生古希臘數學那樣的公理體系和一神教那樣的宗教信仰,以及中世紀那樣的亞里士多德經院哲學傳統,因此不可能產生科學革命。
這個理論面對的巨大挑戰之一是:為什麼同樣是繼承和吸收了古希臘公理體系與數學知識和猶太-基督一神論傳統的拜占庭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卻並沒有能夠產生牛頓經典力學革命和拉瓦錫化學革命?
另一種流行理論認為,雖然拜占庭的羅馬天主教(東正教)和中東地區的伊斯蘭教都具備一神論的特點,但是由於它們都不像路德和加爾文宗教改革以後的“新教”那樣支援“思想自由”,而是依靠經院哲學和宗教教條壓制思想自由,因此不可能產生科學革命。
這個理論也面臨至少兩大挑戰:挑戰之一是路德和加爾文的新教都是排斥科學的,他們都激烈反對當時的義大利科學家伽利略的新思維和哥白尼的日心說理論。挑戰之二是,無論是伽利略的經典力學理論還是拉瓦錫的氧氣燃燒理論,都恰好分別誕生在保守的天主教佔統治地位的義大利和路易十五與路易十六統治下的法國,而不是開明的新教佔統治地位的荷蘭、瑞典或德國北部的城邦國家。為什麼?
還有一種流行的解釋科學革命的理論,基於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在1953年提出的一個觀點:“西方科學的發展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發現透過系統的實驗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文藝復興)。在我看來,人們不必對中國的賢哲沒有走出這兩步感到驚奇。人類居然作出了這些發現,才是令人驚奇的。”
這是目前為止解釋科學革命較為“客觀公正”的視角,但愛因斯坦這個觀點所提供的理由仍然很不充分,面臨諸多問題和挑戰:
首先,18世紀的化學革命雖然與實驗有關,但與古希臘數學沒有絲毫關係。況且物理學巨匠牛頓本人花費整個後半生用實驗方法去研究化學現象,卻一事無成、鎩羽而歸,徒有卓越的邏輯思維頭腦和微積分這個極其先進的數學工具。而化學革命恰恰是由法國火藥局局長和傑出的鍊金術士拉瓦錫引爆的,而且比牛頓的經典力學革命晚了整整一個世紀。為什麼?
其次,究竟什麼是文藝復興以後才開啟的科學實驗傳統?人們喜歡引用弗朗西斯•培根的一句話:“知識就是力量。”那麼伽利略透過反覆測量鐵球在斜面滾動的實驗,究竟想要獲得何種力量?是想獲得上帝造人的力量?還是想獲得別的力量,比如精確預測炮彈在重力作用下何時何地按何種路徑準確命中目標的力量?
而且問題在於,雖然培根提出了系統觀察和實驗的方法論,但近代物理學的實驗傳統並不是由培根所在的新教國家(英國)開啟的,反而是在天主教統治下的義大利開啟的,是由伽利略和早他一百多年的前輩(比如塔塔格利亞)這些天主教徒開啟的。那麼為什麼伽利略和他的前輩們會開啟這樣一個科學實驗傳統呢?這個實驗傳統背後的動機究竟是什麼呢?是企圖用數學與實驗證明上帝的存在,還是有某種更加世俗的實用主義動機?
第三,古希臘文化和數學古籍被拜占庭帝國儲存得好好的,那為什麼延續上千年的拜占庭希臘文明(公元330-1453)卻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而要等到伽利略的出現?伽利略所處的時代究竟為科學發展和科學革命的爆發提供了哪些古希臘所不具備的社會條件?
答案顯然不在於“文藝復興”時期的翻譯運動本身——因為它不外乎將阿拉伯文獻中的古希臘知識翻譯成拉丁文而已,而拜占庭的希臘人卻不需要透過這種翻譯就能閱讀古希臘數學文獻。
答案也不在於北歐的宗教改革運動——因為伽利略並沒有受到新教的影響,而且一直是在天主教佔統治地位的義大利生活、工作、學習和研究。
伽利略所畢生關注的焦點之一,恰好是計算和理解不同重量的球體如何在不同傾角的斜面按不同速度滾動,以及鐵球如何在地球重力作用下做拋物線運動的彈道學問題,以便從中獲得拋射物體運動規律的認識突破。為什麼?
這就迫使我們回到戰爭,回到伽利略所處的充滿戰火的“炮彈(鐵球)滿天飛”的文藝復興時代。
事實上,伽利略在其經典名著《關於兩門新科學的對話》開宗明義昭示了“科學革命”的“戰爭密碼”:“……威尼斯人在著名的兵工廠裡進行的經常性活動,特別是包含力學的那部分工作,對好學的人提出了一個廣闊的研究領域。……生性好奇的我,常常訪問這些地方,純粹是為了觀察那部分人的工作而帶來的愉悅。”
伽利略創立的這兩門“新科學”,一門是材料力學——它是基於威尼斯兵工廠軍艦設計上幾十門重炮的對船體結構和建築材料的受力情況所進行的靜力學幾何原理分析,另一門是鐵球的運動力學——它是基於炮彈飛行的拋物線軌跡在慣性作用下的勻速運動和重力作用下的勻加速運動所進行的數學分析。
伽利略透過在威尼斯兵工廠大量實驗,為這兩門新科學奠定了數學基礎。他因此成為最早把嚴格的數學分析與物理學結合的第一人,成為經典力學革命之父。
他系統地借鑑了他那個時代的阿拉伯-古希臘數學知識,去解決戰爭中遇到的物理學問題,並發現和論證了新的物理學定律——即炮彈飛行的慣性定律和炮彈自由落體的勻加速定律,從而打開了通向現代精密物理科學和變數數學分析的大門。
而且伽利略這本經典名著,除了感謝威尼斯兵工廠的大量長期支撐和協助外,是專門題獻給他科研活動的贊助人——陸軍元帥、總司令、魯埃格地方長官諾阿耶伯爵的。
可見,如果沒有火藥傳入並點燃戰火紛飛的歐洲,伽利略不會去思考裝載幾十門沉重火炮的戰艦受力(靜力學)問題,更別說炮彈飛行的彈道學與動力學問題;拉瓦錫也不會去思考火藥燃燒和爆炸背後的化學機制問題;從而科學革命也就不可能發生。伽利略和拉瓦錫實際上就是他們所處時代自己國家的“錢學森”和“于敏”。
那為什麼科學革命卻沒有爆發在火藥的發源地——中國?而且歷史上各國各族都打仗,為什麼偏偏是歐洲人發明了“數、理、化”?
答案並不單單是古希臘數學知識的缺乏——因為拉瓦錫的化學革命不需要古希臘數學;也並非是實驗歸納方法的缺乏——因為中醫理論、中藥配方、針灸原理、《本草綱目》和《天工開物》都體現了實驗歸納法在古代中國知識體系中的系統應用;相反,實驗方法論鼻祖培根透過採用系統性羅列現象來找出背後原因的歸納法,不僅自己在科學發現上毫無建樹、一事無成,而且這種方法論的哲學表述也是由阿拉伯傳入的。
你看一看自從火藥傳入歐洲以來歐洲發生戰爭的頻率,它比同時代的中國高出上百倍。這張圖中的每一個白點代表一場戰爭,可見文藝復興以來世界上95%以上的戰爭爆發在歐洲,其中絕大多數戰爭爆發在科學革命爆發前後的四百年(1400-1800)間。

圖中央密集的白點表明近代歐洲簡直是個火藥桶,歐洲人爭奪世界資源和殖民地的戰爭又將戰火燒到了美洲、非洲、中東和亞洲。資料來源:維基資料
因此問題的根本答案,是中國基於火藥-火炮的高烈度、高頻率戰爭和圍繞這種新型戰爭而展開的“國家競爭體系”的缺乏——而只有處在這樣一種高烈度、高強度、高頻率的熱兵器戰爭和國家競爭體系中,才能激發出社會精英和國家力量對數學、物理、鍊金術和其他科學知識的巨大渴望、需求、扶持和投入。
因為精確描述炮彈的變速軌跡,需要代數、三角函式和平面幾何;全面理解火藥爆炸和物質燃燒的機理,需要非常豐富的鍊金術知識和大量耗時、耗錢、耗人工的化學實驗,需要國家扶持的專門實驗室(與今天見到的大規模化學實驗室諸如著名的貝爾實驗室沒有本質不同)。
這是為什麼企圖統一歐洲的路易十四國王早在17世紀初斥巨資成立法國科學院的原因,和為什麼路易十五國王批准成立“法國火藥局”、“拉瓦錫國家實驗室”和巴黎高等軍事學院的原因。
中國明朝和清朝都沒有這樣做,所以在科技上落後了;然而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這樣做了,因此趕上了歐洲列強。
其實任何文明都具有兼收幷蓄其他文明的能力;一旦社會需要,就會向別的文明學習和借鑑。正如中國古人不怕千難萬險前往“西天”取經,也正如義大利人不怕千辛萬苦將阿拉伯數學翻譯成拉丁文一樣。
既然所有文明都具備向別的文明學習的拿來主義精神,中華文明也就不需要自己獨立發明佛教或古希臘數學——當年如果需要的話,完全可以透過絲綢之路向阿拉伯文明學習、引進更加先進的數學。
可中國早期歷史上向西方學習和從事文化交流的社會精英,比如張騫、玄奘、班超以及後來的宋明理學大師們,並沒有這樣做。為什麼?難道是流行歷史觀所說的“東方專制主義”造成的思想束縛或缺乏“學術自由”的緣故?或難道是因為中國人特別不擅長數學思維,以至於根本沒有能力吸收西方的數學?
問題的實質恰好在於,出產過《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本草綱目》和《天工開物》的古代中國,沒有產生對“變速運動中的炮彈軌跡”進行精確數學描述的社會需求,沒有產生對火藥及其相關化學成分實行規模化大生產和集中研發的社會需求。
而近代中國經過鴉片戰爭的屈辱和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無情打擊,才終於激發出了這種意識和需求,因此才提出用精密科學——“賽先生”拯救中國的口號。因此中國的國家力量才開始籌建兵工廠、西南聯大、軍事學院、科學院,並公派大批留學生赴日、赴歐、赴美學習數學和科學,與17世紀的法國和英國派學生去義大利拜訪伽利略一樣。
其實法蘭克人、日耳曼人、盎格魯-撒克遜人、俄羅斯人、斯拉夫人、日本入、埃及人和印度人,並不太追問自己的祖先為什麼沒有發明古希臘數學(錯把古希臘人當成自己的祖先又另當別論),也沒有因此而妄自菲薄自己的文化傳統。
今天的中國人喜歡朝自己的老祖宗追問這樣的問題,其實是反映了當下中國對科學與數學的巨大社會需求,意識到落後就要捱打,意識到科學與軍事技術的密切關係。
其實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城邦國家,也是在嘗夠了炮彈的滋味以後,才懂得了“落後就要捱打”的道理,否則但丁和馬基雅維利便不會強烈呼籲實現國家統一和中央集權,達芬奇和伽利略也不會如飢似渴地學習軍事工程技術和數學了。
既然達芬奇和伽利略所掌握的數學知識是從阿拉伯引進的,因而中華文明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把所有其他古老文明擁有的東西(比如歐氏幾何)都通通發明、包辦了,才能發展出科學。
所以,問題的關鍵不是誰先發明瞭歐氏幾何,而是誰先產生了把數學應用於軍事和槍炮工業、應用於描述炮彈軌跡的社會需求。正是因為這種巨大社會需求的缺乏,使得最先發明火藥的中國沒有產生科學革命。
明治維新以後才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海軍與炮兵學院的日本(數學、物理是其基本課程),沒有像中國人那樣因為自己祖上沒有發明平面幾何,就大肆惋惜或者否定自己的文明。拜占庭人坐在古希臘數學和哲學的故紙堆裡上千年,不是也沒有發展出牛頓力學和拉瓦錫化學嗎?
其實,中國歷史上戰爭最頻繁的春秋戰國時期,恰好也是中國歷史上科技飛速進步的時期。但是,那個冷兵器時代的戰爭對科技進步的推動作用,在進入了熱兵器時代的文藝復興時期已經過時,因此遠遠比不上基於“火藥-火炮”的熱兵器戰爭,對科技進步的刺激與推動作用來得大。
近代火藥-火炮與古代弓箭的差別,相當於今天的核彈-反導技術與當年的火炮-城堡技術的差別。
而火藥與火炮技術是在中世紀末期和文藝復興初期才傳入歐洲的。恰好是火器的傳入,使得歐洲在十字軍東征和文藝復興以後,進入了一個類似於中國歷史上的歐洲版“春秋戰國”時代,因此才能夠引起一系列深刻的社會、政治、軍事、經濟制度變革,把與火藥和火炮相關的製造技術和物理化學原理推向極致,從而爆發一場“軍事革命”和“科學革命”,為叢林法則下適者生存的歐洲國家,贏得一場遠比“春秋戰國”時代還要慘烈百倍的國家暴力競賽和軍備競賽,提供源源不斷的激勵與推力。
基礎科學與藝術一樣,都具有很強的公共品性質,需要國家力量有意識的投入併為其創造平臺——包括類似科舉制度和科學院體制在內的科學人才吸納機制,以及政府採購、軍工產業政策和一系列崇尚征服大自然的意識形態的推動。
這是為什麼哪怕蘇聯計劃經濟時期根本沒有所謂“民主、自由、法治”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可言,但是因為有斯大林國家意志的投入,蘇聯時期的科學和數學成就不僅超越俄國曆史上的彼得大帝時期,而且超越同時代的自由歐洲,與同時代的超級大國美國並駕齊驅。
因此,我們必須重新梳理西方崛起的歷史,去真正把握西方崛起的歷史規律。只有這樣,發展中國家、落後國家才知道應該怎麼樣崛起,才有信心透過吸收西方的先進技術和文化成果,推陳出新,從而在自己的歷史文化基礎上創造富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工業文明和科技文明。
觀察者網:研究科學史會涉及到不同文明之間的對比研究,您認為在不同文明對比研究的時候需要避免的陷阱是什麼?
文一:需要避免 “西方中心論”陷阱。首先,人們必須認識到古代科學和近、現代科學的根本區別。比如古代數學,無論是古希臘的平面幾何還是古代中國的代數,都是常量數學,都是以不變的數量和圖形為研究物件的。而近代數學是變數數學,是以變化中的數量-空間關係為研究物件的。而促成數學由常量數學向變數數學這個歷史性轉化的,恰好是中國的火藥-火炮,是炮彈力學和彈道學。
其次,數學不是科學,而只是科學研究的一個工具。而任何工具都有其侷限性。比如今天的數學已經如此發達,但人們仍然不可能從數學中推演出化學元素週期表和人體結構。
第三,科學不只是物理學,它還包括化學、生物學等等,而這些科學很少用到數學,因此與古希臘根本扯不上關係。
第四,近代數學的發展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是由近代物理學的發展推動的,以至伽利略-牛頓之後歐洲的數學就是物理學和力學,而近代物理學又是由炮彈力學推動的,不是人們通常認為的是由亞里士多德經院哲學(三段論)或者古希臘平面幾何式的公理體系運動推動的。
第五,像任何一門史學研究一樣,科學史研究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史料;一方面是史觀───即如何理解和解釋史料。恰好在史觀這個角度,我覺得國內大多數學者陷入了流行的西方中心論陷阱,而這個陷阱是19世紀以來尤其是20世紀後由一大批持“輝格史觀”、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西方中心論”的學者創造出來的,是站在“西方勝利者”的角度書寫的,包括韋伯和今天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們。
而且好多研究科學史的國內學者並不瞭解科學本身的發展史,而是被物理學教材的編寫方式欺騙了,誤以為實際的物理學理論是按照教材提供的演繹方式展開的。
比如華東理工大學的高能物理學家廖瑋教授就在《科學思維的藝術》一書中就批評了這種對科學的錯誤認知:
“常常可以看到有人把物理學當作是邏輯嚴密的精妙理論,可以由少數的原理解釋廣泛的現象,例如牛頓力學體系。許多人以牛頓作為科學的典範,甚至有人把牛頓力學那樣系統化的理論才當作是科學。這種對科學的理解實際上是把教科書上總結好的科學理論當作為科學,甚至當作是科學的全部,實質上是隻把已經完成的理論當作科學。擁有這種思想方法的人常常不知道科學理論中的概念從何而來、有什麼根據……好像哲學家在書齋中的思辨和想象可以憑空建立起科學發展所需的概念,可以勝過科學家在實驗室裡艱苦的實驗工作以及對實驗的思考。……以上這種對科學的理解,是一種對現實顛倒的思路。”
觀察者網:正如您在《科學革命的密碼》中提出,現代革命是軍備競賽是戰爭的產物,那之後的國家是否要透過戰爭來進行科學革命?和平和發展是我們的時代主題,現代社會的科學革命是否會以更加激烈的競爭來推動,比如中美之間的貿易戰、科技戰。
文一: 自古以來,重大的科學突破都是由現實問題推動的,是為了回答當時科學家所處時代最重大的現實問題,包括生產活動和實驗室提出的問題。而人類最重大的現實問題莫過於生存問題,生存危機是人類面臨的最大危機。
生存危機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是大自然的自然災害對人類的威脅,人類為了防避自然災害帶來的巨大危險,必須要產生對大自然進行解釋和預測的能力,這是一個推力。另一個就是戰爭,戰爭對人類的集體性生存造成威脅,給科學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刺激。
比如,美蘇冷戰期間的軍備競賽為西方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創造了多少科學論文,創造了多少科學家和多少技術突破。

1975年,美國宇航員托馬斯·斯塔福德和蘇聯宇航員阿列克謝·列昂諾夫在太空握手。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而這種跨國軍備競賽可以一直追溯到文藝復興時期,伽利略正好是那個時代軍備競賽的領軍人物,他一輩子都在威尼斯兵工廠研究火炮技術。因此伽利略的經典物理學突破完全是軍備競賽和戰爭需求刺激和推動的。
從理想的角度講,人類未來的科學發現的動力不要源自戰爭、軍備競賽,而是希望源自商業競爭,甚至完全被人類的好奇心推動。這個才是我們希望應該作為人類理解自然界、掌握自然規律的最好動力,但是這只是理想狀態。
現實中,科學革命的爆發卻不是這樣的。甚至直到兩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現實中的科學研究和突破頁往往是受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推動的。比如西方頒發的諾貝爾獎,建立各種各樣的實驗室,鼓勵科學家在雜誌上發表文章來獲得提拔和獎金等,都是在刺激科學的發展。
因此,我們不應該把“科學活動應該是怎麼樣的”混淆於“科學活動實際上是怎麼樣的”。理想中的科學應該完全由好奇心推動,可惜現實世界中尤其是歐洲歷史上的科學並非如此。
第一,科學思維的主要材料來源於實踐活動的刺激和提出問題,但科學思維的結果又高於實踐活動,獲得了對普遍規律的認識和第一性原理。但是離開了實踐活動的刺激,就不會提出問題。沒有問題,就不會有答案(科學理論)。
第二,科學尤其是化學生物學的進步即便在早期都不是依靠一個人坐在辦公室依靠數學工具就能靠推導演繹而獲得,而是必須依靠成本高昂的實驗室和科學團體的大規模協作才能獲得。而這個高昂的組織成本和實驗成本需要國家力量的扶持才有可能。
第三,歷史上的經典物理學革命和化學革命受熱兵器戰爭的推動,並不能得出今後的科學革命也要靠戰爭驅動。它只是說明人類之所以對科學活動投資是因為實踐和時代向智者提出了古人(包括古希臘人和古中國人)根本沒有碰到過的劃時代問題,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涉及國家存亡,因此才有了社會力量對科學的重視和科學革命的爆發。
科學發展的歷史和社會動力學告訴我們,一個國家對科學的功利性需求越強大,那個國家的科學發展速度就越快;那個國家對科學研究活動的資金投入越多,科學進步就越快。這是事實 ,但是人類可以跳出科學發展的這個功利主義階段,主動地投入和投資於科學活動。
問題在於當生產力還不足以把人從基本生存壓力下解放出來的時候,一個幾萬人的貧窮小國家是沒有動力去推動基礎科學研究的,除非有現實的社會需求。因此在和平年代為了進一步推動人類科學的發展,所有國家必須聯合起來將科學本身設為目的,成立專門基金,設立一系列激勵機制獎勵機制來鼓勵科學活動,哪怕它們沒有任何回報。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閱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