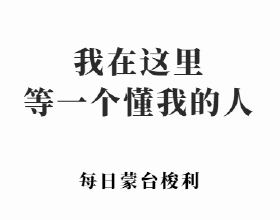張虛懷,你他孃的就是個叛徒。
謝玉淵一聽,手腳麻溜的把高氏從灶間拉出來,安坐在椅子上。
“郎中,被子在哪裡,我幫你去拿。”
“咳……咳……咳……”
張郎中虛咳了幾聲,目光朝東頭的房間瞄了一眼。
“那個……男女有別,我的房間,你別進去。還有,我這院兒雖小,規矩卻大。”
謝玉淵笑道:“郎中,規矩是什麼,你說。”
張郎中手指了下,“東屋住著我侄兒,他得了個古怪的病,吹不得風,見不得光,那屋你別去。每日三餐端到門口就行。”
謝玉淵下意識地向那屋子看過去,笑眯眯道:“郎中,我曉得了。”“後院的那些個草藥,也別亂動,少一根,你給我捲鋪蓋走人。”
“我不會亂動的,放心吧。”
張郎中腦子裡想了半天,似乎也沒有什麼可交代的,一拂袖,又回了房。
謝玉淵心想,這算什麼大規矩,謝家的規矩那才是大到天上去呢!
正想著,幾件破棉襖劈頭蓋臉的向她砸過來。
“都縫一縫。”
謝玉淵趕緊接住了,一低頭,差點沒被燻死過去,這衣服一股子什麼餿味。
高氏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像幼鳥似的,對周圍的一切充滿恐懼,直到手裡拿到針線,她的臉上才有點血色。
她好像也對衣服上的味道很不滿意,嫌棄地撇了撇鼻子。娘安頓好,謝玉淵端了臉盆,拿了毛巾,“郎中,洗臉了。”
張朗中撅著屁股在箱籠裡找破衣服,聽到喊,頭也不抬,“放著吧,給我侄兒準備早飯去。”
謝玉淵放下臉盆,回灶間盛了早飯,端到東屋門口。
就這麼放在地上是餵狗的,她找了把竹椅,把碗筷都放在竹椅上,朝屋裡喊了一聲。“少爺,吃早飯了,天兒冷,得趁熱吃。”
見屋裡沒動靜,謝玉淵也沒等,把餘下的早飯一一擺上桌。
剛擺好,看到屋角有堆髒衣服,便抱著髒衣服走到井邊。
目光像是被什麼牽引住似的,她朝東屋看過去,心裡驚了下。
竹椅上的早飯不見了,但那門還是關得嚴嚴實實。奇怪,她竟然一點動靜都沒有聽到。
張郎中這時,抱著一堆舊衣服出來。
看到美麗的女子蜷縮在屋角縫衣服;堂屋的桌上擺著熱氣騰騰的早飯;井邊傳來打水的聲音。
恍惚間。
他感覺又回到了那一處遙遠的地方,那裡有……“郎中,家裡有皂角嗎?”
張郎中猛的回神,“有,有,在灶間。”
謝玉淵衝他笑了笑,“郎中,咱們家得多買點皂角,衣服味兒大,得好好洗洗。”
張郎中臉色變了變,心想,你這丫頭自來熟,也有個分寸,誰和你是咱們家。謝玉淵拿了皂角走出來,又往東屋瞄了眼。
竹椅上,多了幾個空碗。
謝玉淵飛快的把空碗收拾下,把竹椅放回原處,一邊放,一邊嘀咕。
“這少爺是餓死鬼投胎嗎,怎麼吃得這麼快?”
屋裡。
臨窗而立的少年,手微微一顫,一雙漆黑的眼睛,無波無瀾。
……
張郎中吃好早飯,就陸續有病人過來看病。
謝玉淵怕高氏見多了陌生人發病,把她挪到了灶間。自己則在外面端茶遞水打下手。
她眼睛耳朵都沒閒著,把張郎中給病人說的話,開的方子,一樣樣記在心裡。孫老孃走進來時,就看到這樣一副場景。
張郎中半眯縫著眼睛,一隻手捋著山羊鬍子,一隻手搭著病人的脈,老神在在。
一旁,謝玉淵那個小賤人正在添茶。
添完茶,她順勢磨了幾下墨,又拿起抹布東抹一下,西抹一下。
孫老孃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一下子不太敢走進去。“阿婆來了。”
謝玉淵迎出去,臉上帶著笑。
“是來找孃的嗎?娘在灶間給郎中縫衣服和被子。郎中說,孃的針線活兒好,要幫著在這裡縫幾天。”
孫老孃一張口,發現自己不知道該說啥,話都叫這小賤人堵住了。
“阿婆不用擔心,我會把娘照顧好的,張郎中是個大善人,不會白讓娘幹活的,總會給幾個錢的。”
一聽到錢,孫老孃立刻扯出個笑。
“我哪裡來找你孃的,我就是不放心你,好好侍候張郎中,多點眼力勁。”
“那阿婆慢走,我就不留你了,郎中那裡離不開人。”
孫老孃看著她的背影,心裡酸溜溜的想,她什麼時候說要走了?